新诗谱(三)
作者: 胡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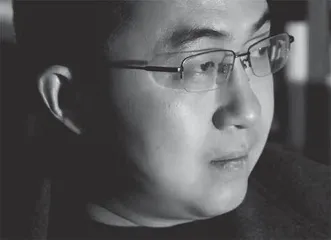
笔者于2015年至2024年,奋笔10载,增删5次,撰成一部《新诗谱》,共入166个词条,论及167位诗人,起于鲁迅,迄于郑小琼,前者生于1881年,后者生于1980年,两者生年恰好相隔一个世纪。除了宋渠宋炜兄弟被合写,其余诗人均被单写为一个词条。所有词条概不分段,刁钻其视角,精当其剪裁,高频其信息,妖冶其语法,奇特其结构,浓缩其篇幅,兼顾诗人评传、名篇细读、文化比较与思想探赜。现摘发部分词条,以飨读者。
陆忆敏(1962 —)
陆忆敏的名作《美国妇女杂志》,仔细读来,可能就响应了至少一个普拉斯(Sylvia Plath),至少两个伍尔芙(Virginia Woolf)。首先,来说“两个伍尔芙”,其一,是指女权主义者伍尔芙,比如,她写过《一个自己的房间》。这个伍尔芙虚构过一个故事——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妹妹,具有惊人天赋,为了追求戏剧与自由,她从家里逃到伦敦,却没有机会写作,也没有机会演出,最后只字没写就自杀了。然而,时代变了。来读《美国妇女杂志》,“你认认那群人/谁曾经是我/我站在你跟前/已洗手不干”。“你”是谁?很有可能,伍尔芙早已谈及——不过就是叫那个妹妹缝袜子和煮肉的“母亲”,爱她和打她的“父亲”,嘲笑她的“胖子”,同情她并让她怀了孕的“经理”。“你”,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当然与那个妹妹相比,陆忆敏已经有了更多勇气。其二,是指小说家伍尔芙,比如,她写过《海浪》。这个伍尔芙虚构过一个人物——诗人纳维尔(Neville),在出名以后,他老是带着自己的名片,不是给别人看,而是给自己看,不是为了社交,而是为了随时补习、提醒和证明自己的身份。来读《美国妇女杂志》,“把发辫绕上右鬓的/把头发披覆脸颊的/目光板直的,或讥诮的女士/你认认那群人,一个一个//谁曾经是我”。“我”是谁?也许,乃是“女士的复数”。“我”,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普拉斯怎么说?“我认为个人经验不应当是一种密封的、顾影自怜的经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诗人才把“我”关联于《美国妇女杂志》。伍尔芙曾谈到,直到19世纪,女作家都只有“起居室”,而没有“自己的房间”,甚至“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半个小时”。似乎是为了极具针对性地声援伍尔芙,陆忆敏写出组诗《室内的一九八八》——你看看,她不但有了“室内”,还有了“一九八八”。这个组诗共包括十五首日记体短诗,很有可能来自与某个幽灵同住的经验,这个幽灵不妨就是提前从作者/生者身上分裂出去的他者/死者。来读第二首,亦即《二月二十四日》,“我多次重归旧园/在那昏暗的走廊终端/与先人们同时落难”。来读第三首,亦即《三月十四日》,“你苍白的手指扶着黑色的圆领/在谛听流水/经过昨天流进你的心田”。来读第十一首,亦即《六月二十一日》,“寂静中我听到你的琴声/我像一只白色的现代鸽子倚床而睡/嘴角挂着几滴乳汁般的句子”。有你有我,琴瑟和鸣;想写就写,不看脸色。其次,来说“一个普拉斯”,是指死亡艺术家普拉斯,比如,她写过《拉撒路夫人》。普拉斯有过多次自杀,终于在1963年得逞。来读《拉撒路夫人》,“死亡/是一种艺术,像其他一切事物。/我做得很好”。如果说普拉斯是死亡艺术家,那么,陆忆敏就是死亡研究所。来读《美国妇女杂志》,“挟着词典,翻到死亡这一页/我们剪贴这个词,刺绣这个字眼/拆开它的九个笔划又装上”。来读《可以死去就死去》,“汽车开来不必躲闪/煤气未关不必起床/游向深海不必回头//可以死去就死去,一如/可以成功就成功”。还可参读《死亡是一种球形糖果》《死亡》和《温柔地死在本城》。对于陆忆敏来说,死亡,几乎成为可以把玩、刺绣、拆卸、组装、品尝而无 须回避的事物。诗人写过一篇短文,试图理解伍尔芙;写过一首短诗,专门献给普拉斯;伍尔芙和普拉斯成全了她的“崇洋诗学”,却无益于她的“尚古诗学”。她留下了一个疑问:“谁能理解伍尔芙?”又留下了一个反问:“为什么古代如此优越?”陆忆敏之为陆忆敏,不在“西洋的中国化”,恰在“传统的现代化”。来读《避暑山庄的红色建筑》,“我所敬畏的深院/我亲近的泥淖/我楼壁上的红粉/我楼壁上的黄粉/我深闺中的白色骷髅封印/收留的夏日,打成一叠,浓墨鉴收/它尚无坟,我也无死,依墙而行”。“崇洋诗学”给了诗人以“死亡”的加速度,“尚古诗学”给了诗人以“无死”的自觉性。故而陆忆敏的结果,定然大异于普拉斯。柏桦对此诗“充满了敬仰之情”,认定其为“天才之作”“偶然之作”,因而令他“必须正视,必须服从,必须热爱”。还可参读《沙堡》和《墨马》——前者长于用典,“赶鱼过山”,后者长于用喻,“以墨为马”,两者均堪称杰作。诗人在有限的异化中,保全了那颗固执而优越的汉语之心。她带给我们一个值得称庆的复活节——古风的复活节,汉风的复活节,以及中国传统的复活节。崔卫平怎么评价陆忆敏?一则曰“文明的女儿”,再则曰“结晶式的人物”。最后,伍尔芙还曾再次谈到莎士比亚的妹妹:“她被埋在公交车停车场。我相信她还活着,活在你们身上,活在不在场的女性身上,因为她们正洗碗、哄孩子睡觉,但她们是活着的,因为伟大的诗人不会逝去,会一直存活,唯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肉体罢了。”莎士比亚的妹妹,借用了我们之间的一个肉体——也许是伍尔芙,也许是陆忆敏,后者正是前者的后裔,因而后者的最早一批作品,或可视为前者的最后一批作品。
杨 黎(1962 —)
1980年读到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窥视者》,1986年参与创办《非非》,对于杨黎来说,这是两个迥乎不同的仪式——后者是个较大的仪式,前者是个较小的仪式,后者热闹,前者孤独,后者好比打群架,前者好比偷禁果,后者只波及了他的一时,前者却锁定了他的一生。在读到格里耶之前,诗人已读过加缪(Albert Camus)——他与朋友办过一个刊物《鼠疫》,并曾张贴于成都春熙路。格里耶,加缪,有何不同?“在勾引者面前我永远是童子鸡,而在被勾引者面前,我就像一个流氓。”关于那本《窥视者》,如今,诗人记忆犹新,“我刚刚读了两页之后,合上书,抬起头,眼睛看向很远的地方;比天空还远,比阳光还远,就在我身边的房屋和房屋之间”。是在1983年,诗人写出《中午》和《怪客》,确定了“写作的叙事性”。到了1986年,他又写出《街景》和《小镇》,确定了“写作的客观性”。这四首小长诗,毫无疑问,都曾受教于格里耶,乃是后者所谓“结结巴巴登场的新作品”。格里耶开创了“新小说”,该派志在改革法国传统小说——从巴尔扎克(Balzac),到前文曾有言及的加缪。新小说听命于“视觉”和“自觉”,偏嗜“同时性技巧”,恪守“中性视角”,倡导“零度叙事”,极为厌恶“形容词”“抒情”和“连贯性”。按照巴特(Roland Barthes)的说法,是要剔除“物的浪漫心”;借用这个说法,还要剔除“人的浪漫心”——也就是说,他们鼓励“人的物化”,却反对“物的人格化”。诸如此类的美学怪癖,在杨黎这里有过不同程度的展现。《中午》也罢,《怪客》也罢,《街景》也罢,《小镇》也罢,《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也罢,都像是从新小说——《窥视者》或《橡皮》——里面滑落出来的文字片段。就在1986年,秋天,诗人写出《高处》:“A,或是B/从耳边/传向远处/又从远处/传向森林/再从森林/传向上面的天空。”全诗长达一百二十三行,絮絮叨叨,反反复复,抛出了一个“本然而非使然”的世界,亦即格里耶所谓“它存在着,如此而已”的世界。小长诗《高处》可与文论《声音的发现》共读,在很大的程度上,前者践行了后者,后者阐释了前者,两者具有极高的“互文性”。因而可以接着说,《高处》乃是一首“声音之诗”,一首“能指之诗”,一首“无情无义之诗”。对于作者来说,“这首诗的完成,实现了我对诗的最终理解”;对于读者来说,“你们可以怀疑它们的意义,但是,你们无法怀疑它们的存在”。《高处》堪称登峰造极,据内部消息,直接影响过蓝马的小长诗《世的界》。这是闲话不提;却说杨黎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从格里耶出发,他还有机会走上一条绝路。到了2000年,他提出“废话理论”。何谓“废话”?“语言的极限、盲区和永恒的不可能。”诗人立志把“废话”写成“诗”,把“诗”写成“废话”,实际上已经炒了“语义”的鱿鱼。少女有少女的“语义”,银行有银行的“语义”。1984年,诗人向领导保证再也不会旷工,却在当天下午永远脱离了单位。无论是对“少女语义”的屈从,还是对“银行语义”的冒犯,都让诗人感受到了“语义”的蛮横。“语义”对“我”做了什么呢?既有服务,又有管制,既有保护,又有欺负,既有引诱,又有拒绝,既有打开,又有隔离,既有教导,又有唆使,既提供真相,又倾倒谎言。诗人不要“语义”(哪怕比峨眉山还重),只要“废话”(哪怕比气球还轻)。他发出了赞叹:“诗啊,言之无物。”——杨黎在新诗史上最早启动了“意义背离计划”,唯其如此,柏桦断言“杨黎才是真先锋”。我们已经被这个邪派高手带到了沟里,甚至于快要忘记得一干二净——脏水是脏水,婴儿是婴儿,既有“负语义”,亦有“正语义”,岂能不分青红皂白?到了2017年,诗人自己也坦陈:“但我天生又是一个抒情的人,一个酒色之徒,而且我命中伤感成分还非常重。”也许,只有“性”,能够让诗人从逍遥的“废话之诗”,偶尔返回到挂满蛛丝的“反废话之诗”。最后这个小结,也许无褒无贬——法国新小说又叫“反小说”,那么,杨黎新诗或可称为“非诗”。
森 子(1962 —)
森子出生于呼兰区,定居在平顶山。呼兰区意味着什么呢?北方,乡村,童年和少年。平顶山意味着什么呢?中原,市街,青年和中晚年。诗人曾多次写到萧红,后者也是呼兰区人氏。2010年,诗人写出《哈尔滨》:“你喜欢积极的否定?不,不。/我心中有两个半月亮。”当然,还可参读《呼兰河传》。森子有点像萧红笔下的“有二伯”,却更像卡夫卡(Franz Kafka)笔下的“饥饿艺术家”。有二伯是个什么情况呢?“他很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他很喜欢和大黄狗谈天。他一和人在一起,就一句话没有了,就是有话也是很古怪的,使人听了常常不得要领。”可见“人类中心主义”,随时都有碰上钉子的可能。有二伯是颗大钉子,森子是颗小钉子;有二伯更喜欢动物,森子既喜欢动物又喜欢植物。“我想换一只鸟的心脏,可以轻盈地飞翔。我还想安上喜鹊的尾巴,招摇过市,华丽异常。”你难道没有看见吗,还有只野兔,时常出没于森子的字行?这里且不说他的动物诗,先来说他的植物诗。自2002年至2003年,诗人写出大组诗《采花盗》。来读《水仙》:“她来自温暖的南方/穿着单薄的衣裳/你也可以说她/什么也没穿,不会/影响她绽放的心情/她总是蹲在寒冷的街上/装蒜。”来读《辛夷花》:“假如,我可以娶一棵树/做妻子,就选中你/为一棵树而结一次婚/或头昏一次,没关系/如果你同意,就让/花瓣落地,我们一起/到街道办事处登记。”水仙能“被装蒜”,令人莞尔;辛夷能“被结婚”,令人莞尔。故而桑克谈及《采花盗》,直接判为“轻体诗”(Light verse)。英国轻体诗比如奥登(Wystan Hugh Auden)的《学术涂鸦》,既有讽刺性,又有愉悦感。《采花盗》,没有一丝讽刺性,却有大把愉悦感。“人类中心主义”向后退,“植物中心主义”向前进,两者都放下了身段,将从悲剧性的分居转向喜剧性的同居。采花盗,采花盗,盗既采花,花亦采盗。这是植物的荒诞派,也是人类的乌托邦。与其将《采花盗》判为轻体诗,不如判为广义的“咏物诗”。很多诗人写咏物诗,或用“隐喻”,或用“叙事”,只有森子兼用“隐喻”与“叙事”。1997年,诗人写出《废灯泡》:“灯丝断了,它从光明的位置退休/它最后的一眨眼解除高烧/回到寒冷而透明的废品博物馆。”2003年,他又写出《雨刮器》:“它就剪出扇形的前途/给我们看,并折返于/90度的最大值。”然而诗人的开悟既不在于对“隐喻”的苦练,也不在于对“叙事”的精通,而在于他对“隐喻”与“转喻”的混淆,对“叙事”与“抒情”的混淆。笔者所谓“混淆”或可换算成森子所谓“克服”——用“李白”克服着“杜甫”,用“抒情诗”克服着“史诗”,用“有限”克服着“无限”,用“树叶”克服着“个人面积的不均”与“想象力的不收费的服务”。2010年,诗人写出《比喻》:“我克服了具体的一个个小城堡,/在每个困难上插一朵玫瑰,/从危机模式的诗歌中撤离。以不对克服对,/主题是对反应机制的羞愧。”此诗堪称“元诗”(metapoem),从头到尾,无非诠释了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警句:“从某种意义上看,诗一向是诗的反面。”反面永远在身体对面,食物永远在嘴巴外面,诗人和诗永远在死胡同里面。饥饿艺术家抬起小脑袋,撮起双唇,最后对那个管事怎么说?“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这个艺术家还会有知音吗?骷髅地里,站着森子!来听森子怎么说?“而饥饿状态也许是食物(世界)最愿意看到的人的状态,它不是惩罚,而是一种奖赏。所以饥饿、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的诗人好于饱食者,他永不满足,虽然他知道自己的消化能力有限。”这个诗人把“星星”当作“佳肴”,命中注定,他要把所谓的轻体诗写成本色的“困难诗”(difficult verse)。“我相信诗艺,诗相信我与它合作的诚意。”2020年,诗人写出《灵魂的白》:“前天收到萨克斯来信/还未来得及回复/耳朵的海洋回荡乌贼的钟声/我真是服了你了/铁打的日子象征日出的困境/不是鸡蛋皮太厚,而是钙质的流失/问好,就这样/向怎么也抓不住的被缚的感觉致敬!”诗人用“抓不住”克服着“抓住”,用“未完成”克服着“完成”,用“不可解”克服着“可解”,用“不满意”克服着“满意”。他在手气好的时候,比如自2021年至2024年,先后写出组诗《临筐集叶》,系列诗《夜枝》,还有长诗《丁香谷——火星1号》,分别感念人世、触碰未知并探索科幻;在手气不好的时候,他几乎用“诗的高等函数”克服了“读者的云计算”。“读不懂是读者的权利”,他说,“而晦涩是诗的权利”。真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1999年,他写出《山谷中的鹰》:“一只鹰在山里,和它的影子,/它的孤独获得了支援。”我们不挑食,食物太多了;诗人最挑食,食物太少了。诗人已经“不计成败”,那么,我们岂有资格抱怨他的“晦涩”。来听王家新怎么说:“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仍坐在小广场上:那里并不是没有什么可吃的,他们体现的是饥饿本身。因此在人们的嘲笑中,他们仍会将他们的饥饿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