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庐山,不周山
作者: 陈仪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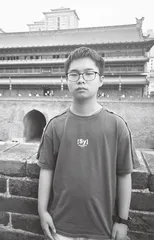
作者自画
我从小就热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最佩服法国的天才少年兰波。我喜爱诗,借由诗得以虔诚地享用文学的珍馐。当我独自大声地朗读一段文字,用响亮的、热烈的声音朗读时,文字,尤其是诗歌的语言,将使我脱离现实,把我带去一个更加明亮广阔的世界。当我回来时,海天一色,了无纤尘,我也就干净了。我也很爱哲学——那是一种理性的深刻的世界规律的凝固体。一个人若是触碰到哲学的表面,也就触碰到了他世界的奥秘;一个人若是触碰到了哲学的深处,也就触碰到了他自己的奥秘。我感激文学和哲学带给我的一切欢娱,感激它们无穷尽的“美”,令我在一片尘埃中,寻到一块璞玉。
一
1101年,庐山。
乾明寺长老垂首合眼,低声诵经,已有一个时辰。他缓缓起身,仰头看向墙壁,一尘不染的洁白之上,有墨色纵横挥洒。交错的笔迹历经多年,依旧清晰如故,于曦光微风下熠熠生辉。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长老!”
狂舞风中,粗袍飘逸,消瘦的身躯拄杖立于伽蓝之外。他的身后,万竹摇曳,云雾轻笼。
这是苏东坡人生当中极其平常的一次出游。那时,夕阳垂地,江流四野,他和他的朋友总是这样三五成群,扶风而上,沿着蜿蜒的山路和白日的光迹,遁入山林。六十多年,在那段崎岖而绮丽的岁月当中,苏东坡几乎看尽了八方山河。他由衷喜爱着那些草木江石,喜爱着那些自然奇景,每每双脚踏入泥泞,自然的气息潜入鼻腔,便觉畅快不已,仿佛他本便是那山野的一分子。
苏东坡的笔头功夫是不得了的,纸上的行文是他此生最骄傲的事情之一。在迷蒙的少年时代,他的文学天赋以及高远志向便已显现出来。这样的一位天才,落笔便是三尺惊鸿,掠过人心,以至于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也要满头大汗道一句:“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年轻时候,总要有一个光怪陆离的精神世界;若此世界一日被磨灭成幻影,那么心灵也便无处安放。苏轼的精神世界,是开阔的,是豪迈的,是辽远的;这样一个精神世界,引领着他日夜不辍地书写。这样一种书写,让他声名远扬;也是这样一种书写,让他客死他乡。
当故事的车辙又回到其本身,访问乾明寺的苏子瞻并未考虑这些事情。他只明白,文学是他一生无可摆脱的习惯,他的文字愈来愈辉煌,他的面容愈来愈凄凉。
“长老,你可还认得我?”
“施主可是子瞻?”
苏东坡端正长袍作了个揖:“正是十七年前来访的苏子瞻。长老竟然还记得。”
“萍水相逢,情缘已深千丈。”
童子已取来茶水。苏东坡跨过门槛走了进来。檀香,烟火,以及山中的潮湿气,这些气味是他所熟悉的。他闭目冥思,恨不能解开衣衫,将肉身与此云雾融合一体。
一场意义横跨千古的对谈已经开始。对谈的具体内容,历史只字不提。我们可以窥探到,这场对话会包含苏轼那漫长人生的无限回忆,还有如何也绕不过的那些才华、理想、自由和勇气。最后,所有的话语,都沉寂于那本便无声的山林里。
二
对谈的起点,降落在眉山下的山溪之间。苏东坡的父亲在青春的末路回头顿悟,二十八岁才开始奋发科考。他有一妻程氏,贤惠温婉,精通诗书。丈夫的觉醒,离不开这位女子每日无果却不弃的劝说。同时,程氏还为苏家生下了两个男孩,大儿苏轼,小儿苏辙。
苏轼的幼年缺乏父亲的陪伴,还好有母亲,不仅照顾他的衣食起居,还亲自教他诗书文理。日益长大,他也进学堂读书去了。一日,小苏轼随先生读到《范滂传》,学了那个冤死而无悔者的故事,心中撼动。他回到家,奔到母亲身边,很认真地问她:“我如果做个像范滂那样的人,您会同意吗?”程氏笑着说了句:“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哪有长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君子呢?有哪个母亲,不渴望成为圣贤之母呢?程氏着实未曾想到,年幼的孩子竟然有如此高远的志向。她看见了一颗波澜不惊而注定汹涌澎湃的心,叫她欢喜,叫她惊异。或许凭着这样一颗心,她自己的孩子真会兼济天下;或许凭着这样一颗心,自己的儿子真会在汗青之上闪烁其名;或许凭着这样一颗心,只是这样一颗心······
苏轼的童年,除了书典,还有山野、伙伴和游戏。他上山种树,下山寻果。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他的父亲苏洵回来了,沉着而不脱稚气。一日,苏轼在泥土里挖出一块绿色的鱼形石头,苏洵见了,欣喜无比:“这是个好兆头啊——我的儿子——是要干大事的人。”
苏洵回家后,积极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天才!他无比确信,自己的两个孩子是天才。他自己也是一位天才。眉山的炊烟市井已经容不下三个天才那蓬勃的梦想。于是,父子三人踏上了一段毅然决然的旅程:出川。
三
此时苏轼已经娶了王弗为妻。苏轼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性,便是母亲程氏与妻子王弗。历史上,他的母亲身世并不详细;他的妻子,有名有姓。
苏轼与王弗初遇时,两人皆是情窦初开的年纪。那时王弗身披绮罗,娉婷如霞,在闺中饱读诗书,也早早听闻了那位天才少年的大名,便心生爱慕。一次她从瑞草桥到中岩游山朝庙,却见到苏轼正于池畔拊掌唤鱼。两人忽然目光对视,皆是惊愕,而后面露羞颜。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节啊,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落英缤纷,花鸟从容。才子佳人静静伫立于此,风声之中,年华过隙。
未来的故事暂且不提。父子三人一路前行,游山玩水,看尽人间繁华。嘉祐元年,苏轼首次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一纸书文,让当时的考官及文坛大师欧阳修和梅尧臣大为震惊。欧阳修读罢文章,拭去脸上的汗珠,大喊“快哉”。由此,苏轼的名声彻底在京师传开。苏轼无比自豪,满眼尽是那无限光辉的未来。他的才华已经敛藏多年,他的等待即将到达尽头。他要与史书上范滂等人并肩,他的梦想在此刻闪闪发光,而这时,眉山却传来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
苏轼回乡,悲痛不已。几年后,妻子王弗离世;两年过去,慈父苏洵也撒手人寰。苏轼霎时从幸福的少年变成孤单的旅人,身边只剩下弟弟苏辙。而彼时朝堂上,一场风雨倾泻而下。一个名叫王安石的怪才开始了他的变法。这场变法,太过超前,太过危险,太过理想,以至于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欧阳修,因反对新法,被迫离京。多么陌生啊,多么诡异啊,腥风血雨洗刷过后的朝堂,成了一个苏轼完全不认得的迷离世界。
四
苏轼最终还是惹怒了王安石。他于是前往杭州。又几经波折,来到了徐州。那时的徐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泛于梁山泊,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
苏轼从未见过这般景象。百姓流离失所,寄身草野。满天都是号哭声,满地都是死尸。这不是那个繁华无边的人间,这是一个真实的、苦难的、辛酸的世界。苏轼常常想起那时眉山满城丝绸,或是汴京花灯满楼,人潮汹涌,车马相依。高耸的楼房正在他的记忆深处闪烁光芒,读到的诗文正在他的心中搭建一个完美的世界。人们的脸上都是笑容,每个日子都充盈欢娱。
然而这世界就此彻底消失了。那个他曾经幻想出来的极乐人间,无疑是不现实的。如今他身在异乡,头顶上黑云压城,脚底下淤泥遍地。他终于认清了现实。初来乍到时见到的悲惨景象,让苏轼苦思冥想,他的脸上没有微笑,他的灵魂不复从容。他明白,圣人的言语打动不了上天,美好的诗文改变不了江河,道德的律令也拯救不了人间。命运是不可改变的,要想在命运的洪流中挽回希望,就必须靠自己,靠双脚,坚守着脚下的土地矢志不移。既然无法扭转命运,那就超越命运。
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他带着士兵们,拿着簸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板(六尺)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效仿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
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密州等多处为百姓立下功劳。人们对他的认知不再仅仅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才子,更像一个伟岸的英雄,苏轼在这“英雄”式的行动中,收获了真正的快乐。他的眼里又有了光影。他欣然书写了这样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遥遥银河的天狼星啊,此刻,你又可听见那一声呼喊?如果你已有耳闻,为何又一遍遍将其掷于黑暗?
五
乌台诗案。
这是一件谈到苏轼便不可避开的事情。它改变了苏轼的一生,改变了他的文学创作,也使苏轼的名字在中国千年文坛愈加闪耀。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此番话语被新党利用,说其狂妄自大,不满朝廷。自古以来,文学都是脆弱的。那些伟大的诗文,君子赞叹其大意,小人窃喜其字节。皇帝大怒,要杀苏轼。此时朝廷上下,却出现了一大片力保苏轼的声音,朝中元老纷纷上书,连那位曾无比厌恶苏轼的王安石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是的,中国的文人最可贵的品质,便是惺惺相惜,团结与共。君子和而不同,才人赏识才人。没有人愿意目睹冉冉巨星的陨落,他们明白,只要这满天星辰还在闪耀,大宋就永远有希望,尽管他们终其一生也无法改变现实的风雨飘摇。
于是皇帝将其贬到黄州。这是一个比徐州还要荒芜的地方,最初苏轼担任的职务是团练副使,只能寓居在寺庙当中。
1082年,苏轼四十五岁。这是他在黄州的第三个年头。他卧在床榻之上,听着窗外苦雨弥天,海棠散落,想着自己灿烂的往昔,心痛不已。
苏轼在寒食节写下这样几句诗——“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两首寒食诗被写成帖,并且流传下来,成了如今众人赞赏的天下第三行书。
苏轼还有一首词,是这样说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样的词,太孤独,太忧伤,与苏轼前半生的诗词大为不同。是怎样的经历造成了如此的孤单?是命运,又是命运。不过此时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还有他人的命运。
苏轼的家人,大多已经离世了,唯一的弟弟也不在身边,天涯太远,尺素无音。而他的那些挚友、恩师,也相继离世。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这样的文字,出自欧阳修之手。那时欧阳修还在思念梅尧臣,如今,他自己也驾鹤西去。芳丛不再,青春不复。童年,故乡,爱情……一幕幕往昔的故事在苏轼的眼前上演,他看着一个锋芒毕露的少年,满心欢喜,不谙世事,幻想着改天换地,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不过是卑微的蝼蚁。
他哭了。若是年幼时,母亲一定会在身边为他拭去眼泪;若是年轻时,妻子一定会坐在身旁为其开导;若是三年前,弟弟也一定会陪他诉尽衷肠……而此刻,他发现自己是第一次独自面对人生的困苦,思念无尽,只剩明月夜,短松冈。
大难而不死,对他而言已经是幸运,但他对此并不领情。他渴望的不是苟活于世——他怀念从前——但他更渴望未来——哦,过去是多么璀璨啊,自己是多么可悲啊,如果他那时谨言慎行,那么这个王朝一切光荣的大门都仍会为他打开,史书上依旧会有他的名字。他已经积攒了足够多的名声与功德,他完全可以避免掉这种悲戚的命运,这个渺小偏远的地方本永远不会有他的身影……可是生活——真正的生活,不过是一场没有排练的悲剧——演员们无序地舞蹈,生命正在幕后燃烧。一切死亡都没有回音,一切结局都没有句号。那些离开与变化都太突然了,苏轼完全没有准备。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成为心里那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