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中国人挥之不去的灵魂味道
作者: 新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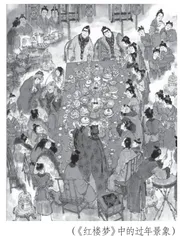
■ 策划/新作文 执行/寒云
年少时,过年,总是一个孩子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过年代表着会有各种好吃的,会有新衣服,会有压岁钱,还会有数不尽的欢乐和玩闹。而长大后,不论身居何方,不论这一年是喜是忧,过年回家,永远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识。年味,成为我们岁末最能安慰心灵的灵药。
◇古人的春节
从古至今,一年一度,过年都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
中国人对传统旧历年是最为重视的。一般来说,从腊月二十三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这二十多天里,人们会持续忙碌,张罗着如何过一个满意的新年。
如果从夏代的“岁”开始算,那么中国人过年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当然,“年”这个说法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据古代辞书《尔雅》记载,尧舜时称年为“载”,夏代称年为“岁”,商代称年为“祀”,直到周代才称为“年”,于是开始有了过年的说法。
经过了朝代更迭,过年的习俗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拿比较近的清代来说,也与现在的过年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比如说过年放假。清代的政府官员并没有周末,放假靠的是旬休制度,每十天为一旬,也就是说十天里只有一天是休息日,比咱们现在还辛苦点。唯独到了旧历年,假期是最长的。
当然,放假的日子也不是随随便便定的,而要由一个叫作钦天监的机构看历书来决定,哪一天开始放假最吉利。在放假之前,各个政府衙门还会举办一个隆重的“封印”仪式——把衙门用的印拿封条封起来,表示在这一期间不再使用了,于是正式进入过年放假阶段。
再比如,放鞭炮。现在,虽然城市里禁止放鞭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听到,在远郊乡村地区,鞭炮声最密集的时间是子夜,也就是半夜12点。古时却是傍晚六七点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开始祭祀了,在屋里摆供,祭祀先祖,屋外就开始噼里啪啦鞭炮声不断,这意味着,礼敬祖先的重要程度要远超新旧交接。
当然,像祭祀这种习俗,有些家庭依然保留着,而有些家庭对此已经不那么重视了。就像有些传统习俗被依然保留至今,而有些也已经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悄然远去了。
◇年味
“80后”、“90后”小时候,年味儿是排骨、肘子、带鱼、虎头鸡,是口袋里装不下的糖果和花生,是新衣新裤新鞋子,是炉火边的热气腾腾的饺子蘸醋。二踢脚、窜天猴要离得远远的,成挂的鞭炮要拆成一个一个玩,新年的钟声伴随着张罗年夜饭的热闹,菜似乎总在锅里翻滚出浓香。
现如今,物质上的丰裕让孩子们不再对于吃的玩的有特殊的期盼,那么过年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很简单。团圆和乐是过年的真正奥义,形式只是点缀,内涵才是精髓,年味儿不是淡了,而是我们忙着刷手机、打游戏,淡漠了长久而耐心的陪伴。“合—家—欢—乐”四个字,其实缺一不可。
后来长大了,离开家乡,一年难得回家。再后来,大家都感慨说,“年味越来越淡啦”。
中国人心中这份至高无上的仪式感,千百年来声势浩大的全民狂欢,兴味似乎日渐稀薄了。
但年味儿和这项辞旧迎新的重大仪式,成了每个小家庭自发的、不约而同的“自觉”。比如:全家人一起贴对联、贴福字、挂灯笼,以期来年红红火火、时运亨通。给长辈、孩子包红包,为这大吉之日再添几分喜气与祥和。
(《红楼梦》中的过年景象)
◇年货
四十年前,我们的物质生活较之今天只能用匮乏来形容,就连过年期间的鱼、肉、蛋、奶都要限量供应。
作家王小妮记录了一个20世纪70年代北方城市家庭领到的春节年货票证:两瓶啤酒、半斤水果糖、一只冻鸡、一只冻鱼。这分量听起来已经不仅仅是匮乏的程度了,就算是两个好友相见叙旧小酌也不够吃个痛快,更别提作为一顿丰盛的年饭了。在那个物质并不富饶的年代,春节期间的冻鸡冻鱼就足够让人向往,就像王小妮说的,“现在有人嘲笑吃货,吃货才是我们深厚的传统”。
如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早已经不是稀罕的年货了,人们在吃之上寻找更高的精神追求,比如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到餐厅吃年夜饭,享受美食的同时,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陪伴家人身上。故宫年夜饭曾成为热炒的话题,恰恰反映的是对一顿年夜饭而言,人们的需求已越来越多样,甚至愿意为传统文化和仪式感买单。
新年期间,我们不断寻觅新的美味,曾经引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可能已经被更加美味的年货取代,但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新年期间的美食也在不断进阶。
一到新年,另一种必备的年货就是新衣服了,诗人海桑短短几句就道出了新衣服在年货中的地位:
一个人穿新衣服
是去走亲戚的
一家人穿新衣服
是要娶新媳妇的
大家都穿新衣服
就是过年了
至于为什么新年要穿新衣呢?想象一下,春节去串门走亲戚,谁不愿意穿得漂漂亮亮?既献上了新春祝福,又收获了越长越漂亮的夸赞,这份油然而生的喜悦,少不了新衣服的功劳。同时,也是万象更新的意思。
◇中国红
在过年的时候,最夺目的色彩,无疑就是红色了。一到过年,整个中国几乎都会陷入红色的海洋,甚至有了一个专门的色彩,就叫“中国红”。在中文语境中,“红”可谓占尽了好处,它几乎催生了所有带有吉利寓意的词汇,红利、得宠、出名、走运……
我们常说的正红,其实就是中国红。古人以青、赤、黄、白、黑色为正色,为众色之本。五色中常引朱赤,以其色最为煊赫也。中国红乃绛红大赤之色,明艳而不轻浮,厚重而不凌厉。
在中国文化中,红色拥有极为丰富的含义。认真追溯起来,国人对于红的偏爱,五千年前就已昭然可见。
红色崇拜
红色崇拜的起源,普遍认为有三种,即太阳、火和血液。
《淮南子·天文训》言:“日为德,月为刑,月归而万物死,日至而万物生。”看到阳光下万物生机勃勃,古人便产生了对太阳的依恋和崇拜,自然而然,象征太阳的红色便备受青睐。
《说文解字》中则提道:“赤,南方色也。从大,从火。”红色也是火,燧人氏钻木取火,带来光明和温暖。而人类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更让红色成为流淌在血液中的革命基因,彰显出力量和权威。
尤其正红、朱红地位不俗,一度和“黄”一起,成为皇家垄断色。按照传统的五德与五方、五色的对应体系,皇城中的黄色属土,乃是中央之色。而红为火,土赖火生,火多土焦;火能生土,土多火晦。用红墙举黄瓦,有滋生、助长之意,亦象征稳固,表兴旺发达。
明末清初几十年,红色逐渐进入民俗,平民终于能“安心服用”。
在民俗学家那里,国人爱红还有了一套特别的解释。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种叫作“年”的吃人怪兽,体大如牛,张着血盆大口,每逢冬藏后便出来猎食,人们莫不惊恐。但后来人们发现,年兽最怕三样东西:红色、火光和声响。于是年兽出现之前,家家户户在门前挂上红色桃木板,并燃火,发出各种声响,免除年兽侵扰。久而久之,人们便认为红色可以辟邪。比如“戴红绳、穿红袜”,在心理上令人升腾起温暖、有力量的感觉,在可能遭逢的“流年不利”面前也不至于太过意志消沉。
潜移默化中,红色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特定符号。不仅仅是本命年,只要逢及重要节日,人们都要把身边几乎一切装饰成红色,用红红火火的外象驱赶走躲藏在内心的邪祟。
传统中式婚礼中,从新娘出嫁当天穿的“凤冠霞帔”,到婚礼上的装饰物、举行仪式的场所都要以红色为主基调。过年时做的年糕上要点上一个红点,婴儿满月时要做红蛋馈赠亲友,乔迁、高中之喜要送红色利是封……对于红色的崇尚,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也照应了趋吉避凶的朴素世界观。
◇中国人对年的执着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有千难万阻,过年都要回家,所以才会有中国独有的“春运”。“春节”是一个有魔力的词,无论当代的青年如何用父母唠叨、车票难买等一系列劳心费神的理由来告诉自己“春节”二字的无趣,但当日历牌上越来越近的“除夕”二字和新闻主持甜美的“今天是春运的第X天”轮番提醒你腊月余额不足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开始身在曹营心在汉,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发出号叫:“我想回家!”农民工、白领、小商小贩、学生……每一个漂泊异乡的人,一到年终,无论多远,家都像一块大磁铁一样有着巨大的引力吸引我们回去。
回家的火车上,也许你会吐槽:“过年其实没啥意思嘛,无非就是那几个过法,单调、枯燥、千篇一律……”想着想着,嘴角却不禁泛起笑容。尽管大家都说无趣,但却还是身心向往。原来过年这件事,也逃不脱“真香”定律。
★结语
传承了千百年的“过年”仪式,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年味带给我们无论身体还是灵魂那种极致的熨帖感,让我们深深着迷。同时,过年也成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情结,我们的记忆。春节,成为中国传统节日的集大成者,所有关于节日的意义在这里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过年了,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过个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