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莫斯科的“红色交通线”
作者: 王秦怡
站在山脚向上看去,郁郁葱葱的山林中依稀有一条小径。时值夏末秋初,小径上长满了绿绿的野草……这便是当年中共六大代表所走的绥芬河出入境通道“别勒洼交通线”遗址。
除了别勒洼,当时绥芬河出入境通道还有东北沟、21号界碑等处。94年前,中共六大代表中的一部分人正是从这些通道穿越国境线,秘密前往远方的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再从海参崴坐火车到莫斯科。
在这些过境人群中,有几个特殊的身影。他们不是六大代表,却往来于中苏边境,为六大代表的安全出入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是中共绥芬河国际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
“红色通道”的建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秘密召开。
“这是一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馆长王玉富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动政府,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这时的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据周恩来在六大上所作的“组织问题报告”中统计,从1927年3月到中共六大召开前夕,被惨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4万多人。
鉴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党的地方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中共中央一时难以找到比较安全的中共六大开会场所。192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不到一个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便讨论通过了这一报请。在此形势下,如何保证中共六大代表们安全出入境,成为中共六大召开的首要问题。
1896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决定由俄国在中国境内修筑中国东方铁路(以下简称中东铁路)。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中国国内路段以哈尔滨为交通枢纽,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西至满洲里,东西两端分别与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接轨。在中东铁路东线,绥芬河和哈尔滨之间有4趟客邮、货物列车往来,绥芬河成为连接中俄两国的重要通道。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不久,中共中央在中东铁路沿线建立国际地下交通站,绥芬河国际交通站以小铺子为掩护,成为中国共产党联络接头的重要场所。
在绥芬河这条国际通道上从事秘密工作的交通员们,前有苏子元、高庆有,后有赵毅敏夫妇等人。他们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感人至深。
1926年,22岁的苏子元来到绥芬河,担任光华小学校长,并在这里成立了中共绥宁特别支部,光华小学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联系共产国际的交通站。同年,高庆有受党组织委派到绥芬河开展革命活动,并在东宁组建了中共东宁特别支部,担任特别支部书记。二人不畏艰险,以小学校长、铁路职工等身份作掩护,帮助从哈尔滨来绥芬河的同志,秘密穿越国境奔赴苏联。
至1928年,“上海—哈尔滨—绥芬河—海参崴—莫斯科”这条地下交通线已经非常成熟。
当年,六大代表们往返于莫斯科和国内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经哈尔滨走西方口岸满洲里,二是经哈尔滨走东方口岸绥芬河。“绥芬河坐落在中俄边境线上,因为中共六大这次会议深深镌刻下国际红色通道的印记。”王玉富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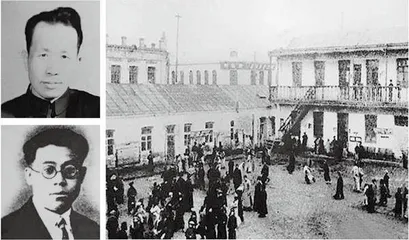

“刘老板”的估衣店
1928年春,即有六大代表陆续启程前往苏联。走绥芬河路线的六大代表,由哈尔滨乘火车到达绥芬河后,先与交通站的同志接头,一般被安排在他们的家中休息吃饭。到了晚上,由苏联方面的人带路过境,途中翻山涉水,走很长时间,一般第二天早晨才能到达苏联境内的约定地点。然后六大代表们乘火车到达海参崴,再由海参崴直抵莫斯科。当时火车是烧木柴的,这几段路程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从满洲里线到莫斯科距离更近,出境时,哈尔滨接待站尽量安排六大代表们走那条路线而不走绥芬河。但六大结束后,出于安全考虑,尽量避免走重复的路线,代表们则多从绥芬河入境。
据不完全考证,六大代表中,瞿秋白、蔡畅、龚饮冰、孟坚、龚德元等19人从绥芬河出境。周恩来、罗章龙、王德三、邓颖超、李立三、蔡畅、邓中夏、杨之华、向忠发、张国焘等51人都是从绥芬河入境。
为接应六大代表回国,绥芬河地下交通线的交通员们做了不少工作。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就是以估衣店为掩护、护送六大代表入境的赵毅敏和凌莎夫妇。
据赵毅敏的女儿凌楚回忆:“那是1928年冬天,我父亲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国,他是从绥芬河入境走中东铁路到哈尔滨,我母亲后来也经此线到哈尔滨。本来组织通知他们到上海中央局工作,我父亲也是作好了去上海的准备,可是当时绥芬河交通站的负责人资道昆受伤,急需有人去接替其工作。是去中央局还是接手交通站?当组织来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时,他没有二话,表示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当时,国内革命形势严峻,需要大批人员回国工作,与赵毅敏一同归国的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学生共27名。为什么承担这项重任的是赵毅敏?
赵毅敏后来回忆,他回国到达中苏边境格罗捷阔沃附近时,一位苏联联络站的负责人说要两三个人先到绥芬河背一批衣服过来,因为他们穿西装过境太引人注目,回国时必须穿中国衣服。
“东北冬天积雪很深,背着东西在雪里跋涉,极为艰苦。在雪里背出一身汗,风一吹,冷得要命。”这样一项苦差事,别人不太愿意去,赵毅敏却自告奋勇,“一位来自上海的老工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表示愿跟我一块去。于是,我俩过境,将中国衣服装在麻袋里,再步行背过国境。”
就这样,赵毅敏的表现得到党组织的肯定。他化名“刘老板”,和妻子凌莎受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委派,在绥芬河开设了一家叫“双合盛”的杂货铺(后改为估衣店),掩护、接应中共六大代表回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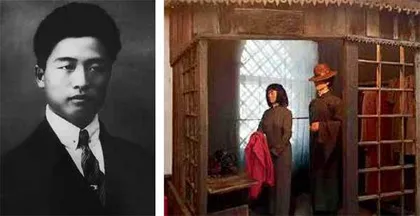
一趟危险的行程
每到夜晚,估衣店就开始繁忙起来。往来于中苏边境线的革命者,都要来这里改换行装。
小店内衣物样式丰富,有俄国人的大衣、长筒靴,也有中国传统长袍、农夫的破棉袄。一批六大代表要回国了,交通员就先把中国衣服背过国境,让代表们扮成苦力或商贩等,徒步越境至绥芬河,再安全中转回国内各地。
“有一次,在迎接代表回国的时候,赵毅敏在冰天雪地里站了24个小时,终于成功将代表们顺利送回国内。当他完成任务回家时,发现有3个脚趾被严重冻伤。”王玉富说。
与出国时不同,六大代表的回国时间安排拉得非常长,这无疑给交通站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
以估衣店作掩护,交通站还担负着回国人员路线调查与选择的重任。据赵毅敏回忆,冬天,他们踏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实地勘查,摸清敌人在何处设哨卡、何处有重兵把守,然后选择合适的地形和路线,带领回国人员安全通过。有时,赵毅敏还将自己装扮成祭奠祖坟的当地农民,在山脚下的坟前跪下,燃起香纸,才能骗过敌人的岗哨。
在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里,珍藏着邓颖超办公室1982年回复给呼伦贝尔盟政府的一封信。信中,邓颖超讲述了她与周恩来、李立三等四人从绥芬河入境归国的经历。那是一个大雨天,一名白俄交通员赶着一辆拉满饲草的马车,四人藏在饲草里,昼伏夜行,终于安全越境。因为雨太大,他们的衣服和捆在腰间的文件都被淋湿了。
罗章龙也是经绥芬河归国的。从莫斯科抵达海参崴后,他在海参崴红河子的一处小山庄停留一星期,等待越境机会。
一天,山庄主人尼考夫通知晚上起程,众人穿着桦皮凉鞋越山涉水,穿过设有障碍物的沟渠,其间还曾改穿红军制服外套,最后才抵达目的地。众人正休息时,黑夜中突然闪出一个青年向导,引他们快速步入绥芬河车站,并交给每人一张当晚西行的卧铺票及旅费、途中日用品等。
身处此情此景,罗章龙不禁雅兴大发,赋诗纪行:“紫霞吹野暮山焚,皂帽桦鞋夕进军。午夜星繁风正急,衔枚疾走渡绥芬。”
因为有了赵毅敏等人的掩护,经绥芬河出入境的六大代表们得以安全往返。为了铭记“赵毅敏”们的故事,再现这条“红色的生命线”,绥芬河市专门为赵毅敏夫妇建立了一座公园,取名为“小裁缝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