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子
作者: 南在南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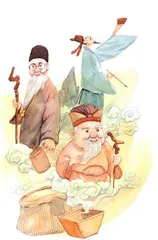
隔壁的小孩举着一张语文卷子说要请教我。他会找我,是因为有一回考试,他的语文卷子上的阅读题用的是我写的文章。他想问的也是阅读题,文章写的是齐白石的吝啬与慷慨,其中有这么一段:“汪曾祺在《老舍先生》一文中曾提到,齐老先生家里量米的竹升子都是自己保管的。每天吃饭要由他量了米才行。一大家子人,吃米不少。老先生舍不得,量一筒,手抖一下。家里做饭,媳妇就说不够,‘您再给添一点!’齐老先生就嘀咕,‘你要吃这么多啊!’然后再给量一筒……”文章后面的问题是:这一段写出了齐白石的什么品德?这孩子写了“吝啬”,老师判错,标准答案是“念物维艰,节俭度日”。这孩子觉得他写的答案至少应该算对了一半,得给他一点儿分。他问我同不同意。我点头表示同意,因为“吝啬”和“节俭”有时不好区分。不过,我告诉他,形容品德只能说节俭,说吝啬带点儿贬义。
老话说:“富从升合起,贫因不算来。近河不得枉使水,近山不得枉烧柴。”节俭从来都是美德。一合很少,大约是三两。不过,西北人很少用合来量粮食。
事情过了好多天,我没事翻汪曾祺的集子,看见《老舍先生》,细节与那张试卷上的不一样。齐老先生是量米了,但手没有抖,也没用竹升子,用的是香烟罐头。香烟罐头是老式说法,一个小圆筒,叫罐头有点夸张。我见过南方的圆筒竹升子,样子与香烟罐头差不多。
我愣怔了一会儿,升子这个东西忽然浮现在眼前。升子离开我太久了。
从前在乡下,家家离不开升子,也离不开斗。升子和斗都是量粮食的器物。虽说也有秤,可用升子来量是祖先传下来的。升子是用五块木板拼起来的,四块等腰梯形围在一起,一块正方形做底,卯榫契合。一般来说,满满一升麦子约有三斤重。木匠做升子,得用秤校,校准了再安底。还有一种大升子,能装四斤麦子。从前的礼簿里会写:某某送苞谷两升。用的要是大升,账房先生得注明。十升是一斗,十斗是一石。农家差不多都有板柜,板柜装满了能盛两石粮食,看着叫人心里踏实。从前家里来了客人,总要客气地说“打扰了”,主人家要说,“就是多加一双筷子、多添一瓢水的事情”。话虽这样说,让客人吃顿细粮才是待客之道。那时要吃细粮有些难,好些人家要找邻家去借,东家没有,找西家,总得借着。小孩儿抱着升子悄悄从后门出去借细粮。不大一会儿,细粮借回来了,小孩儿还得从后门回来,因为怕客人看到粮是借的心里不好受。
到归还时,升子里的面粉常常要堆得高高的。有一回我问祖母:“为啥借一平升要还堆得高高的一升呢?”祖母笑笑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
不过,买卖粮食时都是平升。量的人手里拿着像直尺的木条,在升子口荡一荡,把多出来的推下去,道一声:“皮薄!”这边答一句:“规矩!”
古人量酒时用斗,“李白斗酒诗百篇”。也有用升的,元稹就写过“偶然沽市酒,不越四五升”。奇怪的是买卖布匹时也用升,据说八十缕线为一升,想来怕是窄窄的一绺儿。
升子除了本身的用途,在乡下还被用来替代香炉,祭祖时用。在这样的场合,升子有点像礼器。乡下人家敬土地爷时也用得到升子。土地爷大约有很多,孙悟空朝地上打一棍子,就能跳出来好多位。我们那儿的土地庙很寒酸,几块砖,几片瓦,就成了庙。放个旧升子,装满玉米,再烧三炷香,人们就能请土地爷保佑庄稼丰收。有的人家还要请土地爷帮忙照看鸡鸭,别让老鹰给抓了,并保佑跑掉的猫能够回来……我读到一篇文章,写楚人围攻齐国,齐威王准备了一百斤黄金、十辆马车当礼品,让淳于髡去赵国搬救兵。淳于髡大笑,齐威王不解。淳于髡说,他笑是因为来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个农人,拿着一个猪蹄和一杯酒,祈祷说:“高地上收的庄稼堆满谷仓,低田里收的庄稼装满车辆……”他是在给齐威王打比方。
好像也没什么可笑的,乡下人家敬土地的用心的确不在于供品。农人自己寒暑耕作,不敢懈怠,敬土地爷,是诉说,也是寻求陪伴。
( 本刊原创稿件, 勾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