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阿勒泰
作者: 马宇平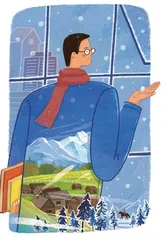
10年前,我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第15届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在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区支教。
“你们那时骑马上班吗?”“住毡房吗?”……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后,很多朋友向我抛来这些问题。
我们支教的地点不在牧区,也不在景区,而在阿勒泰市。就是这座只有一条主干道,“一个馕饼从北滚到南”的边地小城,成了我们回忆阿勒泰时最美的地方。
我现在还记得上第一堂课时的场景。我的学生近一半是哈萨克族,他们会讲哈萨克语、汉语和英语。我的学生勒布朗·冯——这是他给自己起的英文名,当他得知我从天津坐了6个小时飞机来到阿勒泰时,一脸严肃地说:“天津真是太偏僻了!”
他来自布尔津县,在额尔齐斯河畔长大。大学毕业后,勒布朗回到阿勒泰,当了一名老师。不久前我看到他的微信朋友圈,说他指导的学生参加信息竞赛获奖了。
在阿勒泰待了一年后,我在某些时刻理解了他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我那时教高中两个班的英语,每周上17课、备17课,做梦都是在讲台上暴走。夏天,我们最多的娱乐活动就是散步。眼前的克兰河,先汇入额尔齐斯河,然后一路向北,最后奔腾流入北冰洋。我第一次感觉,世界的版图都随着这条河徐徐展开,它给了我比蓝天更具体的辽阔感。
阿勒泰的热总是一闪而过,冷才是她的底色。
每年10月,阿勒泰开始飘雪,差不多要到来年4月才结束。每到冬天,连着几天飘雪,建筑物、路标只高出地面一点点,整个城市好像矮了一截。
我的学生告诉我,每个阿勒泰的孩子几乎会走路时就学会了滑雪。而我,在21岁时才终于站上了阿勒泰的雪道。
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我第一次挑战中级道,尽管做足了准备,但我还是腿发软,牙齿也跟着打战。这时,我看到一个捂得严严实实、个头儿高高大大的人向我挪来。他走近后我才发现,那是我们班的班长,1.9米高,平时待我很冷淡,我经常仰着头批评他,他则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在雪道上,他站在我身边,微微猫着腰,给我强调着技术要领。然后他拍着手鼓励我:“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然而,我的这一滑简直是“史诗级灾难”,因为速度快,转弯角度过大,重心太靠后,我连人带板一起摔了出去。摔得倒是不疼,就是觉得太丢人了。
我们班长比教练更快地来到我旁边,一边帮我拍打身上的雪,一边调侃道:“以后再别吹牛了,手刹都用上了。”
那一刻,我既感动又愧疚。在讲台上,我自诩为老师,教人语言的规则;在生活中,却应该拜学生为师,学习为人真诚、豁达之意。
在这天远地远的“苦寒之地”,总有很多年轻人前赴后继地赶来。
学校有一名年轻的地理老师,毕业于四川的一所高校。他拉了一个行李箱,坐了48个小时的火车从成都到乌鲁木齐,然后坐12个小时的大巴到阿勒泰。4月的天气还是挺冷的,他试讲的时候穿着一件黑棉衣,试讲的内容是《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因为试讲要求是学生学到哪里,教师就要从哪里接着讲下去。
学校安排年轻老师互相听课,我在他的课上听他给学生讲:“像我们国家,北有冰原,南有大洋,西连大漠,东接大海,这才是大国。”
他决定留下来,留在这个大国的角落里。这个“冷门”决定的背后,是发自内心的热情。他说:“来这里是不错的选择,人生本来也没有最好的选择。”
10年了,有人回去过,有人再没回去;有人想回去,也有人再也回不去了。相比一生驻守那里的同事们,我们这些支教老师做得太少,收获得太多。
我们的一位团友说,阿勒泰冷得刚刚好,那里的青春多少年后拿出来都是新鲜的,那里的人必须活得很热情才能打发岁月。每到下雪的日子,去过那里的人都会想起她。
阿勒泰,我们常常会想起她。如果再去一回,我们想做得更多。
(月和叶摘自《中国青年报》2024年5月20日,与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