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的十种兵器
作者: 许晓迪
下午3点40,作协8楼的办公室,窗外一朵云飘过,遮住太阳。屋里瞬间暗下来,摄影记者一下坐直了身子。作家邱华栋笑:“以为飞碟来了是吗?”
他是一个抓取意象的高手,自1992年来到北京,面对剧烈变迁中的庞大都市,水银泻地般写下一篇篇城市小说。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他是报社记者、杂志编辑、小说家、诗人、武人、藏书家、书评人、作协领导……仿佛身怀十种兵器的高手。
18岁走出新疆昌吉,邱华栋感念自己的语文老师。他原名邱华东,高二时,语文老师说,你又不是上海人,叫什么“华东”,加个“木”吧,以后姓李、姓杨的都会帮你。改名后两个月,武汉大学的保送通知就来了。后来,他也常给人测字、改名。
他还有一位难忘的语文老师,叫黄加震,平日除了教课,还在业余体校武术队做总教练。邱华栋跟着他,学了6年武术。2016年夏天,他去拜访黄老师。老先生将收藏多年的兵器全拿出来,长刀、短刃、明器、暗器,加起来上百件,摆满一屋子。师徒二人来到楼下花园,70多岁的师父,一个弓步,将青龙偃月刀一横,单手举过头顶;换40多岁的徒弟上,一个弓步,几秒后,大刀哐当落地。
想写武侠小说的念头由此而起。于是有了《十侠》,从春秋到清末,邱华栋将10位侠客的故事揳入江湖与庙堂之间,在真实的历史现场开掘侠之奥义。
“每个中国人身上都自带侠气”
开篇《击衣》,写的是春秋晚期刺客豫让的故事。
这是一个老故事,《史记》《战国策》《吕氏春秋》中都有记载。三家分晋,赵襄子杀了智伯瑶,门客豫让为报答知遇之恩,潜伏在仇人身边。改名换姓,身上涂漆,让皮肤长满恶疮;吞下火炭,将嗓子烫哑。
邱华栋笔下,司马迁三四百字的叙述,有了一番当代人的阐发。豫让第一次刺杀失败,史书中没有细节点染。而在《击衣》中,邱华栋让豫让埋伏在厕所,一边假装清洗池子,一边听着赵襄子解决内急的声音:“他蹲在那里,这时我就出手,实在不是一个剑客能做得出来的,我一定要等他拉完屎出来净手的时候再下手,才算是有礼有节。”这是一个蠢笨的刺客,生死存亡间坚守某种不合时宜的尊严,却是中国文化谱系中最为血气丰盈的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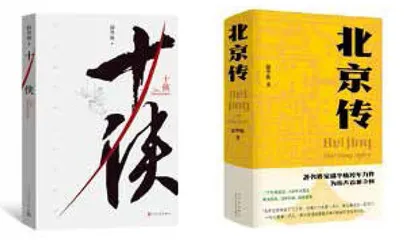
小说最后,刺杀失败的豫让恳请赵襄子脱下外衣,以剑刺击华服。赵襄子长叹,答应了:“这样保全了你的忠,也体现我的义。”豫让挥舞短剑,三跃三击后,将双剑一横一竖,一抹一刺,自杀而死。“这样一来,赵襄子和豫让都变成了侠客义士。”邱华栋说。那是中国最年轻天真的时候,人人都是侠客,强大的精神漫过衰亡的肉身。
邱华栋喜欢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有北宋、西夏、大辽、大理的历史版图,《鹿鼎记》将韦小宝植入《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现场。这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笔法,也成了《十侠》的大招。
比如《龟息》,讲乌龟的呼吸。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气功热风行,邱华栋那时学武,也曾对着太阳、月亮盘腿而坐,呼吸吐纳练内功。很多年后,他在南美一个动物园看到一只大龟,直立起来一米八高,于是有了小说里身后跟着一群陆龟、水龟、石龟、草龟、白龟、褐龟的300岁高士,最后用药丸毒死了暴虐的秦始皇。
很多故事的灵感,都来自邱华栋的生活和阅读。有一阵,他研究唐代建筑,得知一种名为“间壁”的密室,就在《听功》中将一位耳力出众的“双面间谍”藏在其中,用“顺风耳”探听唐太宗换立太子的奥秘;读完《宋徽宗传》,对这位“文艺皇帝”产生兴趣,就在《画隐》中安排一个刺客潜入皇家画室,用缩骨术缩成一块山石蹲在画里;读《忽必烈传》,写到一场佛道两家的御前辩论,就在《辩道》中设置一场“华山论剑”,各个门派幻术迭出,如同《西游记》中的“车迟国斗法” 。还有一次在公园中,他看到几个人在玩绳子,就在《绳技》中虚构了一对卖艺父女,用一根长绳帮助兵败的建文帝逃出生天。
《十侠》里,邱华栋写的不是刀光剑影的江湖,而是正史背后明灭难辨的地带。自春秋至明清,侠客作为一种民间力量,不断被庙堂的权力中心打压。最后一篇《剑笈》,邱华栋让旋风派的剑客把武功秘笈进献给了编修《四库全书》的纪晓岚,“如果有这样一本书,在清代恐怕也是被烧掉的下场吧?”
《十侠》里侠客们的结局,大多是深藏功名、隐遁江湖。这也是武士阶层的真实命运。这两天,邱华栋在看纪录片《藏着的武林》,从甘肃山旮旯里练长枪的放羊人到西安小吃街上每晚打烊后对打切磋的小老板,他看得新奇,而后释然:中国功夫还是很厉害的,不是所有武术家都是“耗子尾汁”的马保国。
武林是“藏着”的,侠客在民间,却如同一个幽灵,盘旋在普通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中。“它和西方世界一切按法律来的契约精神不同,是一种道德承诺,是日常生活里的除暴安良、扶危济困、见义勇为、担当信义。”邱华栋说,“每个中国人身上都自带侠气。”
从天山脚下到樱花树下
15岁那年,邱华栋写过一部武侠小说,16万字,叫《碧血侠情录》,讲清朝的一群江湖侠客。
80年代,武侠小说风靡,《少林寺》热映,掀起年轻人习武狂潮,新疆昌吉街头,半大小子们斗殴打群架,释放青春荷尔蒙。邱华栋看完《少林寺》,就跑到业余体校,参加了武术队。
训练很苦,早上一个多小时,下午放学两个多小时,晚上练完回家,累得吃不下饭。文武双全的黄加震老师,“拿着棍子往那一站,非常凶残”,经常把他们揍得鼻青脸肿,头上都是包。
压腿、劈叉、站桩、马步、冲拳,基本功练了一年多,才是套路和器械。邱华栋个子不高,人胖胖的,选了广东南拳,打起来虎虎生风。
器械,他练的是单刀,至今挂在家中,一米多长,放在黑色皮套里,时不时拿出来练练。武术比赛用单刀,刀片薄,抖起来哗啦作响,表演性大于实战。他这把,刀刃厚,发不出声音。
“经过武术训练,人有一种韧劲。练排打,憋足气各种挨打,忍耐到底;3米高的墙,从助跑到扒着沿儿翻过,3秒钟必须完成。”邱华栋说,练武给了他一副结实身板,初中时,他和一些朋友骑着自行车,穿越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还有几次向着天山深处进军,白天披星戴月,晚上睡在河边的睡袋里,从石头山、草山、塔松山林,一路而上,直到雪山之巅。
昌吉,一个天山脚下的小城市,一抬头就能看到5548米高的博格达峰。邱华栋每天面对雪山,读着西部边塞诗,很快开始模仿大人的腔调写作——一部模仿金庸和梁羽生的《碧血侠情录》,十几篇以汗血马、雪豹、火狐狸、黄羊等为主角的动物小说,还有几百首诗。那时,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在下面激情澎湃地写诗,数学成绩一塌糊涂。
1988年,邱华栋的中短篇小说集《别了,十七岁》出版,一夜成名,如同后来的郭敬明和韩寒。那一年,他19岁,因数学太差,考名牌大学无望,看到一些名校破格招收少年作家的消息,把作品整理了几份,直接邮给了北大、武大、南大、复旦的4位校长。
最终,武汉大学录取了他。那时的武大,走出了王家新、池莉、方方等作家,各地诗人来串联交流,熊召政、野夫、廖亦武等从四面八方进入作家班。邱华栋是文学社的骨干,每年3、4月,在樱花树下组织诗歌朗诵会。他组织大家看翻译作品,这个星期读海明威,七八十篇看完,模仿海明威写一个短篇;下一星期读博尔赫斯,读完后再写一个短篇。
武大的宿舍条件差,一个屋挤八张床,没有阳台,也没风扇,武汉夏天酷热难耐,就多跑几趟东湖游个泳。物质清苦,但精神高昂,每个人都操心着时代的大问题,都有几个笔友书信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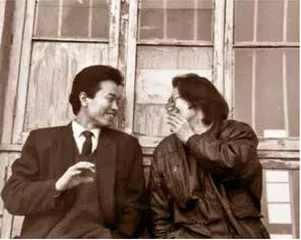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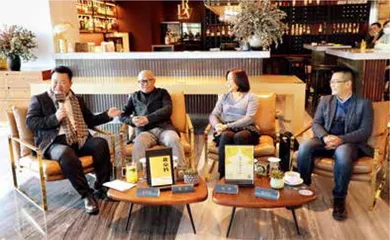
1992年,邱华栋大学毕业,同学们抱头痛哭,喝得大醉。正是从这一年,武大校园盛开的樱花,开始对游客收费——中国社会开始迈入市场时代。
吞吐一切,消化一切,记录一切
那一年7月,邱华栋被分配到北京市经委下属的一个人才开发中心,住在什刹海附近的办公室。十个蛇皮袋子的书,被他一袋袋背上了五楼。
报到后,单位安排他去怀柔黄花城的水库规划一个培训中心,每日忙着征地、盖房、和农民谈判,没事时就爬到附近的长城上,手搭凉棚,瞭望北京。到了周末,他回到城区,在后海边溜达,去郭沫若故居里的亭子边读书,或者躺到老辅仁大学的槐树下看报。
一年后,邱华栋去了《中华工商时报》做记者,报社在亮马河一带,那是90年代北京最热闹繁华、光怪陆离的一片。他不停地搬家,像牧羊人一样,拖着一袋袋书,贴着墙一本本往上码,摞成一堵墙。
白天,邱华栋为抓新闻满世界跑。他曾和一个河南来的拾荒者生活了一天,晚上回到住处,在那间7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老人拉开布帘,木架上摆满了空香水瓶,那是他的收藏,足有200多个。他也曾跑到圆明园采访,那里汇集着一群流浪艺术家,有人住在公共汽车下面,有人住在平房中间的过道里,面如菜色、灰头土脸,却两眼放光,一脑袋稀奇古怪的想法。
到了晚上,他带着城市中的各种消息回家,趴在桌上写成小说。1995年,《上海文学》推出“新市民小说”栏目,第一篇就是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小说里,几个外省青年来到北京,驱车而过,看到的是“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一座座摩登楼宇。他们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 野心勃勃地展开个人奋斗,梦想与腥臊共存、热忱与窘迫并举。
那些年,邱华栋在文学杂志上频繁亮相。他的本子里列着密密麻麻的写作计划,完成一项就用红笔打个钩。评论界给他贴上了“新生代”“晚生代”“后先锋”种种标签,称他是王朔之后“城市文学”的代言人。
邱华栋的北京,没有老舍笔下胡同、四合院的文化乡愁,也没有王朔那般贴身刻骨的大院记忆与顽主故事。他的北京,是“一座满镜子的迷宫”“黑暗之中的灯光之船”,是各阶层“闯入者”的奋斗秀场,将一个个大学毕业生、流浪艺术家、诗人、小报记者、小商人、打工妹、白领,改造、异化为“时装人”“广告人”“直销人”“蜘蛛人”“化学人”“电话人”“钟表人”“持证人”“平面人”“新美人”……
作家刘震云说,别的作家写的是“故”事,邱华栋写的是“新”事:“他能迅速把眼巴前发生的新事,迅速放到他的小说里。当代社会变化多端,像一杯浑水,澄清需要时间,但邱华栋等不得。这个好与不好的浑浊和新生,也许更加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