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娜
作者: 张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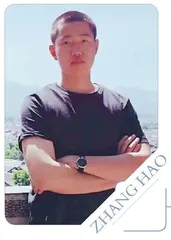
一
在通往海市的大巴上,塔娜就憋闷得难受,她想,还不如骑马去来得自在,可是爷爷不放心:“又不是成吉思汗的时代,现在哪有跑马的驿道,再说你就是真的骑到了城里,又把马拴在哪里?拴在公交站吗?”
“唉,麻烦死了!”
每次去海市,都要走好远的路,到旗客运站挤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排队,再钻进这个“大闷炉”里,一路上发动机嗡嗡嗡地叫,晃晃悠悠,晕晕乎乎,车里总有一股机油的味道飘来飘去。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塔娜脑子里总会蹦出“黑色”这个词。她觉得生活就是停留在各种色彩里,嘈杂憋闷就是黑色,宁静祥和就是藕荷色……司机头顶的小电视在播放很老的武打片,看不懂,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在那一个小方框里,呼呼哈哈地叫喊,莫名其妙地大笑大叫。
为什么不买个小汽车呢?唰的一下就到了,多快,多舒服。可额吉却不让阿爸买,她总是听到谁谁谁喝酒开车被逮了,谁谁谁开车撞到了一起,总之她认定开车就要出事,塔娜就一直坐不上小汽车。
塔娜睡得迷迷糊糊,被车颠醒了,她把车窗敞开一条缝隙,冷空气嗖嗖地挤进来,凉意从鼻孔钻入大脑,瞬时精神了很多。蓝色的窗帘被人拽坏了,挡不住阳光,透过玻璃,烤在脸上。她眯起眼睛,看着雪开始融化的地方,初春的枯草被太阳照得金光灿烂,裸露的土地上好像也泛着一层油光。光线在天空下延伸,好像一朵金色的蒲公英,迎着早春的北风,在大地上四处飞散。
风景在窗边变换延展,之前一片雪白的大地,开始有了不同的色彩,现在是春天。
虽然是初春,还是会时不时下雪,天气依旧很冷,但正午的阳光照在大地上,晒得身上暖融融的,让人几乎忘了寒冷。
车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塔娜看到一栋灰黑色水泥建筑,突兀地立在草原之上,四周除了这栋丑陋的建筑什么都没有。它就像是被遗弃在这里的实验品,估计连它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出现在人世。
“它这样躺了好久了吧?”
塔娜穿着新做的紫红色袍子,做之前额吉说,哪有小姑娘穿老姑娘的颜色,多老气!塔娜说:“我才不管,上次伊利奇姐姐闺蜜出嫁,我去看了,新娘子就是穿的紫红色的袍子,系着彩绣的腰带,可带劲了!我就要穿!”
现在她穿着新袍子,手缩在袖口里,脸围在奶白色的围脖里,感觉自己在灰灰黑黑的人群里格外显眼。
乳白色的靴子也是新做的,漂亮,厚实,合脚。手工鞣制的软皮,靴帮上绣着蓝色的盘肠纹。穿上它在雪地里走,只见雪在脚后跟轻轻扬起。踩在雪上嘎吱嘎吱响,就像是小孩偷吃饼干的声音。
想到这些,塔娜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她合上眼,又睡着了。
二
塔娜这次要去城里的姨妈家,带去额吉新做的奶干和肉干。
与她同去的,还有一只刚断奶的小猫咪。这次家里的猫咪花花生了五只花色不同的小猫,姨妈要了一只小橘猫。
因为猫咪太小了,塔娜只好把它装进书包里,但是小猫脱离了熟悉的环境,害怕得发抖,在黑暗中瞪着溜圆的小眼睛,带着困惑的神情喵喵叫,几声低几声高,车里的人听到声音都看向塔娜。她有些不好意思了,就伸手进去,把小猫搂在掌心,轻轻摇晃着安抚小猫,嘴唇嘬着发出呜呜的长音。塔娜的手很暖,小猫不一会儿就合上眼睛睡着了。
额吉说,要好好和姨妈聊聊学习的事。之前是借读,这次开学,塔娜就正式转到海市上初中了,姨妈是语文老师,以后塔娜就借住在她家里。
塔娜对学校说不上是什么感觉,但是额吉执意要送她去海市上中学。额吉说了很多很多,什么起跑线啦,不能耽误啦,一辈子的事啦,塔娜没怎么听懂,她只是对未知的新生活有一些好奇,但又没有特别期待。之前转学报到那天,有的孩子紧紧攥着大人的手,眼泪汪汪,只有塔娜是自己一人报到的,姨妈还要去带班级队伍,嘱咐几句就走了。塔娜觉得自己一人也没什么,不明白有的孩子为啥要哭。额吉走之前说了,长着一张嘴,立着两条腿,不懂就问,能走就走,大姑娘了,没什么怕的,所以塔娜一直都是一个人跑来跑去。
这次她又路过学校,现在是假期,大门紧闭,她停下来,隔着围栏,看着空无一人的操场和教学楼,感觉怪冷清的。
她想起放假前,有一天教室里突然蹿进一只灰黑色的大耗子,同学都在大声尖叫,有的还站到了凳子上。这有什么啊,塔娜觉得莫名其妙,城里人啊,都爱大惊小怪的,草地上耗子多得是,有什么可怕的。她甚至觉得耗子胖乎乎的挺可爱,她想都没想,就一手抓住了耗子,提着它的尾巴把它扔到了外面。
这下塔娜成了学校里的名人,同学遇到她,都会说,这就是徒手捉老鼠的那个。塔娜很想说,她叫塔娜,但她向来不在乎这些小事,随便吧,叫什么都好。
她觉得大家都在为了什么事发愁,班主任看着他们上自习时,总会用一副闷闷不乐的神情望着窗外,好像要望到很远的地方似的。身边的同学们用手挡着嘴悄声说话,很多词语飘到塔娜的耳朵里——“喜欢”“帅”“爸妈”“烦人”“出去”“逛街”“炸鸡”“篮球”……有人在哭,有人在笑,说不完的故事,道不清的烦恼。塔娜的世界没那么复杂,她甚至觉得,每天的生活都会像风一样四处流动,快乐与忧愁,都会不断飘走。每天早上,当她被和煦的阳光晒醒的时候,她就会真切地感受到幸福。
三
塔娜总会想到,班上那个叫海日汗的瘦弱男孩,经常受欺负,他的爸爸很早就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体育课上,他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操场上溜达,这时候塔娜总会凑上去说两句话。
“我说,海日汗。”
“嗯?”
“你想爸爸吗?”
“那是啥感觉呢?我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梦到过爸爸?”
“我忘记爸爸长什么样子了。”
……
听到这话,塔娜突然觉得自己也有些记不清奶奶的样子了。虽然奶奶才去世两年,但留存在塔娜记忆中的,更多是奶奶的味道、暖融融的声音,以及依偎在奶奶身边的触感。
奶奶走的前两天,塔娜一直陪在身边。她喜欢握着奶奶的手,像抚摸着覆盖柔软苔藓的棕色树干。奶奶的手那么有力,瘦硬中有柔软,里面好像有树液在缓缓流淌。
她想让时间永远在这一刻停留,和奶奶待在一起,哪怕化为石像。
在世的时候,奶奶总会点着圣祖像前的小油灯,把家里的东西擦得发亮,一刻也不闲着。每天早上,塔娜都是被奶茶的香味唤醒的,奶奶用木勺哗哗地搅拌奶茶,这时塔娜的心里就像被某种柔软的东西抚过一样。奶奶身上有一种好闻的味道,混杂了檀香和奶香,还有一种老人特有的味道,闻起来让人安心。大白猫可着劲儿往奶奶怀里拱,睡得天昏地暗。
在这之前,塔娜对生死没有什么概念,也不会为了奶奶终有一日会离开感到悲哀。现在,塔娜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她深爱的人从生活中消失,那种思念是什么滋味。
葬礼那天,塔娜没有哭。因为她觉得奶奶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与她同在,只是自己没法靠在奶奶身边了。她看到奶奶躺在那里,合着眼睛,颧骨高耸,没有笑,也没有绷紧了嘴,像做着一个长梦。有好几次,塔娜认为自己看见奶奶的眼皮微微颤动,但是心里却有个声音告诉她这不可能。
她想,这是我和奶奶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奇怪的是,塔娜只会在梦里哭。也不知为什么,她和奶奶躺在毡包里,毡包顶是敞开的,夜空被装进一个小小的圆圈里,她们仰望着浩渺星辰,奶奶的一头银发也如月亮般闪着银光。
奶奶说:“娜娜,奶奶搬家了。”
塔娜望着奶奶,没有言语,只是默默地泪流满面。
有时她坐在草原的山包上,想着奶奶会去什么地方,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人都到了哪里。爷爷说奶奶会再回到人世,那奶奶是化成一粒种子,随风飘落到另一片草原上,再一次生长出来吗?
还是说,奶奶会随着额尔古纳河的河水,流啊流,流到北冰洋?
北冰洋那里,应该很冷吧!
老去的大黑狗也会到同一个地方吗?还有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最后又会去向何处呢?最终大家都会在一处团聚吗?还是像蒲公英种子那样,随风散落天涯?
但草原不会回答,日头隐没,紫霞沉落,夜风一遍又一遍地吹动野草,沙沙沙沙……
四
上学时,她还是经常会想起在草原上的日子。
暑假里,她去宝日希勒,住在哥哥家里。她的嫂子是哲盟人,保留着老家吃饭的习惯,大早上就起来炸酱,做饭包,焖米饭。
清晨六点,塔娜就被热腾腾的饭香唤醒了,她越是想睡,香气就越是源源不断地飘过来,最后她放弃抵抗,从炕上爬起来。
“唔……我们的大姑娘起床了。”
嫂子的声音透亮,她有着小麦色的皮肤,脸颊微微泛红,带着一点点雀斑,和本地白皮肤的布里亚特人很不一样。嫂子说那是小时候帮家里干活晒的。她总是一刻不停地收拾打扫,塔娜好想说,嫂子,歇歇吧,躺着多舒服呀。但塔娜看到嫂子似乎很开心,总是一边干活一边哼着歌。塔娜觉得,也许这就是嫂子的快乐。
要是在家里,她习惯吃刚烤出来的面包,然后涂上西米丹和稠李子果酱,再喝上一大碗奶茶。但是嫂子家的早饭就和午饭一样实在,她吃不动,就把桌子上酸了的奶子拿过来,拌上砂糖和炒米开始吃。
盛夏时节,天总是亮得很早,牛时不时地哞哞叫。吃过饭,她就和嫂子一起去挖草药,采山丁子和稠李子。
当塔娜裸露的脚踝蹭过野草时,也带下了叶尖上还未干透的露珠,她索性脱下鞋,拽下袜子,赤着脚,被草叶扎得酥酥麻麻,冰冰凉凉。
她们走到一处没有草皮的裸露沙地,塔娜躺下来,背部感受着热沙的炙烤,透过手指的缝隙,眯着眼睛望向太阳。云彩像羊群一样在天空中肆意奔跑。
她的视线越过河上泛起的银光,落在远处寺庙的白塔上。白塔好像触手可及。但蹚过一条又一条的河流,你会发现它还在远方伫立。
望着无边绿地,塔娜突然想到:
“大海是什么样呢?会像蓝色的草原吗?”
五
这次见姨妈,感觉她好像老了许多。她还是一个人生活在一栋大房子里。
姨妈说:“哎哟我的大姑娘,让姨妈好好看看你。”
小猫从包里钻出来,认真地打量着新世界,东嗅嗅,西嗅嗅。
姨妈忙着做菜招待她。她觉得自己懂得姨妈的心,但她不知道如何去说,她们俩谁也没有按照额吉安排的剧本去说,聊家里亲人的杂事,聊猫咪,就是没聊学习。
她知道,姨妈已经很累了,但如果不去安静地享受姨妈为她做的一切,姨妈就不会心安。
天色未黑前,塔娜和姨妈道别,坐上回去的班车。
客车像追赶着刚刚爬升的晚霞一样,驶向无边旷野,窗缝传来尖细的风声,车上的人都昏昏欲睡,残留的日光钻进来,从人们的脸上扫过。路边是正在归棚的牛群,慢吞吞地走,斜眼看着公路上鸣笛的汽车。
离开海市不一会儿,夜色便像浓雾一样散开,看不清是开向哪里,这条路显得无比漫长。
塔娜做了一个梦。
梦中的场景没缘由地变换,家里终于买了小汽车,额吉还是叉腰叹着气,阿爸喜滋滋地钻进车里。她本想开门,但是不受控制地踮起脚尖,停在车顶,接着蹦向半空,越飞越高,在云端俯瞰着小车、城市和草原。
然后她像失重般坠落,掠过云层与飞鸟,眼看要摔在草地上,却又被一股柔和而有力的气流托起,慢慢地降落。
眼前有一个用玫红色丝巾遮住面孔的少女,立在草原上,唱着哀戚的长调:
白嘴鸦离巢
会飞往何处
远嫁的姑娘
正去往他乡
河水流淌着
不知道方向
“河水流淌”“河水流淌”,这一句就像流淌在脑子里一样,在梦里面摆脱不掉。
梦里面的天空是暗色的,只有少女看起来如此真切,不断有亮光闪烁、消失。
“我是来到了梦和现实的缝隙里吗?”
那些不时闪烁的亮光,好像夜色里车窗边闪过的车灯,让她分不清究竟是梦着还是醒着。
她觉得那少女像自己,又不是自己。少女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为自己而歌唱。
一时间,她感到人世间的不真切,不知身处何处。世界开始模糊了,连同她的意识一起,飘向无比神秘又渺远的地方。好像星空,好像月亮,此时没有快乐,没有悲伤,只有少女远去的一点背影,像月轮边的淡淡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