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鸣村庄
作者: 石红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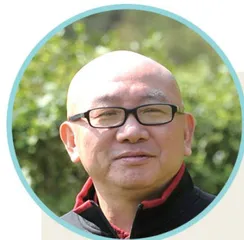
石红许,江西鄱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饶市文学院总编辑、市作家协会主席。散文见诸各种文学选本和《散文》《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美文》《福建
文学》等文学期刊。著有散文集《河红万里》《风语西河》《山河新雨》等。曾获刘勰散文奖、吴伯箫散文奖、中国徐霞客游记文学奖、首届中国红高梁文化散文奖等。

一只只大雁飞来鄱阳湖畔过冬,每年不远万里地如期而至。一座座村庄就这样被雁鸣包围。雁群不断变换队形,以“人"字形为主,每队十几只、数十只不等,像是在村庄的上空彩排。秋收时,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在田里留下一些稻穗,为回归的候鸟接风洗尘。
每年这个季节,我都会回到鄱阳老家住上几天。回到家乡,感觉是那么的踏实。寂寥的田野少了其他季节的郁郁葱葱,飞翔的翅膀填补着天地间过多的虚空。雁影穿梭,“嘎…”,一声声雁鸣汇合成激越有力的大合唱,令人振奋。仰望天空,我感觉它们是在以老带新练习飞翔,又像是在进行一次次不会厌倦的演习。我试图追随一支大雁的队伍,去探寻它们的归处。可雁群仿佛早已洞察我的心思,不一会儿就飞向了天边,再也找不到。天空辽远,带走了我的遐想正迟疑,天空又飞来一行大雁。它们一字排开,鸣声开路
一日上午,朔风呼啸,我紧紧衣领,又一次走向野外。沿着村前的一条水渠,我向着田野深处走去,头顶上空是一群纵横飞翔的大雁。收割后的稻田里,排列着一株株禾蒐,一大片一大片的,显得非常有气势,仿若坚守岗位的卫兵。我穿行在枯黄稻草的馨香里,像一个活动的感叹号,追踪羽翼末尾的喧杂。
拐上一条新修葺的乡村公路,我来到一座小庙宇前。翠竹掩映、雁鸣覆盖,给它增添了几分禅意。蓦然间,我发现庙宇旁的小河对面的稻田里,像是有成群结队的灰鸭在优哉游哉,思忖那是人工养殖的鸭子,却纳闷它们似乎个头更大。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绕到河对岸近距离细看。我就像个摸到敌后的特工,悄悄靠近。突然,那群灰鸭扑棱棱地腾飞而起。我这才发现原来它们不是鸭子,而是可爱的大雁。我有点懊恼自己不经意间打扰了大雁们的岁月静好。我就像小时候一样,希望能有在草丛里发现一颗鸟蛋的欣喜。
那大片低洼的稻田蓄积着浅浅的水,正是大雁们的最佳栖息地。它们在那里追逐嬉戏,寻找小鱼、小虾和螺蛳吃,享受着世外桃源。鄱阳湖平原上的稻田一丘连着一丘,几十、上百乃至上千亩成片。冬季的稻田几乎无人劳作,大雁就把这里当成了理想的家园。偶有人来,它们便起飞挪到另一个地方继续聚集。它们也会不时提升飞行高度,翱翔在村庄的上空,巡视、探寻、捕捉。我貌似找到了大雁好动的原因。
一条长长的圩堤环抱着村庄,堤外是汇人鄱阳湖的河流,万羽齐翔,这是人鸟共同家园的美好见证。冬季鄱阳湖畔的村庄是音乐的村庄,被雁鸣、鹤唱、鹅歌环绕。那仿若多声部演绎的音乐会,回荡在田野,与滔滔鄱阳湖水交织,谱写出冬日动人的乐章。老家人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恢宏热闹的场面一“鹅嘶雁叫”,每天晚上都是听着这一天籁进人梦乡。
鄱阳湖的不少鸟儿并不惧人,日日夜夜在村庄的上空盘旋,在村庄外的田野上栖息。除了大雁,村庄外更远处还有白鹤、灰鹤、天鹅,以及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候鸟一—老家人统称为“野鸭子”。当然也有留鸟,诸如乌鸦、喜鹊、八哥,在这片大地上生活鄱阳湖水肥草美,哺育万物苍生。
一只只精灵在纵情施展向上、侧翻、平滑、俯冲、旋转等飞翔技巧,如剑如光,时而呢喃,时而高歌;时而耳鬓厮磨,时而乍起纷飞。它们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等地起飞,长途跋涉,只为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生存,只为完成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回归。一片羽毛飘落,如船儿浮在水面,载着满月和晴朗、霜雪与雨露,告别艰难险阻,告别旧的一轮寒冷,去向来时的故乡。它们穿越大半个地球,带着斑斓的梦想,向着熟悉的水草气息,向着涂抹暖色的阳光,是使命,也是不变的承诺
在这儿,若遇见受伤的鸟儿,村里人都会悉心呵护、精心疗伤。身穿迷彩服的护鸟队日夜巡逻,清障、观测、拍照、记录,是行走风景中的风景。对于鄱阳湖湿地的每一个滩涂港汊、每一处草洲、每一片芦苇荡,护鸟队都如数家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鄱阳湖的怀抱足够宽广,足够鸟儿群起群落地回旋,足够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圩堤外的草洲上,大雁、白鹤、白枕鹤、白头鹤、灰鹤、小天鹅、东方白鹳、白琵鹭、黑翅长脚鹬、鸿雁、豆雁、黑腹滨鹬、野鸭等,是大自然的恩赐。鸟鸣声声,悦耳动听,温润地漫过心灵。走在故乡的大地上,我的心是如此的安静。
这样的野外行走常常使我乐不思蜀,直到手机响起,家人喊我吃饭,我才缓缓地折返村庄。路上不时有埋伏在稻田的一小群大雁起飞,像是一个个未知的惊喜在等候我经过。
“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停留在稻田、河汊、港湾的鸟儿,无论是低头寻觅,还是散漫游走,又或是挺起胸膛仰天长啸,身影如昨日、如未来。
我恍然,我与它们都是鄱阳湖的故人,一生都在练习告别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czsz20250801.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