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写诗的孩子不砸玻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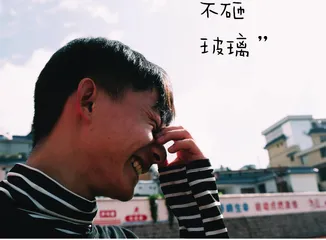
“放学回家的路长长的/只有我一个/家里的牛圈大大的/只有小牛一头/当我抱住它的时候/我们都有了朋友。”
写下这首诗的,是云南省漭水初级中学的学生施应锁。
2020年,央视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第3集《长大》,讲述了云南省漭水初级中学一群留守少年与诗歌相遇的故事。他们捕捉自然,透过云层,透过大山,看到远方。他们用诗歌盛放青春的心绪,记录成长的烦恼。
201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已有2年支教经验的康瑜创办了“是光诗歌”公益组织,将四季诗歌课程普及到偏远的乡村学校,云南省漭水初级中学便是其中之一。诗歌让孩子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校长于春云对康瑜说:“之前孩子们有什么愤怒的情绪,都会砸我的玻璃,现在就砸得少了。但是他们会写一首愤怒的小诗,塞到我的门缝下。”
即使有诗歌课程,很多留守少年仍然考不上高中,诗歌也不能换来在外务工的父母的陪伴。然而,在淡淡悲伤的底色上,覆上了一层明亮的色彩——
“诗歌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但它有可能改变一个人。”
大概是进入初中后的第三节语文课吧,语文老师和我们提了“诗歌课”这样一个概念。我以为就是像小学时学古诗词那样,却听大山头来的一个同学说,是让我们自己写诗。写诗——怎么可能?那不是大诗人才做的事情吗?我,肯定不行。
那节课,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语文老师说要带我们熟悉校园,“顺便采风”,地点是校园里的孔子像前,那里栽种着笔直的银杏树。老师让我们在校园里疯跑了一圈,再到银杏树下观察叶子和树的关系,并且加了一句:“诗歌没有对错,你想说的就是诗。”我盘腿坐下,拾起一片银杏叶,背靠着坚实的银杏树,闭上眼睛,心里泛出一种踏实的感觉,好像在与银杏树对话:“带我看看你们的故事吧。”
这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节诗歌课。没有出什么成果,心里有些歉疚,我是很想写出点东西的。老师仿佛看穿了我,笑眯眯地说:“不急,不急!放慢脚步,用心观察和思考,不要太在意结果。”
上过这样“慢”的诗歌课后,我会带着思考去翻找我的回忆。
那时,白天家里必定是空荡荡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出门劳作了,家里只剩下阿祖和我。阿祖八九十岁了,他的眼睛已看不清东西。六七岁的我和阿祖相互照看,这正如我所愿!
躺在家里看动画片是个不错的选择!烦人的是,每到傍晚,我的动画片都会被阿祖换成《新闻联播》。我在一旁嘟囔着:“你看也看不到,光听又有什么意思?简直是浪费。”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了了。当阿祖再来敲门时,我并没有打开房门,而是在门内用双手紧紧地扣死了门把手,心想,反正他看不见,把门锁死就好了。见无人应答,他准备拉开门,但已做好充足准备的我怎能让他如愿?
直到他喊出我的名字,我有点心虚,但又不舍得放弃。一次,两次……我越拉越紧。终于,他紧握的双手松开了,迈着沉重的步伐回了自己的房间。我为赢得这场“战争”而窃喜!晚上,爷爷奶奶拉着我的手问阿祖我当天在家的表现,阿祖却对这事只字不提,满脸笑容地表扬我。
我以为阿祖是怕我以后不给他听《新闻联播》了,所以不敢把我的“恶行”公之于众,还为自己的“机智”得意。现在上了诗歌课后,我学会了静下心来慢慢思考,阿祖那时的表扬让我面红耳赤。岁月不待人,当我终于成为阿祖口中的样子时,阿祖已经离开了。这个我本想永远烂在青春木匣子里的老故事,如今,我愿意将它分享出来。因为诗歌教会了我,要坦荡地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我在诗歌本上创作出了我的第一首小诗:
小时候
我想把你锁在门外
长大后
你真的被锁在了门外
诗歌真的很神奇,它仿佛带着魔力,一施法,一片片银杏叶纷纷落下,掩盖了这一切。后来,那些树叶便成了我的书签,永远伴随着我。
那时,我还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语文老师跟我们说,镇上中学有一个年轻的支教老师带着那里的孩子们写诗,诗写得非常好。就这样,我们村完小的老师也深受影响,决心带我们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成为一个个小诗人。
当时,我们的课本里很少出现现代诗,而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却频频出来“折磨”人,以至于我认为诗歌就是那些枯燥的古诗。更让人头疼的是,老师布置了“写诗”的周末作业,要求我们必须完成。
背着“亿万斤重”的诗歌卡片回到家,我看到父亲谈了不久的女朋友端坐在沙发上。她比母亲漂亮,比母亲脾气好,但眼中却没有母亲那般藏不住的爱意。那年母亲和父亲吵架,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再也没有醒来。对于刚步入小学的我来说,母亲的离去好像是出了远门,我没有太多印象。家里的亲戚哭得声嘶力竭,我就那样怯怯地站着和他们一起哭。
慢慢长大后,我才意识到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走了。我开始习惯性地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隐藏起来。同样,这次写不出诗歌的痛苦与惆怅,我也不会告诉父亲的女朋友。奶奶和我说,要是我不愿意叫她“母亲”,可以叫她“孃孃”。我知道整个世界都待我极好,我没什么好抱怨的。只是母亲走后,我已经习惯了不太言语的生活。我不知道难过时是可以和别人倾诉的,我还没有学会。
进入初中后,新的语文老师为我们讲解诗歌。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诗可以不讲究对仗工整、音律合谐;第一次了解,不用华丽的词藻、丰富的修辞,也可以传递出真情;第一次感受到,天马行空的想象是那么有趣,身边每一件小事都那么富有诗意;第一次认识到,有一种行为叫倾诉!
从此,诗歌不再是给我施加压力的作业,反而成了我忙碌的学习生活中的调剂品。它让我愿意用更积极的态度去感受午后阳光的温暖、夜间星河的灿烂。
现在,诗歌已然成了我倾诉的方式。在云南省漭水初级中学,我写下了第一首被“是光诗歌”公益组织录用的小诗《妈妈说》:
对于你
抚养是义务
而爱是本能
这首小诗,写出了母亲对我的爱,以及我对母亲的思念。我可以大胆地表达对母爱的渴望。平时不敢言说的想法,旁人认为矫情的话语和悄悄埋在心底的故事,我可以在诗歌的国度里畅所欲言。
因为诗,我有了和母亲一样可以倾诉的对象!
在拍摄中,小锁(施应锁)和小云(穆庆云)这两个孩子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刚开始接触时,我们的小锁憨厚到有些“懦弱”,他最好的朋友是家里的小黄牛,但这种乡土味的成长环境并没有让他变得木讷,反而激发了他的共情能力,这是让我最惊讶的。在他的诗句中,隐晦的表达盖不住内心的火热。他最爱和妹妹一起遛弯,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他主动不要手机,想考个好高中,爱吃肉但是经常让给妹妹和奶奶,他是那么热爱自己周围的一切。
小云非常懂事,懂事到令我们心疼。每次跟她聊天,她眼睛里闪烁的那种对外面世界渴望的光芒真的盖不住。我们很难想象,这双清澈的双眼掩盖了多少孤独的夜。
夜半灯旁,当小云举起手机,给妈妈读着“母亲去广东的时候/我把我的鞋放在母亲鞋的旁边”,我和摄像老师都按捺不住情绪,几度落泪。
我感谢诗歌,让小云突破了内心那道表达的高墙。面对生活,你可以说、唱、跑、跳,你也可以写诗,灼热或冰冷,九霄的羽毛与尘间的青泥,桌边的饭碗和床下的小鞋,还有远方的母亲。字字如雨珠入云,打落在这诗间。
这些孩子也让我开始思考。
我们拍摄了孩子们幻想“十年之后的自己”的场景,这个命题也很打动我。很巧,拍摄的时候我24岁,他们14岁左右。我的现在,就是他们畅想的未来,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尤其是当他们说出自己的未来时,我也会揣摩,我成为这些孩子口中优秀的大人了吗?
还有一部分思考,来自脚下的这片土地和眼前的教育方式。
除了标准化和成功学,我们还有其他定义“好的教育”的方式吗?
小锁一开始是比较木讷的,少言寡语。他所在的年级是全校最小的初一,他又是班里最矮小的学生。但一回到家,他就是妹妹的大哥哥,是田间的小诗人,这种反差让我惊讶于孩子的多面性。回想自己的小学、初中时期,其实当时的我也是有很多切面的人,并不是某个标签下的“某某学校的学生”。还有很多孩子因为片子时长有限无法一一展现,但他们就在那里。这世上还有很多小锁、小云,他们并不只是活在报道中的标签,并不只有“留守”“贫困”,他们有那么多的闪光点,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捐钱捐物,更需要关注的目光、情感的共鸣。
即便在大数据手段如此成熟的今天,人依然是不能被简单标签化的存在,而孩童的灵魂更加纤细、敏感,这让我思考了很多关于乡村教育、城乡视角的问题。
小锁、小云们,他们的双眼所见是怎样的世界?而我们又能为那些缤纷的大千世界做些什么?想来,我也在通过这次拍摄慢慢长大。
乡村少年的诗
孩子 云南省漭水初级中学 穆庆云
小鸟是大树的孩子
白云是蓝天的孩子
路灯是黑夜的孩子
母亲去广东的时候
我把我的鞋
放在母亲鞋的旁边
因为
我是母亲的孩子
小石头 云南省漭水初级中学 鲁慧蓉
岸边的小石头
无人问津
像是睡着了
其实
它只是在等待
能溅起无数水花的人
心事 云南省漭水初级中学 罗刘发
我把心事做成书签
夹在书里
再次翻开时
书还是原来的样子
只有心事
变成了青春
答案 云南省漭水初级中学 李海映
当我得到
人生的正确答案
我已经失去了
作答的能力
冷战 云南省漭水初级中学 于世雄
这是个无聊的游戏
我和同伴却玩了一个下午
他不和我说话
我也不和他说话
湖与鱼 湖南省岳阳县麻塘中心学校 姜静怡
我每天都喝几瓶水
一生就能喝下一座湖
湖里的鱼
游来游去
交换心事
生出快乐的浮萍
楼 湖南省岳阳县麻塘中心学校 方天乐
它克服了恐高
慢慢地
变高
一见钟情 湖南省岳阳县麻塘中心学校 徐志葵
春风吹过我的脸颊
我望向围墙外那闯进的
一片绿绿的嫩叶
像小羊见了小草似的
忍不住凑了上去
我注视着它,走了神
我爱着它,我也深深地爱着春天
影子 湖南省岳阳县麻塘中心学校 黄嘉蓉
我喜欢我的影子
我喜欢她在有风的夜晚
奔跑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