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悬一线,我不放手
作者: 薄世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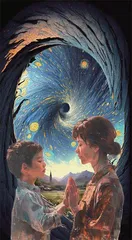
1
作为一名天天在临床救治生命的ICU(重症监护室)医生,在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病例,见证过各种各样的爱之后,我认为理性的爱应该包括3点:先救自己、拥抱时间、不放弃希望。
首先是先救自己。
民用航空业有个安全规则:一旦在高空发生失压或者其他意外,氧气面罩会自动脱落,此时父母要先给自己戴好面罩,再帮助未成年的孩子。为什么?如果单纯地靠冲动、靠天性、靠本能,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救孩子,万一大人突然缺氧窒息,反而会失去救孩子的能力。父母只有自己先活着,才能救孩子。
临床医学界也有规则,要求在优先保证施救者安全的前提下再开展救援。在进行心肺复苏的现场,施救者第一步要做的不是马上对心跳停止的人做胸外按压,而是评估环境是否安全。因为只有施救者安全,被救者才可能获救。
先救自己,然后才有能力帮到需要帮助的人,让爱更有价值。这看似是个常识,但要做到并不容易,尤其是父母在遇到孩子生病甚至处于危难之中时。先救自己是理性的爱中最难做到的一环。
其次是拥抱时间。
当我们遇到一时还无法解决的困难时,我们很容易被爱的名义裹挟,做出不理智、无原则、盲目牺牲的选择。而事实上,先争取活下来,把困难交给时间,用时间去对抗困顿,可能是更好的策略。
在临床医学上,很多疾病的治疗随着时间发展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比如冠心病、结核病、肺炎、哮喘、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甚至某些类型的癌症……现在治不好的疾病,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案。尤其是新的医疗技术——基因编辑、脑机接口、mRNA等技术的涌现,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技术完全有可能运用于治疗疾病,给患者的治疗提供更多选择。
最后是不放弃希望。
当患者命悬一线、危机重重,家属对患者怀抱希望、不放弃治疗的结果可能是患者的康复。有时候,不放弃才能等来奇迹。
只要一提到“希望”,我就会立刻回忆起一个发生于2005年的溺水男孩的病例。
2
“医生,你告诉我,我儿子醒来的希望有多大?”男孩的母亲个子不高,眼睛红肿,站在ICU门口盯着我问。
“现在看,能不能保住性命还不一定。”我说,“孩子的生命体征太不平稳了,深昏迷、休克,要用大剂量升压药,心率每分钟145次,需要通过呼吸机吸入纯氧才能维持氧合,而且心跳停了这么久,大脑缺氧太严重了。”我摇了摇头。
离她两三米远的电梯间外的地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他头发一绺一绺的,只穿了一条泳裤,脚底满是黑色的泥巴。他耷拉着头一声不吭,听我这么说,突然发疯了似的“啪啪啪”左右开弓用力地打自己的脸。
女人连头都没回,继续说:“我儿子特别听话,医生你想想办法,他变成什么样我都接受。”
很多人可能会质疑我,为什么不告诉这个8岁男孩的父母,他们的孩子醒来的希望有多大。这个孩子因为溺水发生了心搏骤停,陷入了深昏迷,这时候给他的父母一个确切的数字,对他们接下来的决策至关重要。他们至亲的人躺在ICU,这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愿意花钱,哪怕是拿出一生的积蓄来维系希望。
医生不应该给一个确切的数字吗?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在很多时候,医生很难用数字准确地描述希望。
为什么?
首先是人体的复杂性,同一种病,不同患者也可能症状迥异,即便治疗方案一模一样,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其次,临床上某一数据的获得,必须基于人为控制的标准化的研究方法或规范的流行病学调查。关于溺水后心跳停止、经心肺复苏恢复心跳后陷入昏迷的少见病例,患者能够醒来的概率是多少,在世界范围内并无翔实可靠的数据。最后,多种因素会影响患者预后。比如,影响这个孩子能否醒来、将来大脑功能可以恢复到什么程度的因素太多了,除了医生的治疗,孩子对治疗的反应、有无基础病、治疗期间会不会出现严重并发症这些因素,还有个更关键的因素:他当时心跳到底停了多久。大脑皮层对完全缺血、缺氧的耐受时间一般只有4~6分钟,一旦超过这个时间,逆转的机会就会非常渺茫。
所以,没人能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那天晚上,这对父子去游泳,父亲游得高兴,把孩子丢了。等他找到孩子的时候,已经有人把男孩从水里捞了出来,当时孩子的心跳、呼吸都没了,一群人在泳池边又是慌乱地控水,又是按压。后来救护车来了,急救医生给孩子做胸外按压,气管插上管,给上抢救用药,终于出现了心电波形和微弱的血压,这时距离父亲发现孩子不见已经过去了20多分钟。这20多分钟里,孩子大脑缺氧的时间到底是多久?刚发现孩子心搏骤停的时候,泳池边的那些并不算专业的人给他做的胸外按压是否有效?这些问题统统说不清,因而这个孩子能醒来的确切概率是多少便无从谈起。
在这个男孩转来ICU的那天晚上,我立刻给他安排了全院专家会诊。各个科的专家对他的情况做了详细评估。他处于深昏迷,瞳孔光反射虽然还存在,但很微弱,这说明他的大脑功能严重受损。同时,这个男孩还合并了严重的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导致他出现顽固的低氧血症,需要应用呼吸机。同时,他吸入的并不清洁的池水又引起呼吸道炎症反应、渗出增多,肺部发生了严重感染,需要应用广谱抗生素。他刚入ICU时血压很低,要用大量的升压药物维持血压……
所有这些问题,都让他苏醒的希望变得渺茫。
每天下午3点到4点,ICU有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为了防止家属频繁进出增加患者发生医院内感染的风险,探视时间控制得很严。
这个孩子的母亲每天探视的时候,都会协助护士给孩子翻身、擦身子。
“儿啊,你睁开眼。”
“儿啊,你睁眼看看我。”
她一边擦身子,一边在孩子耳边喊。
有一天她找到我,说:“薄医生,你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多喊喊我儿子。我不会耽搁你们治疗,我也不会打扰到别的病人。”
说实话,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但我很难满足她。每个家属都眼巴巴地盼着能多点探视时间,谁都想多陪陪亲人,但如果给她开了这个口子,其他家属一定也会提要求,这对病房的管理和患者的安全都是不利的。
她不停地对我说:“你相信我,我不会打扰到别人的。”
我对同事刘大夫说:“我真想帮帮她。”
刘大夫点子多。“让她走后楼道吧,”他说,“晚上偷偷地来。只是没电梯,只能摸黑爬上来。”
这个病例入院的那年,ICU病房尚未搬迁,还在老内科楼的4楼,从后楼道可以直接走到这个孩子住的最西边的那张病床,这么走确实也不会影响到其他患者。
那天晚上,我和护士们都假装没看到她,任由她一遍遍地在孩子耳边喊:“儿啊,你睁开眼,你睁开眼。”
从那天后,每天晚上她都会偷偷地从后楼道上来,护士们会给她留好门,其他医生值班的时候也会默许,她每天晚上都在孩子耳边小声地一遍一遍地喊。
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个男孩,他长得白白净净,有着长长的睫毛、浓密的眉毛,但眼睛紧闭,没一丝反应。
每天晚上,他母亲几乎把嘴贴到他的耳朵边,一遍一遍轻声地喊着:“儿啊,儿啊,你睁睁眼。”
转眼过去半年了,她的很多亲戚朋友开始劝她:“算了,别让孩子受罪了。”
她说:“我儿子能醒。”
她还是每天晚上从后楼道爬上来,摸着孩子的头一遍一遍地喊。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个母亲坚持来ICU呼唤儿子,是一种对孩子的执念,也是一种不理性的“自我牺牲”。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为什么?
首先,尽管这个孩子处于深昏迷,依旧危机重重,但他的瞳孔反射还在,自主呼吸也有;尽管刚来ICU的时候他的很多生理反射消失了,但随着治疗,他的生命体征逐渐稳定,很多反射逐步恢复。这些客观指标的改善说明,尽管可能性渺茫,但孩子还有醒过来的希望。
其次,在我看来,母亲的呼唤不仅是爱的召唤,也是一种治疗。这位母亲每天对着孩子的耳朵轻声地喊着“儿啊,你睁睁眼,你睁睁眼”,这种呼唤就像每到炊烟袅袅时分,母亲扯着嗓子、拉长了声音,呼喊她因为顽皮忘了回家的孩子回家。
所以,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选择给这对母子留了一条“后楼道”。有人说,教条之上有人心。医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它蕴含着人性。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无比痛心的病例,这样一个昏迷不醒的孩子,还有他每天喊着“儿啊,你睁睁眼”的母亲,再严苛的规则也应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做出些许调整。何况迄今为止,医学上还有很多不能完全清晰阐释的现象,谁敢说人类的爱中没有促人康复的能量存在?谁敢说爱不是一种治疗?
而我坚信,尽管爱的治疗作用暂时还不可言说,暂时还无法准确定量,但爱的能量一定存在。
有一天我上夜班,这个母亲又像往常一样,走进病房,走到孩子的病床边,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孩子的脸,弯下身子在孩子耳边喊。
突然,孩子的眼睛动了一下。她瞪大了眼,怀疑自己看错了。
“儿啊,你睁开眼啊,你可怜可怜你妈。”
突然,这个昏迷半年多的孩子睁开了眼睛……
我推断,这个孩子之所以能够醒来,一定是他在心搏骤停时,好心人在泳池边的及时按压有效,使得他的大脑完全缺氧的时间并没有那么久,所以他才有了这微弱的醒来的希望。这个病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力量。
在我看来,医学发展史上每一项重大技术和理论的突破,都不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胜利,而是在危机当头,在患者命悬一线时,医生、患者、家属不放手带来的奇迹。
有人说:“希望就像太阳,如果你只在看见的时候才相信,你就无法度过漫漫长夜。”
这个病例告诉我们:希望有时看似遥不可及,但只要我们不放手,它或许就近在咫尺。
后来这个孩子出院了,智力没受到影响。我后来听说,他休学一年后又去上学了。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我想,他应该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吧。
(刘 振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命悬一线,我不放手:ICU生死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