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一”讲话“两个结合”看经典阅读的当代意义
作者: 刘跃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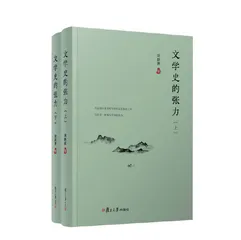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其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我们倡导全民阅读,就是贯彻落实这个精神。
为什么阅读经典
世纪之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书异军突起,迅速占领市场。而今,读书已非难事。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大脑成为各类知识竞相涌入的跑马场,很少有消化吸收的机会。
当下社会公众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情形是:在阅读的传播媒介上有传统的纸媒,也有新兴的网络及社交媒介,比如微信等;阅读的内容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以大杂烩的局面形容概括似不为过;阅读情形则主要呈现为碎片化阅读、快餐式阅读和猎奇性阅读;阅读群体的主力军是中等收入者,由于网络的普及,青少年也崛起为阅读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古代经典作品的阅读而言,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快节奏,价值观的多元化,加上语言文字的隔膜,阅读状况并不理想。即便是现当代以来的文学作品的光芒,也处于消退边缘的状态。
目前,人们了解古代经典作品内容的方式,有包括出版物在内的各类纸媒、电视、网络、电影、社交媒介,还有社会因素的影响等。对于广大的社会公众而言,由于传播媒介和阅读趣味的变化,影视媒体和网络小说改编是直接或间接接触经典作品的重要方式。比如,央视文教频道推出的“百家讲坛”栏目,综合频道推出的“中国诗词大会”栏目,影响力都不小。根据网络小说而摄制的电视剧《庆余年》,收视率一度较高,其中表现主人公文学修养之高和记忆力超人的方式,就是“串烧”似的背诵古诗词,把一些经典的诗词名句间接地传输给社会公众。但这些与通读或精读一部完整的经典作品还是不同的,仍然大体属于灌输式或碎片式的接受。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读经典成为解决当前精神困惑、重建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经典是什么?经者,常也。经典,就是常读常新的书。常读常新的著作不多,马列经典、红色经典、传统经典,就是这样的著作。
怎样阅读经典
一是马列经典。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主流思想已经接近一个世纪了。这一科学真理之所以能于20世纪传入东方的中国,并能在彼时万卉纷呈的思想园地中一枝独秀,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不仅由于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能够在文化层面积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对话交流,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支撑和认同,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沃土和传播的载体。
例证之一:作家的生存环境与物质环境。
2011年8月28日,在“中荷文化交流:文学、美学与历史”论坛的闭幕式上,荷兰著名学者Mieke Bal大声呼吁:文化研究如何返回经济因素。因为物质生活对于作家精神生活的决定性影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论证过的一个基本常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有这样一段名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从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来阐释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来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得出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这样的结论。这个问题大家在过去研究中都是关注的,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也就是说一切出发点都是由经济决定的。但是落实到具体作品研究时,又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文学史中讲了那么多文学家,讲了那么多文学作品,但是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呢?就是这些作家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的作品似乎是在一个真空的状态中产生出来的,缺乏对具体的物质文化氛围的阐释。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一个作家的生存环境直接影响到他对整个社会的基本判断;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又直接影响那个时代的上层建筑。
例证之二:时间与空间的维度。
文学不是避风港,也不是空中楼阁,它一定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当中的;一个作家的精神生活也离不开他的物质环境。我们只有把作家和作品置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加以考察,才能确定其特有的价值,才不会流于空泛。诚如恩格斯《反杜林论》所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过去,我们常常大而化之,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而今我们比较注意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还原,走近了真实的历史,所得结论也就比较切实。
例证之三:文学研究要关注不同的社会阶层。
虽然现在对于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以为然,但是这个问题无法绕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开篇就说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于社会的认识,也应从社会阶层的分析开始。
什么是阶层?其实就是人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不同阶层自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学形态。其实,这已经进入了社会学的观察范围,即研究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所谓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化,这些角色和地位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形态变化,以及规范和调节各种社会互动关系的价值观念变化。宏观上,对整个社会影响极大的结构性变化,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组织结构、利益关系结构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结构等十一种重要结构的深刻变化。理论上,可以把这十一种结构分为五组:(1)社会基础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2)社会空间结构,包括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3)社会活动结构,包括就业结构、职业结构和组织结构;(4)社会关系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关系结构;(5)社会规范结构,也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结构。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化,不再是过去的两分法,而是变成了若干个阶层,这就涉及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
文学史永远就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写的,是文学史家的产物,他所关注的只是他认为值得关注的东西,已有一定的过滤,含有自己的判断取舍,是否真实地反映历史,还是问题。所以文学史永远不可能100%地反映那段历史。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只关注一个阶层,即所谓的精英文化。虽然不用这个词,实际所叙述的主要是这个阶层的文学。事实上,文学发展是多样性的,不可能只有一个阅读群体。像“五四”运动前后,文坛主流是什么?文学史告诉我们是胡适、陈独秀等文化精英们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但是这些新文化运动是谁在扛?都是精英分子来扛,而老百姓关心的是什么?依然是鸳鸯蝴蝶派的东西。鲁迅生于1881年,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而张恨水生于1895年,其名著《春明外史》出版于1930年。他前后创作了一百多部长篇小说,三千万言,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价值,是一种游戏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没有思想性和革命性,但是却有市场性。可以说,他在当时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鲁迅的母亲就是张恨水迷。上世纪30年代,其影响甚至超过五四时代的战将,以至于这些战将还要争夺市场和读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文化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化。在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种文体、学术思潮,大都源于民间。即便是一些外来文化,也往往是通过民间逐渐影响到上层社会。它们跟主流文化始终保持距离,但是影响往往比主流文化更大,而写文学史的人是不会把这些人写进去的,因为他们不入流,但他们在文学史上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
二是红色经典。近年来,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以丑为美,二是解构经典。我们知道,随着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上帝创世的神话被打破了,理性万能的说法也被质疑。中心没有了,主流没有了,剩下一地碎片。于是,审丑成为时髦。作为美的对立面——丑,自有其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追求。《巴黎圣母院》的主人公很丑,但心灵很美。而今呢,很多作品美丑不分,甚至为迎合世俗口味,用滑稽戏谑庄重,用丑陋消解崇高。
解构经典便是这种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如《诗经》《楚辞》,伟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等,在一些文学史著作中,甚至一笔带过,似乎无足轻重,那些不入流的作家、作品,反而登堂入室。审美观点不同,评价标准各异,文学史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叙述历史。而我,依然信奉传统的看法。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听叶嘉莹先生讲课。她说自己回国教书,没有别的目的,“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老人家至今依然从事着对传统文化的传经布道工作,令人敬仰。《诗》、《骚》、李、杜,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偶像,如果消解掉,我们的灵魂该如何安放?自从喜欢上文学,我就从“鲁、郭、茅、巴、老、曹”等经典作家作品读起,受到精神洗礼。而今,在听起来很好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下,这些作家逐渐被边缘、被冷落;即便被提及,也不无讥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大声呼吁尊重传统,积极倡导重读经典。近年,文学研究所依托河北、陕西、山西等红色根据地开展文学国情调研,举办多种学术研讨会,取得一系列成果。
三是传统经典。从根本上说,中国学问源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所谓“六经”,汉代称为“六艺”。《乐经》不传,古文经学家以为《乐经》实有,因秦火而亡,今文经学家认为没有《乐经》,乐包括在诗和礼之中,只有五经。东汉时,除了五经以外,增加了《孝经》和《论语》,合为七经。唐代,把《礼经》分为三:《仪礼》《周礼》《礼记》;再把《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增加到九经。晚唐时期,又把《论语》《孝经》《尔雅》加进去成为十二经。宋代为了抬高《孟子》的地位,朱熹作《孟子集注》,进入经的行列,于是儒家的经典成为十三经。这是儒家基本经典,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典籍。当然也有在此基础上另推出一些典籍者,如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卷九)就在此基础上益之以《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等,以为二十一经。但无论如何划分,都以五经为基始。
例证之一:传统经典的思想价值。
首先,传统经典中的家国情怀,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脊梁。在中国人的心中,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与家庭、家族、国家紧密相连。从家出发,个人、家庭、群体、国家乃至天下,一脉相承,共同支撑着我们的理想。这就是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基于我们祖先对天的敬畏。天是最高的境界。天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从自然层面来说,日月运行,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有其亘古不变的运行规律。从社会层面来说,天就是老百姓。《左传》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民的地位是很高的。由此说来,敬天就是敬畏百姓。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指出,谁能获得百姓的信任,谁就会赢得最终的胜利。谁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谁就必然招致灭亡。《尚书》多次强调知人安民的重要性。《荀子·王制》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管子·四顺》也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天地间,民为贵,这是非常重要的民本思想。
从个体层面来说,他的一言一行也必须心中有天,以德昭示天下。《大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起点,强调内心修养、个人行为的重要性,最终以经世济民为目标,因为一个人的好坏,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它关系到家族的荣耀,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更关系到天下兴亡。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何做到修、齐、治、平,《中庸》还有两句话特别重要,一是正心诚意,二是致知格物。心正,才能意诚。诚有天道、人道之别。天道的关键在于诚,而人道的终极目标则是对诚的追求。《周易》就强调君子当进德修业,修辞立诚。欧阳修《朋党论》也说,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道义、忠信、名节,都与诚有关。守道以诚,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报国以诚,就能同心共济,坚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致知格物,即推诚于物,致意于实,就是强调实践的意义。明代大儒王守仁在《答顾东桥书》中就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习近平同志指出:“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这符合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