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载东台知县魏源
作者: 张宏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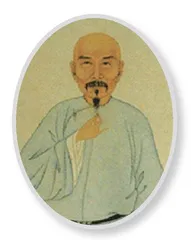
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秋的一天,一艘由江苏扬州开出的帮船,沿着运盐官河驶过海道口,在东台城西的商盐码头靠岸。船上走下来一位中等身材官人模样的中年男子,他就是东台新任知县魏源。
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墨生、汉士,号良图,湖南邵阳隆回县司门前人。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魏源随父来到京师入国子监。1820年全家迁居江苏扬州新城。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魏源来到南京清凉山下乌龙潭边购地建三进草堂,便长年居住于此,其间他与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往来甚密,其名著《海国图志》即在此撰写完成。
一
1844年2月,迫于谋取一官半职之薪俸养家糊口的压力,51岁高龄的魏源不得已接受朋友的规劝,再次忍辱,第五次走向科举闱场。这次会试的“四书”题出自《孟子·告之章句上》,以“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这14个字为题。魏源文思如潮涌,严格按照八股文的格式一气呵成,写就一篇时文。这一次,终于拨云见日,考中进士第19名。远在新疆戍所的林则徐闻听好友魏源中榜,不禁喜而赋诗以相贺。
据说当时魏源的文章获得了阅卷考官“劲扫千军,倒倾三峡”的批语,但谁知主考官看了却再生波折,以“磨勘稿草模糊”,即以其试卷草稿字迹模糊为由,罚其停殿试一年(延期一年殿试)。魏源满腔屈辱和悲愤,写出了一组揭露科举制度弊病的政治讽刺诗——《都中吟》13首。在诗中,魏源以“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嘲讽只要能写上一笔秀丽的小楷,能胡诌几首八韵诗,就可以当上文武将相,而且“官不翰林不谥文,官不翰林不入阁”。然而,由这种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脱离实际的书呆子,又有什么用呢,只能让他们“润色承平”,装装门面。魏源的忧愤之情可见一斑。1845年春,魏源补行殿试中恩科(于正科外皇帝特恩开科取士)三甲,93名进士,奉旨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
据当时传说,魏源上年考中进士后,主考官、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1782—1856,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是当时掌握实权的大学士,因此“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有意将魏源罗致手下。但魏源非常鄙视这个“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大奸似忠、伪学伪才”的顽固派首领,痛恨他在鸦片战争中主张议和、排斥构陷林则徐、重用投降派的丑陋行径,因而对他“漫不为礼”,不愿意走投靠“穆党”升官或者留京重用的捷径,并为此付出了罚“停殿试一年”和中进士却不能点翰林这样沉重的代价。好友邓显鹤来信对魏源中试后却未能授职翰林院表示惋惜。魏源回信表示,入翰林史官并不是自己的志向,今日史官整日以蝇头小楷、俳体八韵为报国之能事,我厕身其间,何以为情?不如做一个亲民官,为百姓办点实事。
经过六次会试,52岁终于熬成进士,魏源此时内心还是很复杂的。从15岁进学,已过去30多年,魏源不禁自嘲为“中年老妇,再作新娘”,但考中总还是高兴的,“万行柳色万声莺,啼遍千门万户春”(《游别海淀四首》其一,见《魏源集》)的诗句很是能够表达他的喜悦之情。虽已年过半百,毕竟踏上了真正的仕途。
二
此次,魏源奉命走马上任,暂时署理扬州府东台县知县一职,这也是他做幕僚十几年后第一次出任地方行政长官。东台知县的职责范围,大体包括管办全县水利路桥、县学书院、乡规民约、宗教慈善等,催办范公堤(北宋范仲淹在东台西溪担任盐官时修建的捍海堰)西各乡的田赋漕粮,处理全县刑民讼案和私盐案件等。东台沿海各盐场的产运销归各盐课司和分运司管理,然而由此引起的民事刑事案件却由知县管,知县却不能去盐场拘拿欠税灶户盐丁,不能影响盐业生产经营。因此,东台县这个知县并不怎么好当。《清史稿》说,东台县况“繁、疲”。比其上级扬州府“冲、繁、疲、难”少两个字。繁者,集镇繁荣,人口繁多,事务繁芜;疲者,荒滩疲敝,盐民疲惫,百姓有讼疲于奔命,县官场员疲于催税。魏源到任时东台建县已77年,面临着催收漕粮的艰难任务。到任东台前后半年多,这个知县的位子居然让魏源赔光了家中的所有积蓄。
当时,东台是江苏扬州府东部的一个小县,境内一条范公堤将东台县域东西一分为二,堤东地区为黄海盐碱滩涂,堤西地区为地势低洼的里下河地区,可谓地瘠民贫,农业经常歉收,朝廷规定的钱漕税赋(钱粮税收)征收愈加困难。
清代,漕运是国家税收的大宗,与盐务、河工同为东南的三大要政。而江苏是征收漕粮很重的省份,农民除了上缴正额的粮税外,还要缴纳耗米、轻赍(即弥补损耗外加征的少量资财)等附加税,而且鸦片战争后附加浮费更多于法定正耗税额,民户缴纳漕赋一石,实纳常常需要两石五六斗之多。折色纳银,实际上甚至需要“米七八石方能完额漕一石”。在这样的重赋苛敛之下,加上来自地主阶级的田赋转嫁,广大农民根本无力负担,“田内所收不敷两税”,使本来就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困农民更加雪上加霜。其结果,一方面是民众纷纷起而反抗,另一方面,“每大县额漕十万石者,止可办六万石”,以致“南漕岁岁缺额”。与此同时,地丁钱粮(按土地、丁口征收钱粮)的征收数额也无法保证。为此,州县往往采用挪移漕项赔垫地丁的方法以免处分,而这又造成漕项的严重亏空。在东台,历任知县也同样由此欠下了一大笔未完成的定额。前任知县葛起元就是因为滥征漕粮且过急而激起民变,差点酿成大祸,葛起元几乎被入狱,“交部议处,撤职发军,以儆怠玩”,故扬州府才急忙让葛起元卸任,委派魏源接任。
但是,东台县的钱漕是很难足额的,魏源一上任又赶上赋税清查,历任的亏空全都倒霉地落到魏源一人头上。
三
魏源到任东台后,礼贤下士,主动拜访了县内德高望重的耆老士绅,征求他们对治理地方的意见建议,同时惩办了一些奸猾恶棍,县民都很悦服,一致称颂“魏公勤惠,是爱我者也”。
魏源赴任前,扬州府告知,东台近年漕款滞迟,务须抓紧攒办,完成国帑(guó tǎng,国家的公款)。魏源到任后,方知东台的漕粮任务非常棘手,全县每年要上缴漕米19 000多石,外加征收来往于泰州、盐城、兴化三处漕粮收缴的90艘粮船运管费用,历任知县视之为畏途。漕运弊端重重,除了“俘收勤根”之外,还存在着“将值交卸,截串先征”的潜规陋习。有的官员就在离任前预先征税,将一笔财政暗亏的糊涂账留给继任者。
魏源接任东台知县,就遇到了这样倒霉的事。上一任知县极力征缴,却将征得的4 000两漕银全部带走,欠款悬挂在账。面对任务和亏空,魏源会集各乡铺的乡长铺董,了解情况,商讨措施。众人反映,近年西水东潮屡屡泛滥,粮食歉收,上年征漕过猛,再征将难以见效。魏源处于狠征苦民、缓征罹咎的两难境地。
魏源没有退缩,而是采取敢于担当、恩威并用的非凡手段。当时,一些民众还沿袭“挟长持短,聚哗”的老路子,聚众而来,吵闹抗税。魏源上任后宣布继续征粮的第二天,就有人击鼓喧哗,阻止征粮,守仓士兵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魏源当机立断,果断采取措施,亲自带士兵到闹事者前来的路上预先设伏,将为首的“擒十余人,置诸狱”,“众乃窜散”,突击抓捕了十多名挑头闹事人员入狱,其余抱头鼠窜而去,一举稳定了县城秩序,由此震慑了抗粮的民众。接着,魏源又出其不意地释放遣散了被抓的挑头闹事人员,且宣布既往不咎,使民众信服,愈益“感劝”,很快上缴漕粮,一场哗变也随之平息了。随后,他又改建书院,整顿育婴堂,救济孤寡老幼,为百姓传种牛痘,“一切善政,不可枚举”。
考虑到东台百姓多半以烧盐、捕捞为生,生活确实艰难,堤西农户既要缴田赋,又要缴漕粮,还要再缴盐课的水乡折价银,委实多重负担。魏源不忍再强讨复征,决计宽宥百姓,说服家人节衣缩食,宁可用自己的薪俸、前半生积蓄和全部家当换成银子垫赔前任所欠漕款,也不愿将这笔额外负担转嫁给无辜的百姓。最终,自己一贫如洗,艰苦度日。
四
针对聚哗抗漕事件,魏源通过调查,发现吏员中有与外界通风透气的情况。新官旧人员,换官不换吏。自己一人来此赴任,唯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方能以上率下,清风正气。于是他蘸墨走笔,撰写楹联,张贴在县衙内,以此勉励自己清廉善政、爱民利民,告诫下属循规蹈矩、便民为民。
题于庭柱上的联:
上有青天,一片冰心盟上帝;民皆赤子,满腔热血注民瘼。
题于门柱上的联:
民不可欺,常忧获戾于百姓;官非易作,唯愿推恩到万家。
题于正堂上的联:
安得民情常达;唯恐己过不闻。
三副楹联,六处提到百姓万家,反映了魏源心系苍生、造福百姓的赤子之心和严于职守、秉公办事的循吏之心。这几副楹联,现复制陈列在东台市城市展示馆内。如今,人们每每读罢此三副楹联,遥想魏公往事,无不感慨万千,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经此聚哗抗漕事件,魏源开始关注、思索征收漕粮这一最大难题,深刻地感受到了江南钱漕弊政的严重,于是撰成《钱漕更弊论》一文,呈交时任江苏巡抚李星沅,道出了自己对更革弊政的想法。指出,江苏漕费之大,州县之累,日甚一日。其弊有三,即明加、暗加、横加。1825年(清道光五年),行海运,停河运一年,旗丁以罢运为苦累,要求补助。1826年,河工大挑,空船截留黄河以北,旗丁又以守船受冻为苦累,要求补助。每苦累一次,则次年必求调剂一次,这就是明加之弊。一开始漕运帮费用制钱不用洋银,当时洋银每圆兑制钱八百文,所以州县官经常舍弃制钱而用洋圆以图省事。后来洋银价日益上涨(即银贵钱贱),兑费也随之增长,其用洋银之费已不可挽回,这就是暗加之弊。1839年间,四府粮道陶廷杰挑斥米色,骄纵旗丁,于是两三年间,各州县约加帮费30万两,这就是横加之弊。朝廷一再减免苏州、松江浮粮,但官民仍不胜其困。原因何在?魏源认为,银价之弊,已经无可奈何,只有裁缺并县之法,每并一缺,则省官规幕费、丁役杂费及应酬之半,这也许是救弊本原之法。由此可见,当时的漕运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魏源在无奈之际提出的“裁缺并县之法”在当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五
魏源在东台期间十分重视贤能人士的发现和举荐。
东台西有大湖,东临大海,西水与东潮经常危及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水患实为首害。当时,东台时堰人冯道立(1782—1860)对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都颇有研究,特别对水利方面钻研很有造诣,著作较多。朝廷曾授冯道立为承德郎,道光皇帝赐手书“征辟”匾额及顶戴花羚等。魏源闻其名,亲自赴时堰小镇登门造访,与冯道立共同商讨治理里下河地区水患的对策措施。冯道立认为,东台必须巩固东西堤防,疏浚入海水道,“尾闾既泄,腹胀自消,下游多一分去路,上游即少一分狂澜,其裨益不仅东台一县也”。魏源对冯道立的治水观甚为赞同,同时见他建立和主持的慈善自治机构很有成效,就手书一副对联赠予冯道立:“绘郏亶之图一卷中己饥已溺,熏阳城之化数千家毋讼毋嚚(嚚,yín,形容人奸诈、狡猾)。”赞赏冯道立的治水思路能解决水患饥荒,乡规民约能化解争吵不和。这副楹联至今刻在东台市时堰镇冯道立故居中堂门前的木柱上。
魏源认为冯道立人才宝贵,极力向两江总督陆建瀛推荐冯道立。冯道立乃获参加制科,举“孝廉方正”,例授承德郎(冯并未出仕),对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水患治理做出了贡献。
魏源尊重和采用冯道立的水利方略,深入各乡巡察河道,分清轻重缓急,疏浚入海水道。魏源查知东台县西与泰州、兴化交界处的斜丰港年久失修,长达百余里的下水河道淤塞,如遇大雨洪水倾泻,对东台影响极大,就利用冬闲时节组织民工修挖疏浚。他亲临现场指挥,合理分工,严明纪律,关心生活,很快就完成了疏浚工程。来年夏季大水,上游涌来的洪水经斜丰港宣泄入海,很好地清除了水患的威胁。
魏源发现东台一直人才不旺,很少有中举者,中进士的更是寥寥无几。他觉得甚为奇怪,就开始调查研究,发现在士子们学习的泮宫(学校的美称,即学宫,原为台城文庙,后在旧城陶瓷厂处)河对面是东窑,有砖瓦窑数十座,百余年来砖瓦烧制不息,终年烈火熊熊,烟气弥漫,尘灰飞扬;砖瓦下河装船,号子人声鼎沸,对士子们的读书学习很有影响。魏源惆然叹曰:“国家求人才于士林,而庠序实士之根本,烈熖冲霄,终年燔炙,复何望耶?”他认为此嘈杂、污浊、昏乱的环境自然影响士子的学习情绪,乃与商会、窑界商量迁移砖窑,以改善学宫的学习环境。商会窑主们思想不通。正协商间,魏母病重,不得已耽搁下来,后来魏源常以此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