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命周期的低收入人口认定和帮扶研究
作者: 严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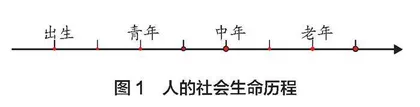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在此基础上,为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大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力度,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2023年10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单位《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3〕39号)(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已纳入和未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的低收入人口提出监测要求;对发现低收入人口未纳入社会救助范围或发现困难情形复杂的,提出了解决办法。
低收入人口及家庭的情况具有动态性,这是因为从人的生命周期来看,动态性是个人和家庭的基本性质。本文从生命周期视角,分析人的不同阶段的脆弱性特点,从而帮助分析低收入人口动态性,以便相关部门进行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
人的生命周期中的脆弱性人的生命历程图
在社会科学家探讨“生命周期”之前,哲学家和诗人早就有此看法。西塞罗(Cicero)就生动地描绘过生命的变化模式、老年人的愉悦,以及他自己在已经成年的孙子死亡时所流露的极度悲伤。莎士比亚对老年的态度则没有那么积极,他认为人生分七个时期,从“呱呱啼哭”的婴儿到“没牙、没视力、没味觉、什么都没有”的老人。[2]52
人的社会生命历程比较容易理解(见图1),从新出生的婴儿开始,经历青年阶段、中年阶段,然后迈入老年阶段。但事实上,从生理方面看,人的体质、体能、心智、精神等都不是一条直线成长和发展的,考虑到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人的学历高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状况更不可能是直线发展的,所以,为加深对人生道路及生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理解,还需转换视角。
社会学界已有“橄榄型”“哑铃型”社会结构学说[3]44,童星教授指出,从立体来看,如果社会结构呈“橄榄型”,中间阶级数量庞大,成为社会的缓冲区,那么这样的社会比较稳定;但如果呈“哑铃型”,那么社会结构也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尝试建构“水母型”社会结构(因形似水母而得名,如图2),静态地可以看出一个社会低龄、青年、中年、老龄群体的分布,以及低龄、老龄的弱势状态;动态地可以看出每一个人从低龄到青年、中年所表现出的由弱变强的特点,以及从中年到老龄所表现出的由强变弱的特点。基于“水母型”社会结构来了解生命历程,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的成长和变化,特别是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弱势群体的生理、学习、就业、收入、生活等状态。
“水母型”社会结构说明
三大群体概念。平常人群体(图中实线,此处不用“正常人群体”,是为避免与其对应的是“不正常人群体”),就是依靠自身能力,通过劳动和就业获得收入能够满足自己及家庭成员需求的人群,包括占比很大的普通人和占比较小的强势群体。平常人群体中的低龄因“幼小”、老龄因“体衰”也有“弱”的方面(低龄和老龄时在A轴以下),对其扶助的责任以家庭为主、国家和社会分担。动态弱势群体(图中段状线),是指因健康、性别、教育、技能、就业机会、地区差异等原因,有劳动能力但就业情况不好、收入不稳的人群,他们在基本生活、医疗、住房、教育培训等方面可能需要国家和社会扶助。常态弱势群体(图中点状线),包括“鳏、寡、孤、独、残”等弱者,即孤儿、残疾人、孤寡老人等,他们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赡(抚)养人,是在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多方面都需要国家和社会扶助的人群。
三条轴线含义。A轴:生命周期中的平均能力线,线的上部表示能力强、下部表示能力弱。平常人群体中低龄者、老龄者能力是弱的。青年和中年人能力是强的。动态弱势群体随着年龄变化,低龄者、老龄者能力是弱的;青年和中年人因教育、地区差异、技术升级等原因,其能力在强弱之间变化,表现出动态特点。常态弱势群体中的人,能力都是弱的。A′轴:低收入(标准)线,按照目前比较多的国家通行方法,即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相对贫困线,也就是低收入(标准)线。B轴:与能力相应的收入线,该线表示人们以其能力劳动和就业所获得的收入。向上部分表示能力强,收入高;向下部分表示能力弱,收入低。
哪些人可能成为弱势群体或低收入人口
幼弱——人的生命早期,因生理弱带来多方面弱的状态。每个人的成长都要经过婴儿、幼儿阶段,等他们长大了,就成为成年人、劳动者,做着体力或脑力劳动,并且成为有劳动工资等收入的人,也就不弱了。据学术界的研究观点,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因直立行走,母体怀孕的身体特点、生理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生婴儿不能成长(熟)得像一些动物的幼崽出生时那样可以行走,吃固态食物,人类的婴儿出生后必须依靠母乳喂养一阶段之后才能逐步摄入固态食物,并学会站立、行走,学会语言、动作等。此后,在身体成长的过程中,还要经过学前教育、小学和中学教育,以及大学教育或职业教育,帮助儿童在身体、知识和技能等方面成长为青少年,进而成长为成年人、劳动者,从而步入人生由“弱”变“强”的时段。
老弱——人的生命晚期,因生理弱带来多方面弱的状态。由青年时的活力四射变为中年的身心沉稳,随着时光的进一步推移,人们自然会进入老年的身心状态。按照国际标准,一般将60岁或65岁定义为老年人的界限。进入老龄阶段的人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弱”的特点,首先是体质弱,人的体质在达到高峰之后,体质和体力自然会衰退。其次是精力弱,表现在听力、视力、嗅觉等多方面。再次是记忆弱,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下降是必然的,包括智力都会下降。最后是反应慢,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精力的衰弱,必然会带来老人的反应和动作慢等问题。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工作能力、生活能力甚至自理能力都会下降或丧失。
青/中年人中的常态弱和动态弱——多方面弱的状态。常态弱势群体中的青/中年人在其生命周期中,主要是因为生理、身体原因,在学习、就业、收入方面受到影响,从而在生活的诸多方面受到影响。平常人中的动态弱势群体可能有劳动能力,但受知识技能、经济社会和地理因素等影响,就业情况不好,收入不稳,生活的诸多方面也受到影响。
由此可见,具有幼弱、老弱以及常态弱、动态弱等特征的人(群)都可能成为弱势群体或低收入人口。常态弱势群体或动态弱势群体中的一些人(家庭)难以或根本不能通过劳动、工作、经营维持正常的生活(也就是收入、生活水平处于图2中的A轴以下),有些人(或家庭)可能出现极端情况,因此《意见》规定:防范冲击社会道德底线事件发生。
低收入人口形成的经济社会因素分析
身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个人(家庭),要想达到普通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既容易也不容易,因为蓬勃发展的经济带给每个人既有机会也有风险。作为经济社会主体的个人(家庭)对经济活动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所带来的结果都可能表现出很大的差别。
在为《大转型》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斯蒂格列茨指出,波兰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广泛流行的渗透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的教义——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4]1自现代以来,有非常多的证据支持以下历史经验:增长可能会导致贫困的增加。我们同样知道,增长可以为社会的绝大部分带来巨大的好处,正如在一些更开化的(enlighted)发达工业国家中所发生的那样。但总是没有记分卡用来记录被推向贫困的个体的数量,或者相对于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而言那些被摧毁掉的就业机会的数量。[4]8即使是亚当·斯密也以他小心谨慎的方式宣布,劳动工资并不是在最富裕的国家里才最高。因此,当穆法兰表明他的以下信念时,他并不是在表达一种不同寻常的观点。他说,由于英格兰尚未达到它伟大的顶点,所以“穷人的数量还将持续增长”[4]89。
阿马蒂亚·森则从可行能力视角分析了失业和贫困。失业还会对失业者的个人自由、主动性和技能产生范围广泛的副作用。这些多方面的副作用包括:失业助长对某些群体的“社会排斥”,导致人们丧失自立心和自信心,损害人们的心理和生理健康。[5]15
在分析社会正义时,有很强的理由用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来判断其个人的处境。根据这一视角,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对贫困问题采用可行能力方法的理由如下:一是贫困可以用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来合理地识别。这种方法集中注意具有自身固有的重要性的剥夺(不像收入低下,它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二是除了收入低下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影响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从而影响到真实的贫困(收入不是产生可行能力的唯一工具)。三是低收入与低可行能力之间的工具性联系,在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的家庭和不同的个人之间,是可变的(收入对可行能力的影响是随境况而异的、条件性的)。[5]86
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做的贡献是,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即收入),转向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加强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理解。失业对个人的生活还有其他严重影响,会导致其他种类的剥夺,这时通过收入补助带来的改善就会相应地减少。大量证据表明,除了收入损失之外,失业会导致多方面的严重影响,包括心理伤害,失去工作动机、技能和自信心,增加身心失调和发病(甚至使死亡率增高),扰乱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强化社会排斥,加剧种族紧张和性别歧视。[5]91
波兰尼和森的分析主要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考察,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可能带来对部分人可行能力的剥夺,由此会产生多方面的问题,表现为失业、贫困、歧视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也可能造成部分劳动年龄段的人成为“低收入人口”,这种“低收入”状态进而衍生出多种社会问题,如受其供养的低龄者和老龄者也都可能成为“低收入人口”。结合 “水母型”社会结构,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不同年龄段的人的低收入情况(见表1)。
表1中,对那些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青/中年人,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劳动就业情况不好,“+”表示可能有收入或低收入情况,而幼弱和老弱的人则无劳动收入(部分老人可能有低的劳动收入),常态弱势群体一般是低收入或无收入的。如果考虑社会保障中的多项目能够及时提供给相应的弱势群体,在表1的下面一行,则可以看出弱势群体都能有社会保障待遇,成为支持低收入人口基本生活的坚实基础。
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6]《意见》指出,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兜底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为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大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力度,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
新中国成立后,得益于中国制度优势,在不同的阶段,对弱势群体的界定和扶助呈现出变化和发展的态势。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面向灾民、难民、失业人员、孤老残幼等弱势群体,采取紧急救济的方式解决他们面临的困境与问题。计划经济时期,在农村建立了“五保”制度,向鳏寡孤独社员提供生活救济;在城镇向孤老病残人员和特殊救济对象提供日常生活救济。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社会政策体系化建设发生战略性升级,对城乡弱势群体进行了包括收入在内的多主体治理、多维度扶助。
政府机制: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主导。马克思、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支持,都看到了在分配中不能忽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都认为无视弱势群体存在及其困苦是不正义的。[7]45 《意见》 指出, 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因此,为保护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政府需承担起帮助弱势群体维持生存和身心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义务。《意见》规定,各地对已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的低收入人口,重点监测相关社会救助政策是否落实到位,是否还存在其他方面的生活困难;对未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的低收入人口,重点监测其家庭状况变化情况,发现符合救助条件的,应当告知相关救助政策,按规定及时启动救助程序。发现低收入人口未纳入社会救助范围,但可能符合救助条件的,要根据困难类型和救助需求,将信息分类推送至相关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处理;发现困难情形复杂的,可适时启动县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通过“一事一议”方式集体研究处理。当然,《意见》也规定对那些不符合救助政策的对象,及时让其退出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