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量故土,史述吾乡吾民
作者: 乔文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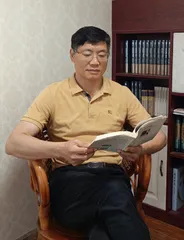
淮北地区,“在唐以前是生态良好的鱼米之乡,演变至明清民国前期,成为穷山恶水之地;从优质稻米产地变成了粗恶杂粮之区;从发达的手工纺织业中心退化成了纺织绝迹的经济边缘地带;从家诗书、户礼乐的文化沃土,变成了杀人越货的盗寇乐园;从精英辈出的人文荟萃之地,沦为江南体力劳动者的主要来源地”。这是一个区域自然生态、经济产业、社会人文的全面退化,弄清楚这种退化何以发生、如何延续深化,对人类,对国家,对民族都是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对于淮北人来说,今天淮北已经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巨大的改善,但千年积弊也并未消除干净,去追问这个问题不仅关涉那些宏大意义,更加关系那几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何以至此,我们将向何处去。
马俊亚是淮北人,他为故乡为这几个古老的问题提供了自己的回答。
自泥土中成长
马俊亚1966年出生于江苏沭阳的一个农村家庭。这个时代,这个地方的农家子弟,他的童年,劳苦和饥饿可想而知。
马俊亚的村子中间有清朝治河时被废弃的后沭河穿过。马俊亚经常带着辘辘饥肠和哥哥一起用平板车拉黄泥,黄泥被泛滥的黄河从黄土高原带来,不适合五谷生长,只能用来填坑盖房。村子西面是范围曾达数百平方公里的青伊湖和桑墟湖,村子因此被称为“湖东口”。村西南是民国时著名匪窟司家荡。村东也是曾达数百平方公里的硕项湖,邻村叫“陆口”。村南是古涟水,直通盐河。村北稍远是沭河。纵横的河汊湖泽带来的,除了打猪草、割柴禾之暇的摸鱼场所,还有年年进村入户、淹没庄稼的涝水,和水退之后的盐碱荒滩,以及邻壑之间的争吵殴斗。
“男孩子不吃十年闲饭”是长辈的教诲。由于父亲被事故烧成重伤,马俊亚8岁时就吃不到“闲饭”了,给家里和生产队干各种农活、体力活就成为生活的主题,在此之前,哥哥姐姐早已开始承担成年人的辛劳和责任,但却挣不到工分。秋收分配时,马俊亚家常常都是“透支户”,分不到几斤粮食。马俊亚的主食通常是掺杂着野菜的玉米糊,他能吃几大碗,但根本不抵饿,“往往在捱到上午第二节课的时候就饿得直冒冷汗”。每年马俊亚家总有一段时间断顿,母亲便会冒着“投机倒把”的风险与人合伙做“炒牌”(一种烤饼),原料小麦磨成80%的白面,15%的粗黑粉,5%的麸皮,白面做成炒牌卖掉,粗黑粉和麸皮便是利息供家人食用。
马俊亚的童年可盼的是外公。外公曾做过私塾先生,不仅会带来吃糠咽菜省下的粮食,让他吃饱一些,还会教他四书五经、千家诗、给他讲诗词韵律,在淮北农村贫瘠的精神土壤中为他带来难得的启蒙。
还在农村时,马俊亚就知道,村里最漂亮的姑娘都会外嫁,有的嫁给河南的矿工,有的嫁给了城里的瞎子,有的嫁给了吃国家粮(城镇户口)的傻子,有的嫁给了国营农场的二流子……当1984年,马俊亚以沭阳县华冲中学总分第一、高于“一本”录取分数线40多分的成绩考取苏州大学历史系,成为村里第一位大学生之后,富裕繁华的江南更是直观地成了贫困荒蛮的故乡的对照。
大学时代的马俊亚每天流连于苏州大学红楼图书馆的古籍之间,“因贫穷,家境不好,在上大学期间也没有多余的钱从事其他娱乐活动,我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读书、读史不仅给他留下了扎实的文化和史学功底,也逐渐唤醒了他的故乡之问。“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对近代经济史比较感兴趣,就计划先研究江南社会,然后再研究苏北,这样或许观察得更准确。”这也是他后来一直坚持的两个研究方向(江南社会经济与淮北社会生态)的由来。
求学期间虽然生活有些紧巴窘迫,但为了学术研究他从不吝啬。为了订阅《中国史研究》和《历史研究》等刊物,不惜缩衣节食;为了查史料,不惜花费到北京上海等地。马俊亚曾多次到上海拜访丁日初先生,每次只能住一晚10元左右的旅店;到北京,汪敬虞先生每次必留饭,与他长谈做学问与做人的道理。在他人都在抱怨论文难以完成的时候,马俊亚只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写作,余下的读博时间大多花在对苏北的调研上。1996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崔之清教授应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段本洛教授邀请,参加马俊亚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崔之清教授认为论文写得相当出色,并将马俊亚推荐给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教授作博士后研究。因此,他也成为南京大学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后并提前出站。
追问故乡:被牺牲的“局部”
“我的研究不是坐在书斋里喝着清茶或咖啡进行的,而是在泥泞的乡村道上捧喝路边的河水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我曾十多次对江南乡村做过调查。对淮北的调查次数就更多了。所以,我自信我的成果一定很‘真实’。”
1991年硕士毕业后,马俊亚到浙江师范大学工作,被派到时在蒋堂镇的金华一中锻炼一年。他决定认真系统地阅读马恩著作。于是,马俊亚在空闲的时间里精读《资本论》,一年做了近30本读书笔记。之后,又一鼓作气,把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读了大半。由此,马俊亚确立了自己的“生活决定意识”的历史观。“吃透了原著,我开始敢讲话了,敢讲自己的历史学观点了。”
早在1995年,马俊亚就开始了对苏北的调查研究,直到2010年历时15年的时间,《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繁体版)一书才得以出版,厘清了江南与淮北社会发展与社会冲突的地区性差异,通过江南与淮北的系统对比,找出了故乡落后的原因。
期间,他对书里划定的研究区域的每个县都做了田野调研,深入闭塞偏僻的乡村,由于没有经费资助,常与小商小贩同住。有时无缘无故被人詈骂,被村民围殴。“可以说,是真实的‘生活’给了我许多史学的观念和论点。”
经过查阅史籍、大量的田野调查,马俊亚在《被牺牲的“局部”》中阐明了淮北落后于江南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淮北地区社会生态的变迁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行政权力统治社会”而造成的负面结果,封建中央政府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而有意牺牲这一“局部利益”。江南由于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较早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得以用少量的耕地,养活众多的人口。相反,淮北的“发展”走了一条与江南截然相反的道路。在唐以前,淮北属于国家的“核心”地区,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非常优越,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1128年,宋军人为掘开黄河大堤造成黄河夺淮,初步破坏了淮北的水利系统;明代以后,政治中心北移,运送江南贡赋的运河漕运日益吃重,治黄治河力度空前,但其指导思想却不是为了民生,而是维持漕运和保护祖陵的政治需要。为了保护大运河的安全,把所有的黄河河水全部逼到了淮北,后来高家堰的修筑在平地上高悬起一个巨大的洪泽湖,整个淮北的水网系统都严格为运河服务,而非农业民生,淮北成了灾荒频发、匪患深重、社会生态崩溃的落后地区。因此,淮北地区的生态畸变和民生困苦被视为局部利益,让位于专制朝廷利益。
在运河之外,淮北还有另一个高踞民生之上的大局,盐务。盐业自始至终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柱,敲剥万民的抓手。但盐业的利益分配是基于与国家核心权力的亲疏远近,完全由政治权力掌控,丝毫不会惠及作为主产地的淮北,只给淮北留下劳役,和被剥夺限制锁死的社会经济。
《被牺牲的“局部”》在豆瓣上评分8.9,这个社科名著级别的评分,很直白地肯定了书的质量。考虑到这是一本区域社会生态史著作,专业性强,主题小众,专业读者比重高,这个评分可能还是偏保守的。马俊亚的著作当然不止于此。他有专著10部,其中《被牺牲的“局部”》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区域社会发展与社会冲突比较研究:以江南淮北为例(1680—1949)》获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除了自己的著述,马俊亚还翻译了很多外国名著,英国霍布斯·鲍姆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美国柯博文的《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影响》、彭慕兰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变迁》。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Modern China(美国)、Modern Asian Studies(剑桥大学)等数十种海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中国社会经济史和生态史专题研究论文100余篇。独立承担或主持的省部级以上课题13项,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运河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历史变迁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抗战经济研究(1931—1945)》等。
在中国古代,“史”的本义是公正。《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我们所想像中的史家,大约也是如此,中正平和,古井无波。但马俊亚似乎不完全如此,在他的文章和著作里,在庞杂的史料和严谨的梳理分析背后,常透出一种浓烈情感,一种对吾乡吾土的深切探究和因之萦绕的千年悲情。
(乔文娟,民革江苏省会委宣传处干部/责编 张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