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科研攻坚克难 不计名利忠诚奉献
作者: 宋志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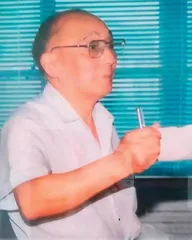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知重负重。全党同志都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保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
1999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两弹一星”事业的科研队伍里,除了这23位科学家之外,还有着一批埋头苦干、执着顽强,默默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他们同样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却甘愿做“幕后英雄”;他们同样来时风华正茂,去时华发苍苍,却始终心存梦想;他们的故事如同他们的事业一样“平凡而伟大”,他们精神如同一座丰碑“无言却永恒”。
“两弹一星”事业是中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伟业,也是科技强国的史诗。近日,《祖国》杂志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两弹一星”遥控遥测技术工程的奠基者葛叔平之子葛元仁,听他讲述父亲葛叔平“鲜为人知”的故事。
《祖国》:您的父亲葛叔平是我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委员,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出身工人家庭的他是如何走上国防科研道路的?
葛元仁:1964年党中央决定进行首次核试验后,父亲作为我军通信测控专家被中央军委指定为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的委员。但在他生前,从来未向家人说起过。直到他去世10年后,我从“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提供的资料上才知道。
我爷爷是长江渡轮上的售票员,家里很穷。我大伯很早就离开家自谋生路去了,二伯当了“上门女婿”,我父亲排行老三,他念到初中的时候,我五叔出生,靠爷爷一点微薄工资很难养活这么多孩子,奶奶就在家里帮人洗衣服、缝补来维持生活。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年幼的父亲被送去木行当学徒。但当了三年学徒,做的都是买菜、洗马桶,伺候老板一家老少的琐事,他不但没学到本领,还经常被打骂,于是,倔强的父亲跑到上海找我大伯去了。
我大伯当时在上海的天马电影制片厂管道具和服装,就给我父亲谋了一个差事,叫场记。所谓场记,就是记录导演现场的指示,给演员提示台词,在后台帮助搬道具、摆布景的杂活。在这个过程中,父亲逐渐对录音器材产生了兴趣。在20世纪30年代,电子录音设备属于“高精尖”设备,他就求教于洋人录音师学习,录音师很有耐心地给他讲,但他的文化程度太低,很多东西不理解,尤其电子设备的说明书都是英文的,使父亲在学习中遇到很多困难。当时恰好住在大伯家的一个邻居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数理化和英语都很好,但他有个缺点,就是由于“抽大烟”搞得很穷。父亲为了请教他,就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省下来作为学费,去请教他各种所需的知识。一段时间后,这个大学生建议父亲去一个法国人办的大学旁听。拍电影通常是晚上九点到凌晨四五点之间,父亲晚上干活,白天的时候就去旁听,逐渐掌握了无线电方面的知识。为了检验自己学到的知识,他开始免费帮人修收音机。后来修得越来越好,成为上海滩小有名气的无线电修理师,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也就开始与社会上的各种人物有了交际。
当时上海有很多商业电台,这些所谓电台,实际上就是一套收发报通信设备,父亲就在不断实践中逐渐掌握了修理收发报机的技术。
有一次,父亲修好一台收发报设备之后,委托人告诉他送到一户人家门口,敲敲门放下就走,其他不用管。但他不知道那是我党的地下联络点,而且已经暴露了。他敲了门,把东西放下刚要走,就被日伪特务抓了。到了警察局,日伪特务审问他、对他拳打脚踢,但他按照事先说好的,“是马路对面一个人给了我一块大洋,让我把东西放到门口,我并不认识那个人。”日伪特务关了父亲一个星期,也没发现他跟共产党有关系,就把他放了。这次事件之后,父亲才知道是给新四军修电台。也是经过了这次考验,地下党组织上认为他思想上是可靠的。
又有一次,新四军的电台送过来让他修,电台的问题是发报机用的大功率电子管烧了。当时日伪对电子元件市场控制很严,很难买到,得用黄金到香港买。正在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一家商业电台也送来维修,父亲看那台设备的同类电子管没坏,就把好的电子管换到新四军的电台上,并告诉对方电子管坏了。对方不信,双方发生争执后,父亲又被警察局抓了起来。最后党组织找人疏通,赔给了对方黄金,这件事才算解决。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父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组织安排父亲进入国民党的中央航空公司工作。当时我们党的一些大宗物资需要从香港购买,国民党海关查得严,钱不方便带出去。后来党组织就想到办法,把钱换成黄金交给我父亲。因为飞机上有很多检修孔,一般人不知道,我父亲作为机组检修人员,会提前上飞机检查,他就把金条放到检修孔里,到了香港就会有人拿走。父亲说,当时的上海龙华机场就有我们的党组织,特殊情况下,龙华机场的电台能够直接跟延安联系。国民党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航空公司里有共产党的电台。
1949年上海解放之前,地下党组织得到了国民党企图把上海比较知名的工程技术人员全部迁移到台湾去的情报,就在国民党特务找到我父亲之前,地下党组织抢先一步,派龙华机场党的负责人华斌同志把我父亲隐蔽了起来,并告知我母亲,不要被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和恐吓所蒙蔽,要千方百计地留下来。在国民党特务把飞机票和手枪都拍在我家桌子上的危急情况下,我母亲按照地下党的指示,不断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终于错过了最后一班飞往台湾的飞机,留在了即将解放的上海。
《祖国》: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先后在华东军区空军第23厂和总参通信兵部研究所工作。在这期间,他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
葛元仁:1949年5月,上海刚一解放,我父亲就被地下党组织安排进入了华东军区空军第23厂担任了技术工作,开始了光明正大地为我党我军进行的军事科研工作。在这期间,父亲有两个重大任务。
第一个是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我父亲负责解决志愿军司令部与各兵团、各军的通信联络问题,他被安排在设计组。因为顺利完成了任务,父亲立功受奖,被第一批调往正在组建的解放军通信兵总部研究所工作。
第二个是解放一江山岛战役前夕。因为父亲被调到总参通信兵总部工作,我们一家人都坐上了赴京的专车,可是车上只有带着身孕的母亲和我与大弟弟,却没有见到父亲。半年后,父亲来到北京后,我们才得知,原来当时他被调去解决一江山岛战役的陆海空通信制式问题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是我军第一次陆、海、空立体协同作战,为此,华东军区成立了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作为华东军区参谋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陆、海、空三军的协调主要是通过通信系统进行,而当时我军这三个军种的通信制式(波长、频率)是不一样的,为了保证陆、海、空三军在战斗中的通信联络畅通,在华东军区23兵工厂负责通信设备研制工作的父亲接受指令,承担起了三军通信设备的制式协调设备的研制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父亲说,为了解决解放一江山岛的三军通信设备的制式协调问题,一直到全部设备经张爱萍亲自验收,移交完成后才离开华东军区,所以晚了半年才到北京。
抗美援朝战争后期,随着我军大规模战役的展开,为了解决各部队间的通信联络问题,在父亲的主持参与下,研制出了我军自己的新一代短波步话机和坦克通信电台。那时我上小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看到父亲课题组的叔叔、阿姨分成两组,开着吉普车在公路上朝相反的方向行驶,并且在车内不停地呼叫,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测试电台的通信距离和性能。抗美援朝结束后,他们中间不少人到家里看望父亲,说起自己研制的电台在朝鲜战场的使用情况时,都是眉飞色舞,一脸的兴奋。父亲因此立了三等功。这也是他在通信兵部完成的第一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民党凭借空军优势,经常派飞机对大陆进行侦查和骚扰。由于我们的侦查、监听设备落后,往往是敌机临近了才能发现,非常被动,为此我国请求苏联帮助。可苏联的设备运来后,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只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干体力活,根本不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参加操作和检修工作。鉴于这种情况,总参下决心自己研制,当时在通信兵部研究所工作的父亲作为课题组长接受了这个任务。父亲主持并参与了为沿海边防空军研制的高频及超高频多路通信和侦察电台设备,最终他们研制的设备技术性能明显优于苏联同类设备,使我国有了自己的第一代军事监听设备。父亲为此立了二等功,进而创建了我军第一个侦察干扰研究室,他被任命为我军第一个负责电子对抗、信息战的“通信侦察干扰”研究室主任。
《祖国》:1964年我国首次核试验时,父亲负责遥控遥测系统的技术工作。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是怎样的?父亲是如何克服这些难题的?
葛元仁:1956年10月,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父亲被调到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负责对火箭的控制系统的研究工作。1960年,为了加速国防科研工作的发展,中央军委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兵部开始筹建为国防尖端电子通信工程服务的第十研究院,调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担任院长、总参通信兵部副主任的孙俊人兼任副院长。第十研究院既负责常规军用的通信,又负责原子弹、导弹等特定武器的控制系统研究开发。
1962年,国防科委下达了无人驾驶爆破艇遥控系统研制任务,这是一项为准备解放台湾的国防急需工程。当时我军还没有进行遥控设备研制的专业人员和单位,我父亲是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侦察干扰(电子对抗)室主任,承担的是防范美制蒋机袭扰大陆的侦察干扰工作。根据国防科委的指令,由父亲带领八名技术人员承担此项研制任务。而后,在父亲带领下,同志们克服了专业新、任务急的困难,全部使用电子管器件制作了超短波调幅电台,实现了控制距离20公里、七指令分频多路传输的遥控爆破装备的研制,圆满完成了这项工程代号为“308-1”的遥控系统工程。“308-1”的遥控系统设备在浙江平湖沿海进行了现场试验时,张爱萍等国防科委和海军有关领导亲临现场,并出席了鉴定会。他认真听取了父亲的汇报后,对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套无线电遥控系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64年,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以张爱萍为主任委员、刘西尧为副主任委员、各参试单位负责人和专家等68人组成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专门负责原子弹的控制系统的研发和执行工作。
据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有个别技术人员在私底下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认为我父亲既不是名牌大学毕业,又没有“留洋”经历,让一个工人出身的“国产”工程师主持这样一项当时最为重要的国家重大项目而感到不解。1993年我调回北京,陪父亲去看望孙俊人将军,当时我也提出了这个疑问。孙俊人将军说,当年院党委是根据“政治可靠,业务突出”的原则进行了认真研究后,由他向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推荐了我父亲负责遥控遥测任务,并获得张爱萍将军的批准,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遥控工程技术团队——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第十二研究室,并任命我父亲为首任研究室主任。
后来父亲曾对我说,张爱萍将军不仅是核试验的一线指挥员,而且是以周总理为主任的中央战略武器研制专门委员会的委员、秘书长,他考虑到我们遥控系统是国内首创,作为整体核试验工作中的中枢神经的重要性和绝密性,以及在美苏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技术封锁下,工作中必定会遇到很多极其困难问题需要全国范围内协调解决,所以要求父亲每周向他汇报工作,以便及时掌握和调整。在张爱萍将军的直接关怀指导下,父亲和他的团队终于完成了建立核试验主控系统的关键性工程。从而,我父亲和他的助手们成为我国遥控遥测工程的开创者、奠基者、技术的带头人。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人民日报》的号外一刊登,举国沸腾。后来从父亲当时的助手樊子麟的文章中我才知道: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曾和基地的“国家核武器试验技术委员会”的委员们商讨,试验成功后立即要给两家记功,其他的回去总结后再说。他建议:一个给飞过蘑菇云的飞行员;另一个他只提条件:“关系全局,成绩突出”。会上,委员们异口同声地说“给遥控!”,提议以国防部的名义给父亲记个人一等功,他所领导的第十二研究室记集体一等功。委员们都知道,遥控遥测系统是整个试验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是通过它联系、协调、指挥了整个试验,也只有它能够将党中央的指令发送出去、试验数据收集回来,为今后的试验打下基础。后来父亲回忆说,他没有想到委员们会那么一致地要求给他记一等功。他说,自己只是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也兑现了自己向毛主席、周总理立的军令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