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者之歌
作者: 吴健
“上海漂亮吗?”
“上海可爱吗?”
这两个概念摆到一起,您会如何回答?至少,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有着25年党龄的王泠一博士向笔者作出了精辟的回答——这种对比,就如同时下青年人常常扪心自问,要“活个精致”还是“活个认真”,“两者会有交集,可哪个更有意义,你会品出味道”!
无论个体的人,抑或千百万人组成的城市,都在社会变迁中被塑造,但同时也参与塑造。“上海的繁华与精致,其实很早就呈现了,但之于社会意义的美好,只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建立人民政权后才能实现。”王泠一坚定地说,“不只我们自己,放眼世界,你同样能发现,世界上但凡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为上海艰苦卓绝的革命解放、持续深化的改革开放,乃至未来可期的美丽绽放而感动,而讴歌,而予以支持!”
无独有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研究员阿夫欣·穆拉维产生同样的共鸣:“1800年,全世界只有3%的人口生活在城镇。1900年,这一比例为15%,尤其20世纪初世界最大的十座城市(包括上海)讲述了西方占据政治经济支配地位的历史。因为19世纪的工业革命,加上迅速扩张的殖民贸易运动,给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带来可观财富,而这是以地球上90%的人坠入灾难深渊为代价的‘阶级城市化’。”这种扭曲的局面,注定要被历史所纠正。
魔都的本原
“魔都”,这个被好多年轻人接受的上海别称,当1923年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创造这一称呼时,内心却充满惶惑,“这是不可思议的城市,充满了魔力”。他无法解释光怪陆离的繁华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在塑造?
“上海的近代化,首先沾染了侵略者的武力掠夺,又经过来华求财的外国资本折射,产生了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影响。”王泠一给笔者展示了一百年前瑞典莫贝格公司(Moberg & Co)驻沪代表G.G·久涅尔别尔格对上海的白描:“上海是中国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人口达200多万,那里贡献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上海是个大都市,拥有相对发达的工商业,它地处沿海,地理位置优越,贸易便利,是中国市场的入口和经济中心。19世纪中叶,东西方列强就从这里抢占中国市场,建立势力范围。上海有电车、高楼,赫赫有名的‘国际天际线’——外滩。有一点不能不坦白,过去的五十余年,列强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主要有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以及日本,他们的做法简单粗暴,无视中国利益,将中国人的利益和尊严踏得粉碎。这在他们发展上海租界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国际法角度看,这个‘国中之国’享有治外法权,在这里适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法律,所以中国当局不享有管辖权。”
怎么解释这种场景呢?王泠一展示了1927年4月15日拍摄的照片,日本帝国海军一等海防舰“八云”号的炮口对准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和在建的江海关大楼,“如果中国人反抗,享有中国内河通航权的外国军舰就能直接镇压,而在平时,列强掌握的旧中国海关和金融机构则在刺刀保护下日进斗金”。实际上,哪怕西方稍有点良知的人对此都不可容忍,久涅尔别尔格说:“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美英法日意等国巡洋舰长期停泊黄浦江,咫尺之遥的外滩洋商大厦、侨民俱乐部和时尚爵士餐厅却散发着优雅风情,这种浪漫无法抹去中国的伤痕。”
“上海是世界上藏污纳垢的场所,这里有数不清的酒吧,有人在里面喝得烂醉如泥,有人在里面买卖鸦片,买卖灵魂,买卖女人的肉体。上海有皮肤黝黑、戴着大头巾的印度巡捕充当公共租界可靠而忠诚的打手,有威严而高傲的英国人充当‘崇高秩序’的维护者。上海是奸商、密探、假绅士和骗子出没的城市,是贪婪剥削的城市,是工人拼死苦干,‘占有者’疯狂牟利的城市。”游历过当年世界几乎所有大都市的久涅尔别尔格不免给上海下了这样的定义,“这是可以大发横财的地方,是冒险家的乐园,到处充满激情,到处又冷酷无情。”
对于这样的上海,1933年2月17日,只为拜望“中国的良心”——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爱尔兰文坛名宿萧伯纳,很不情愿地呆了区区四个小时。有帮闲者吹捧萧翁驾临之际上海久雨放晴,“您福气真大,可以在上海看到太阳”,萧伯纳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这是太阳的福气,可以在上海看到萧伯纳。”萧伯纳对旧上海毫无好感,他对那些记者说:“上海至为恶劣,我对它没有什么兴趣。”请注意,萧伯纳也在上海看到中国的希望,那就是宋庆龄向他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及革命的新情况,离沪前夕,他发表的《给中国人民的短札》直言——“中国人民而能一心一德,敢问世界孰能与之抗衡乎”!
上海在资本主义世界被称为“亚洲巴黎”“黄魔之城”,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注视上海,却源自重重阶级压迫下蕴含的惊人反抗力量。苏联记者A.E·霍多罗夫在1922年所著《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书中提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号召东方各国被压迫人民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1920年4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代表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以新闻记者的公开身份前往中国,名义上是在中国组建一家华俄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在中国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行性”,同行的还有妻子库兹涅佐娃、提供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等,维经斯基也由此成为“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也是西方史学界评价的“最默默无闻的伟大工作者”。
“多少年来,中外专家讨论不休的课题,就是维经斯基为什么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阵地放到上海?”俄联邦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解密档案显示,他们首站是抵达天津和北京,通过在大学任教并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的俄籍教授S.N·波列夫伊(中文名“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中文名“伊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及其周围的革命青年建立联系。然而,北洋军阀势力严密控制的北京缺乏工业,缺乏工人阶级的大部队,在坚持十月革命经验并看重这一点的共产国际代表眼里,封建官僚把持、政治密探遍布的北京暂不具备社会主义运动爆发式成长的条件。后来,维经斯基又拿着李大钊写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另一位重要人物陈独秀,他和李大钊一样,都认同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价值,正引发全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而在中国这一高潮的标准就是1919年汹涌澎湃的五四爱国运动,其中最革命的分子从五四运动左翼分化出来,打算联合起来建立共产党。维经斯基等人还考察过中国另一个政治中心广州,但那里也没有发达的工业。
这就是最后选择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工业城市、无产阶级中心及革命知识分子集中地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乃至远东工作重心的缘故。同年9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人之一V.D·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莫斯科做了有关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远东开展工作的报告,提到“今年5月建立了对不断扩展的工作实行领导的临时集体核心,……所在地定在上海,名为‘共产国际东亚第三秘书处’(一作共产国际东亚秘书处)”。报告强调,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主要出版中心,……秘书处在这里订阅了许多报纸和杂志,我们买到了《上海生活》,中国报纸《周报》等,中国杂志《新青年》(月刊)、《新中国》(已迁至北京)”。10月5日,俄共(布)阿穆尔州委员会也收到一份关于上海政治氛围的报告,里面提到:“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可以公开进行宣传的核心基地。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组织,出版300多种各类刊物,这些刊物全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有时候还举行群众集会。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附有苏俄活动家特别是列宁肖像的文学读物、报纸、杂志。”
国际主义不是虚无缥缈的
在各种因素促进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革命面貌发生根本性转变,接下去无论遭遇再大挫折,这个由先进思想武装起来、始终得到人民无条件支持的政党都能愈挫弥坚,继而走向胜利。同样,每逢中国共产党取得重大胜利特别是在上海胜利时,全世界正义力量都会给予真诚热烈的声援和帮助。
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可以公开进行宣传的核心基地。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组织,出版300多种各类刊物,这些刊物全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有时候还举行群众集会。
1927年3月21日,中共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驱逐北洋军阀直鲁联军,不到十个小时,工人拿下上海华界七个区里的六个区,不久直鲁联军投降,头目毕庶澄躲进公共租界。就这样,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变成红色的海洋。这一消息如闪电般传遍全世界,不仅是苏联,英法德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规模空前的工人学生游行庆祝。当然,最热烈的场景发生在苏联首都莫斯科,有联共(布)党组织书记走到巨大的中国地图前深切地鞠躬致敬,接着从图上拔去标志军阀占领上海的小黑旗,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众人都冲过去用脚踩它,黑旗瞬间给踩没了。无数苏联工人和流亡苏联的各国共产党员上街欢呼,《共产国际通讯》记载道:“莫斯科各工厂都举行集会,演说者在会上阐明了工人占领上海这一壮举的重大意义。”大批工人学生向联共(布)中央机关大楼前的老广场进发,队伍里的中国留学生不断被苏联人围住,他们热烈握手欢呼,有人甚至把几个中国同学扔上天空,落下来再接住!
不幸的是,才三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就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把上海淹没在血泊中,苏联和许多西方国家正义人士的愤怒又是那样激烈,令人印象深刻。莫斯科五一劳动节筹备委员会原打算在游行队伍中陈列一个大型的蒋介石像,向这位北伐军总司令表示敬意,可接到“4·12”政变消息后,他们依然抬出蒋介石像,却是当众烧毁。苏联著名战地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那时候还是小学生,“我们这一代受过布尔什维克教育的人,在自觉生活的过程中,总是记得斗争的上海,它总存在于我们的意识深处,我清晰记得,我们给棒头插着扎成出卖革命的蒋介石样子的稻草人,游行穿越莫斯科全城,接着将其烧掉”。
“我们对上海人民深深的感情和同志般的敬意,绝非突然出现,不,这是久存灵魂中的感情!”多少像西蒙诺夫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是这样强调的,也是这样做的。毕士悌,一个来自朝鲜的军事天才,1919年为争取祖国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他付出“全家尽节”的代价,只身流亡中国。他很快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把反帝反封建视作朝中两大兄弟民族的共同使命,并为之奋斗终身。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已是黄埔军校主任教官、军队仕途光明的毕士悌却坚定跟随共产党,在遍布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受领党组织的任务,辗转来江西苏区,长征中当上红军干部团参谋长,为中革军委打前锋,从乌江一路战斗到腊子口,1936年为掩护党中央东渡黄河身中数弹,弥留之际,他只问了一句:“前方情况如何?毛主席过河没有?”得知毛泽东和党中央已顺利渡河,他才安详地闭上双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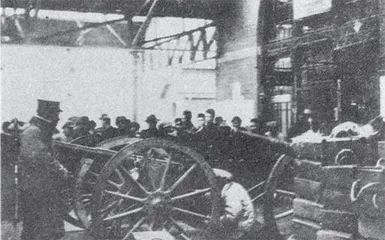
何止是毕士悌,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从不畏惧强暴,他们用炽热的爱给中国革命事业添加浓墨重彩的一笔。“你肯定听说过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这三位美国记者让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形象进一步传播世界,尤其这些工作大多在上海完成。”王泠一提到,这三个美国人的姓氏都以英文字母S为首,人们习惯叫“三S”,“他们于1924-1928年间来到中国,而上海恰恰是‘三S’进入中国的门户,是他们从事进步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他们反映中国革命的报道和著作也基本在这里写作或发表”。
1927年5月,斯特朗乘美国邮轮抵达反动派屠刀挥舞的上海,她遍访孤儿院、教堂和浦东工业区的劳工服务站,确实了解国民党残害共产党和工人的暴行,向世界报道了上海“4·12”大屠杀真相。20年后,斯特朗成功结束在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后又来到上海,住到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忙于写作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她写的关于延安情况的材料,也是从上海送到印度、菲律宾、日本以及欧洲各国去发表的。她在纽约左翼刊物上发表的题为《毛泽东的思想》一文,着重写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思想,介绍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创造,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史沫特莱来华更早,1923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时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华,1929年春夏间到上海,她在上海的“家”成了地下革命活动联络站,苏区重要干部来沪常落脚于此,像红十军军长周建萍就在她家隐蔽养伤。她还不顾个人安危,掩护一些中国同志逃脱追捕。史沫特莱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红军长征消息的外国记者,1931年,柔石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在龙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后,史沫特莱与鲁迅等中国作家一同起草抗议宣言,并译成英文、俄文、日文,在国外报刊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