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科研团队:站在更深沉的高地探索未知造福社会
作者: 华南欢迎来到极限的世界——
在这里,能实现94.8T的最高峰值磁场强度,这是世界第三高脉冲强磁场强度。瞬间冲顶时的惊鸿一瞥,在纪录曲线上留下永恒。
T为“特斯拉”,是表征磁场大小的单位。我们生活的地球,磁场平均只有十万分之五T。
在这里,磁性尺蠖软体机器人以超过1倍身长/秒的移动速度在欢快地“跑动”,是目前报道最快的磁性尺蠖软体机器人。
在这里,铝和物性相差极大金属间的冶金结合变为可能,在强磁场作用下可瞬间“粘合”,成为一种新型轻质复合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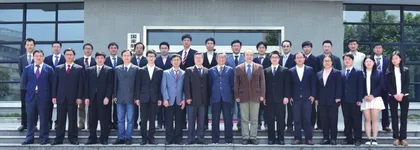
这里是位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简称“强磁场中心”)。实现一项项“极限挑战”的,是几十位70后、80后,和如今越来越多的90后科研人员、工程师队伍,还有他们亲手设计、制造,亲自安装的实验仪器、设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现代科学实验中,强磁场与极低温、超高压一起,被列为最重要的极端条件,要产生更高强度的强磁场,就必须依靠一个“利器”——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高温超导的发现,科研人员急需更高强度的强磁场实验条件开展相关领域前沿科学研究,而此时欧美发达国家已建有30多个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相比之下,由于我国长期缺乏此类装置,科研人员做实验要向国外实验室申请,众多急需开展的科学研究严重受制于人。
为了建设我国自己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14年前,武汉东湖畔,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科技队伍站了出来。
开工11个月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开放实验装置,四年完成脉冲强度从60T到90T的跨越……14年间,从七八人的小团队到八九十人的大集体,从一无所有到世界领先,不断迭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突破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长期战斗在脉冲强磁场科学与技术领域最前沿。
他们设计、搭建的实验装置,在完成强磁场中心科学家们的实验之外,完全面向全世界开放,供世界各地前来做实验的团队使用。自2014年通过验收、正式开放,至2020年底,强磁场中心近7年间累计开放运行时常超过55400小时,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前来进行强磁场实验,国内外97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258项科学研究在此完成,实现了我国强磁场实验条件从“受制于人”到“授之与人”的跨越。
强磁场中心是一个获得过诸多荣誉的集体,2018年获湖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201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21年5月,在得知获得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时,大家格外高兴,“这是属于青年的荣誉,我们是一个年轻、团结的集体”。
从无到有创建中国唯一脉冲强磁场中心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凝聚态物理、材料化学和生命科学等基础科学发展,强磁场装置地位越发重要。200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潘垣敏锐意识到,我国要想在相关科学研究领域进入国际前列,就必须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脉冲强磁场装置。各方几经努力,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建设提上日程。
从2004年7月开始,彭涛、丁洪发、夏正才、陈晋、韩小涛等一批华中科技大学的热血青年陆续加入到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的筹备当中,动笔起草项目申请书。
然而,要起草厚厚一本申请书,对于这群缺少经验的年轻人而言,实在是挑战巨大。“只能找来其他项目申请书,反复琢磨着写,一字一句反复修改。”他们回忆道。大家早已记不清熬了多少个夜晚,经历了多少次的讨论修改,唯一记得的是,即使困难重重,他们从不抱怨,也从没想过放弃。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2007年1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项目正式获批立项。由一所大学承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在教育部高校中还是第一次。
在这些年轻人忙着写立项申请书的时候,华中科技大学校友李亮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母校,建设属于中国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
回国后,李亮和这群年轻人一起,从“绕线圈”做磁体开始,从零开始全身心投入装置建设。当年刚刚读博士研究生的吕以亮,在跟随老师们学习的过程中,他不仅参与绕制了很多线圈,还在老师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不畏艰辛、攻坚克难的科研精神。博士毕业时,吕以亮有很多选择,但他放弃了企业的高薪工作,最终选择加入强磁场中心。回想当初的选择,吕以亮说:“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团队一员,能够在强磁场中心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当时强磁场中心大楼尚未破土,办公条件非常艰苦,七八个老师、学生挤在两间简陋的实验室里,尤其是未安装空调之前,武汉漫长溽热的盛夏里,支撑他们的只有一纸项目规划和心中的梦想。
“2008年4月25日,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破土动工。”不论过去多少年,团队每个人说起这个日子都是脱口而出。对他们来说,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就像他们亲手养大的孩子,每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开工11个月后,中心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样机系统就已研制完成,当年磁场强度能达到75T。也是这一年,韩一波在武汉大学光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后,来到强磁场中心。“虽然最初的规模很小,只有几个年轻老师,以及一个只能放电的电容器,但它吸引我的是,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个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给了我一个方向、有一个希望,这就足够”。

希望如炬,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吸引一个又一个青年工程师、科研人员,既有华中科技大学成长起来的“土著”,也有来自国际知名科研机构和大学的海归学子,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共同朝着明亮的未来疾走。
2010年,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如期竣工,这是首个由教育部高校承建并按时通过验收对外开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填补了我国强磁场装置的空白,为今后我国凝聚态物理、材料、化学、生命等前沿基础学科发展提供了平台支撑。
以85%国产核心部件,解决“卡脖子”问题
2021年五一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近1.5米高、近1米直径的液氦制冷机连着氦气回收装置轰隆隆地响着,近百平方米的实验室里被数个这样的装置和粗粗细细、纵横交织的管子、气囊塞满。一名科研人员在轰鸣声中守着电脑仪器,记录测算。
常温氦气在装置中浸泡冷却,温度降至4K,也就是零下269.15℃,成为低温液氦。作为开展脉冲强磁场下电/磁输运、整数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和自旋电子学等前沿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液氦温区在脉冲强磁场实验室必不可少。通过管道,这些液氦被分配到各个实验室,实验后,它们再升温还原为氦气,通过管道被回收至气囊,经过处理后循环利用。“我国氦资源匮乏,依赖进口,实验用完的氦气必须回收,再利用。这个循环装置是我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强磁场中心工程师刘梦宇说。
沿着走廊再走不远,是韩一波团队设计、搭建的磁光实验站。与初期只有一台能放电的电源相比,现在的磁光实验站由三部分组成,已颇具规模。“这个房间专门放激光器、探测器、光谱仪,隔壁房间是磁体,第三个房间做光学实验。”韩一波介绍着,一脸满足和自豪的笑意。因为实验装置有洁净要求,非实验人员不能随意出入。韩一波隔着实验室窗户介绍,“很多基础性的实验装置搭建,在强磁场中心都由科学家来做。我们设计得非常非常细,一点点试着搭建完成,再调试到最好效果。这些几百公斤重的实验台,都是我们自己抬进去安装好的”。从一间空屋子到一个装备完善的实验室,韩一波和工程师们花了四个多月。
这是强磁场中心的日常一天。在强磁场中心,实验装置每一块电路板的设计图、每一个零件都由科研工作者们自己绘制和安装调试。
核心材料和技术,从来都是“卡脖子”的。强磁场中心团队从没指望等、靠、要、买,他们自己设计器材,自己制造设备,自己搭建实验室,85%以上的材料、部件都是国产。
磁体被视为强磁场装置的心脏。做磁体,是用小指头粗细的导线,绕成线圈,“接上2.5万伏电压,流过4万安培瞬间电流,就可以产生几十T脉冲磁场。但通电线圈会被磁体内部应力拉长和压扁”。李亮说,磁体线圈承受的应力,是“蛟龙”号在7000米海底承受压强的50倍。
磁体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强磁场实验成败。而且磁体绕制没有“回头路”,只能一次成功。“做磁体是手工绕线,绕线的方向、角度都会影响磁体质量。国外实验室都是工人绕线圈,我们是科研人员自己动手。”吕以亮说。

绕制线圈需要用到环氧树脂,因其有强烈气味且有一定毒性,科研人员需要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为了节省穿脱时间,我们早上进入工作间后,一上午就不出来,连水都不喝一口。”夏季,江城武汉气温接近40℃,穿上防护服后更是热得像蒸笼,最初车间里没有空调,后来即便在工作台旁边安装了立式空调,也效果甚微。“每次脱下防护服后仍旧浑身湿透,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吕以亮说。
在青年科研团队的努力下,我国脉冲强磁场装置的理论分析和研制水平迅速跃居世界前列。“李亮主任和教授们提出脉冲磁体非连续性层间加固理论和工艺实现方法,解决了高参数脉冲磁体的力学稳定性问题,大大提高了磁体的性能和寿命,降低了成本。”吕以亮说。
强磁场中心走廊尽头的大车间里,立着两台绕线机,其中早已锈迹斑斑的那台,“是中心科研人员自己设计、制造,已经用了14年,现在还很好用”。吕以亮早已记不清多少个工作日站在这里绕线圈。
2007年至今,彭涛一直负责手工缠绕磁体。从线圈的纹路和颜色,有经验的人能从中看出瑕疵。瑕疵让线圈更早崩溃。“如果浸泡树脂不够充分,反光不同。”彭涛说,他常常“做梦都在绕磁体”,生怕出一点差错。目前强磁场中心常规使用的65T脉冲磁体平均寿命超过800次,远超国际同行350次至500次的水平。
科研经费有限、导体材料不是世界最好,怎样把强磁场实验室搭建好,强磁场中心团队费尽心思。不同科学研究需要不同的磁场波形,为了提高装置运行效率,控制系统负责人韩小涛教授把整个装置设计成模块化结构,由一套中央控制系统精准控制多类电源、多个实验站。“这可以实现在同一科学实验站的同一磁体上产生多种磁场波形,大幅提升我国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的实验效率。”

在装置建设过程中,团结奋进非常重要。“我们拥有一个团结的集体。我和韩小涛、彭涛、丁洪发几位教授,从创始期就在一起,虽然各有分工,但始终团结一致。这个过程中遇到太多困难,有的甚至当时看上去难以逾越,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字。困难面前,我们敢于站出来,去克服、去突破,最后我们成功了。”李亮说。
强磁场中心中控大厅,大小不一的八块显示屏镶嵌在墙体里,每块负责记录不同类型的实验数据。韩一波说:“脉冲强磁场是瞬间消失的磁场,实验要在一瞬间把需要的信号采集好,特别困难,这个难度跟常规实验难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