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房车上
作者: 聂阳欣
在中国,房车不是穷人的退路。保有房车的人群里,最主流的群体是不愁生计的退休老人,其次是年轻的旅行博主,极少一部分人常年在车上生活。
9月,我去成都参观房车展览时,现场看车的90%以上是中老年人,我在其中过于打眼,只好说是搞自媒体的。一位大爷劝我:年纪轻轻的,该找个正经事。
常年以车为家的人,在他人看来或许更加不正经。我所遇见的人里,有不想就业、只靠利息生活的年轻夫妇;有放弃股票、裸辞上路的大厂青年;有退休后终于把自己从社会和家庭的传统义务中解脱出来的老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曾属于城市中产阶层,警觉于日渐僵化而趋同的生活,对城市里的物质欲望和精神焦虑说“我不奉陪了”,企图在路上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和生活,摆脱扎根于城市的状态,重回在大地上游荡的自由。
“生活好像更麻烦了”
阿北和南南是我寻访的第一对正开着房车在路上旅行的夫妻,两人都是“80后”,北京人,皮肤偏黑,像是长期在户外活动。2021年6月拿到定制的房车后,他们从北京出发,先往东去了山东省,再一路西行。我在内蒙古包头市见到他们时,他们刚从哈素海过来,那是一片有着“塞外西湖”之称的天然湖泊,在那里他们用完了所有储备的水和电,几乎是慌不择路地来包头寻找补给。
阿北和南南的房车在福特新全顺底盘的基础上改装,车长约5.4米,外观像一辆普通的封闭小货车。车内壁铺设了地板和隔热板,不足5平方米的内部空间里,满满当当地设置了卫生间、料理台和休息区,休息区可以在沙发卡座和床之间变换形态,沙发对面还留了一块白墙,当作投影仪的幕布。水箱和电路安装在车底,净水箱、灰水箱和黑水箱一共留出大约200升空间,电最多可以储备6.6度,水电是他们在野外生活最大的限制。
我们约在包头老城区见面,我上车后,阿北将车开往郊区,途经赛汗塔拉城中草原,最后停在鹿园旁边的公共停车位上。包头源于蒙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十几年前,市政府修建了鹿园,让这座城名副其实。
南南告诉我,今天的安排是吃午饭、去鹿园喂鹿,第二天也许是逛公园、逛博物馆。他们旅行的节奏很慢,会花上好几天时间来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或者等上好几天,只为了参加一次乡村赶集。
这排停车位一侧是道路绿化带,另一侧紧挨着一片白桦林,三个车位一组,每组之间还有一排绿植,算得上环境优美。此时正值9月中旬,北方大地的暑气逐渐散去,起风时,白桦树的黄叶簌簌落下,逆着光看像金色的蝴蝶在林间飞舞。
两侧的停车位都空着,阿北决定今天的午饭就在这里吃,他从车上把折叠桌、折叠椅拿下来,展开搭好,再搬出高压锅、平底锅、双耳小汤锅、瓦斯炉、气罐、调料,还有两个土豆、一袋花菜、一袋鸡翅根、一大块五花肉,就摆在停车位和白桦林之间的石栏杆上。
因为车内空间小,很多事情需要在车外处理,容易引起围观。阿北和南南尽量选择人少、相对隐蔽的地方。即使开着车窗在路边停着,或者开车门上下时,也经常会被路人凑近观察、询问,尤其是退休老人们。“通常他们会问,你为什么出来玩,你怎么不工作呢,碰上懂房车的,还会聊布局配置。”南南说,“多的时候能说上一两个小时,很费时间,也很尴尬。”
但这次凑近的两个城管不是为了围观,而是来告诉我们:“这里不允许摆摊,不许用明火。” 阿北很奇怪:“为什么?”他刚刚把花菜放进小汤锅里焯水。对方回答:“这两天在评文明城市,抓得紧。”阿北只能把所有的东西原样搬回车里,除了小汤锅,因为里面的水和花菜已经烧热了,只能由南南来端着它。之后我们绕了几条街,找到一条人迹稀少的“断头路”,在路边的凉亭里吃完了午饭。
在路上三个月,阿北和南南已经适应了这样充满变数的生活。房车既是房子又是车,集合了两者的问题。他们坏过水泵,在泥地里陷过车,每周都要清理底盘,检查水箱和水管。有一次天气潮湿,他们的水箱长出一个腐烂的蘑菇。房车的水电依赖外部补给,他们经常找不到“慢充”的充电桩,在不能用水管接水的地方,得一袋一袋把水运到水箱里。房车也不像房子有自足的空间,需要自己把握与外部的边界,为了避免把衣服晒在外面,他们挂在驾驶舱里晾晒,闷久了会有味道。因为觉得在别人的目光中把黑灰水倒入排水口很尴尬,南南要在每天晚上找一个没人路过的排水口。
生活好像更麻烦了,但比起在一个地方定居,他们宁愿在路上。用胡萝卜喂完鹿后,我们坐在树边长凳上闲聊,“我喜欢坐在这里享受晒太阳的快乐。”南南说,她看着远处鹿园门口的检票员,诚心感叹:“我们得感谢这些人的存在,在基层做实事,给国家交税、生育人口,而我们是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
决定上路前,小北和南南放弃的最大一件事是工作。他们在路上每个月的花费大约是5000元,食物的花费占据了一半,其他还包括油费、话费、车的保养和修理费等等。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用积蓄购买的基金,利息基本可以覆盖开支,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想更多地去攒钱。
南南的家人很不理解,在他们的印象里,南南赚钱很拼。二十多岁刚毕业时,南南在北京郊区做导游。单位每个月给两千块租房补贴,她存起来,不花,就睡车里,平时停在单位门口,洗澡上厕所用单位的卫生间,做饭用小电锅。

和阿北在一起后,他们做起小本生意,干了几年,南南不想干了。“我发现自己做不了生意,越挑剔的客户,你越得给好的,而对你客气的,你反倒不用上心,这和‘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不一样。”
阿北和南南关闭公司,在英语零基础的情况下,去了新西兰,想换一种环境生活。头一年每天都在学英语,之后阿北在汽修厂工作,南南四处兼职,当过酒店服务员、超市售货员、农场饲养员、加油站工人,一边体验新西兰的风土人情,一边把花出去的学费赚回来。
南南有一条生活哲学,要想深入了解一个地方,一定要在当地工作,多和人打交道。在人来人往的超市和加油站,南南发现很多新西兰人是以“今天有钱今天花”的态度生活,“他们一辈子都没想过出岛,没钱的时候吃得差一点,有钱了就吃得好一些,他们不攒钱,每天过得也很开心。”
去年因为疫情回国后,他们一度犹豫要不要找份工作。南南想起有一天他们在新西兰自驾游去看银河,附近的旅馆都住满了,他们睡车里,半夜大家都起来看星星,其他人披着衣服冷得打哆嗦,他们在车里开着天窗,显得格外温馨。
小北和南南合计,拿出三四十万买房车,剩余的钱还可以运转,父母有自己的晚年安排,也有其他子女陪在身边,为什么他们不趁着年轻,过四海为家的生活呢?
南南联系过很多房车厂,“一听说我们想定制,就不理我们了。”因为喜爱潜水,阿北和南南希望车内的空间做到干湿分离,潜水后能在车尾换洗再进入休息区,对水电储备、家具配备也有要求。
最后他们找到一家私人改装工作室,由一对情侣开设,男主人哈里曾经在一家车企做汽车设计,女主人荷包蛋是设计师出身,两人从2017年开始住在房车里,自己摸索着改装了几辆车后,把改车作为新的事业。因为喜欢用松木做木板和家具,他们把自己的车称为松木巴士。南南觉得哈里和荷包蛋有实际生活的经验、有合法公告,更关键的是,他们的车多用实木和手工编织物,看起来有“家”的感觉。
去拿车的那天,荷包蛋有些忧虑地跟南南说,这辆车空间小,储物柜可能会不够。南南把东西从随身带的行李箱里取出来,一件不剩地放好,说:“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
然后,他们开着这辆车上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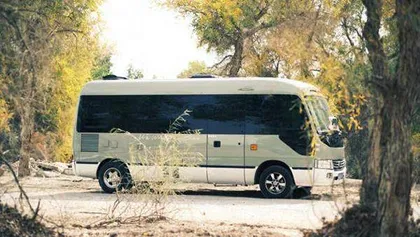


流动的状态
松木巴士更像一个小作坊,除了哈里跟荷包蛋,只有两三个帮工。和很多改装房车的小厂一样,哈里他们改装的第一辆车是自己的“家”。
哈里与荷包蛋以前都在上海工作。哈里的工作地点在嘉兴,租住在上海市区,往返通勤很远,一开始他想对生活做一些温和的反抗,比如买一台房车住在公司停车场,但买完车后他就辞职了。“城市就是一堆人在里面赚钱、花钱,充满了物欲和消费主义。买东西会让我开心,比如我今天心情不好,买一个数码产品缓解,大城市需要消费来弥补空虚,这样的状态和随之而来的虚荣心让我很讨厌。”
荷包蛋也长期处于加班忙碌状态,有时一周去好几个地方出差,一天赶五场报告,身心都在走下坡路。为了放松,她和哈里周末有空就开车去周边玩。
她喜欢在路上移动的状态,“以前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半时间迁徙,边劳作边生活,我们可以实现吗?”荷包蛋和哈里决定,一起辞职,卖掉以前的车,换取两年生活费,在路上探索现代的游牧生活,新生活的口号是:“We wander and share(我们闲逛,偶尔分享)。”
我问哈里,当时有没有想过用同样的钱付一套房子的首付,毕竟房子可能增值,而车一定是贬值的。哈里说没有,“要是算计这些,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荷包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游牧生活时,经常有人评论:“他们家里肯定有好几套房子”“我要是有一个亿我也能过他们一样的生活。”
哈里不以为意,“恰恰相反,你要放弃一个亿才能过这样的生活。”哈里辞职前就知道公司半年后会上市,他手里的股票能套现,但他不想等。
他们买了一辆带旅居车公告的考斯特中巴车,自己设计布局,思考怎样在12平方米的空间里过想要的生活,摸索着在曲面上铺设木板,做木工和软装。水和电则花费了十万元找人安装,但上路后很快就坏了,全部修过一遍后,哈里学会了安装水电。在路上一年后,哈里根据实际体验,又重新改动了隔热材料、布局等。
帮人改车是意外之举。在分享了旅行生活后,几个朋友想要跟他们一样的车,为了赚路费,哈里与荷包蛋尝试着改了四五台车,之后订单越来越多,他们的想法也逐渐转变,从单纯地分享游牧生活,到希望帮助更多人实现这样的生活方式。
刚上路时,荷包蛋会因为天天不工作、游手好闲而感到焦虑,去第一个目的地广西北海时,会因为连日下雨不能赶海而沮丧。可是她发现,他们完全不用着急,下雨的日子就像当地人一样逛逛海鲜市场,在“家”里喝茶看书,等几天后,阳光会出来的。他们不用计划日程,荷包蛋去老挝时,哈里送她到云南边境线,回程路过一片雨林,突然想在这里停留几日,就把车停在村长的院子里,天天跟着村民去雨林采摘食材,学晒干红茶的手艺。
住在车上后,哈里对大城市的厌倦消解了很多。在广州,他们经常坐在车上,隔着玻璃看来来往往的人,“像是在不同的两个时空,或者说,我们只是这个城市的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