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一线的灵魂摆渡人
作者: 杨泽雅
南京长江大桥,市民及游客的打卡地。但在陈思眼中,不只是景点,也是宣泄的出口。很多人在这里欢笑,在这里哭泣,或者在这里死去。近20年来,他每个周末都在大桥上巡逻,目的只有一个——劝生。
由于年岁渐长,陈思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强忍着脊椎腰椎传来的剧烈疼痛,气喘吁吁地跑着。“扑通”一声,那个女人还是死了。陈思眼睁睁看着她跳了下去,在距离自己仅有300米的地方。
这个自己白天曾救助过的女人,又在傍晚纵身一跃跳入江海。
这是陈思最难过的时刻。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两鬓已然斑白,他为自己势单力薄、出手缓慢而深感不安。他不得已返回了桥头,点着了烟,一根又一根地抽了起来。
陈思是物流公司的一名业务员,也是“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获得者。从2003年9月以来,他每个周末都来南京长江大桥上巡逻,目的只有一个——劝生。
“今日平安无事”
这天早上7点,天刚蒙蒙亮,陈思拿着一壶热水,骑上电动车就准备出发。陈思家住在大厂。他要去的地方,是距离大厂将近20公里的南京长江大桥。
在别人眼中,长江大桥是游客打卡的地标性建筑。在陈思眼中,长江大桥不只是观光景点,更是失意之人情感宣泄的出口。无数人在这里欢笑,在这里哭泣,在这里快活,在这里死去。
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以后,有两千多人在此跳桥结束生命,这里成为世界上自杀率较高的地方之一。而更多的人跳入江水,连尸体也找不到。
2003年9月19日,陈思自愿成为南京长江大桥的“劝生志愿者”。陈思工作日上班,周末和节假日就骑电动车往返于南北堡之间,四处巡逻,看到有不对劲的人就跟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陈思在长江大桥做“劝生志愿者”,已救下了403名轻生者。他把自己救人的故事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取名为《大桥日记》。
当天,他在《大桥日记》中写下:上午7点50分到达南堡,下午5点离开大桥,今日平安无事。
而更多的时候情况并非这么幸运。
陈思骑着电动车巡逻,狭窄的桥面上零零散散堆砌着手机、钱包等私人物品。陈思明白,那是轻生者曾经存在的痕迹。
长江大桥边的护栏高1.5米。由于背面没有着力点,攀爬护栏不好借力,个子小巧的女人会脱下高跟鞋,然后纵身跃下。5公里长的桥面上会时不时出现高跟鞋、化妆包、手机等物品,她们为自己精心装扮,体面地离开了人间。春秋天自杀高峰期的时候,大桥上最多十几天出现过90多双鞋,旁边还有现金和手机。这是陈思最看不得的心碎场景。
从多年的救人经历中,陈思得出经验:从南堡数第13个电线杆跳桥的人最多。这里江水翻滚,江面上还不时打起漩涡。很多轻生者说看到有已故的亲人在江里的漩涡中呼唤自己。
从70米高的桥上跳下,身体受到的冲击几乎等同于跳在水泥地上。落水那一刹,人的内脏与骨破裂。有人刚跳下去的时候被救起,看似安然无恙。实际上受到冲击的内脏会缓慢出血,跳桥被救的人最长也活不过10天。
陈思心里堵得慌。他忍不住会想:如果当时我在呢?如果我快一步呢?他们是不是就不会离开?他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头部胀痛,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大桥上的清洁工帮他拿来了降压药,陈思就着水“咕嘟咕嘟”大口吞下。
宿迁老乡频频自杀
1990年夏天,22岁的陈思第一次来到南京。他走在大桥上,火车鸣笛的轰隆声让他感到有些焦躁。
3个月前,陈思和几个老乡一起出来打工。每个人带了100斤大米,就这么踏上了去南京讨生活的旅程。顶着烈日在工地上干活,一点一滴都是自己的辛苦钱。陈思本以为自己年轻力壮,能凭借这股子傻力气赚钱,累点也没什么。他是家中老大,能赚点钱补贴家用,也能让自己在这个城市生活,陈思感到很知足。
3个月后,大米吃完,老板跑路,之前承诺的工资分文未见。有余钱的村民坐大巴返乡,剩下陈思和两个叔叔。三人准备从南京步行回到宿迁老家。“走一步就近一步,还能回不去?”一个叔叔安慰陈思。两个叔叔沿途要饭,要到就分给陈思。三人一路向北,走过长江大桥。那时陈思还不知道,在这座与自己同岁的大桥上,每年有超过百人纵身跃下,结束自己的生命。
过了桥,三人走到大厂,进菜市场要饭。陈思本想吃口饭继续赶路,碰到了早5年来南京打拼的大爹。大爹拦下了陈思,说:“回家干嘛呢,在这儿拾破烂也能养活自己。”
陈思的父亲患有眼疾,父母早早离婚,母亲去了另外一个城市生活。陈思爷爷是抗美援朝烈士,他从小跟着奶奶长大。老家只有三间茅草屋。一家人靠种地和奶奶每月6元的抚恤金过活。

想到自己家中的情况,陈思听从了大爹的建议。从拾破烂做起,有了三五十的本钱就卖青菜,卖水果。1996年在老乡徐阿姨的帮忙下开了家小商店。同年把老家的草房变成了瓦房,并和一个南京姑娘结婚。1997年女儿出生。
陈思这才感觉在南京立足了。
陈思有一天去进货的路上经过长江大桥,看到一个双目无神、失魂落魄的小女孩。意识到情况不对,他将女孩拦腰抱下,还给她买了面包和矿泉水。
跟女孩聊天才知道,女孩误入了传销组织,以死相逼才侥幸逃生。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她狼吞虎咽,享受着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也正是这个时候,陈思知道了大桥上有人自杀。也正是这次,陈思明白自杀的人原来是可以救的。
2003年,陈思从电视上看到,一名宿迁女大学生抱着毕业证书,从南堡一跃而下。同年,电视上频频传来跳桥的新闻,自杀者大多为宿迁老乡。帮自己在南京立足的是老乡,频频跳桥的也是老乡,陈思心里过意不去,决定有时间就上桥救人。
第一个自杀救助志愿者
2003年9月19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陈思走上了大桥,成为大桥上第一个自杀救助志愿者。
大桥上车水马龙。下面过火车,上面走汽车。初来乍到的陈思极不习惯大桥上的异味和嘈杂环境,带了一块心形广告牌给自己壮胆。牌子上面写着:“全社会都来关注自杀者。天无绝人之路,退一步海阔天空,善待生命每一天”,上面还印着他的私人住址和电话。
上桥第一天一无所获。
2003年9月20日,陈思守护大桥的第二天。自认在当地受了三年“冤枉官司”的王裕兴打算跳桥自尽。王裕兴到南京来上访,因为缺少证据,上访10多天也没有结果。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推着一辆载有自己全部家当的自行车,想要纵身跳入江河。王裕兴的异常举动被陈思察觉到,陈思将其拦腰抱下并耐心劝导。
“你给我写个证明,我就不死。”两人僵持不下。
“写什么证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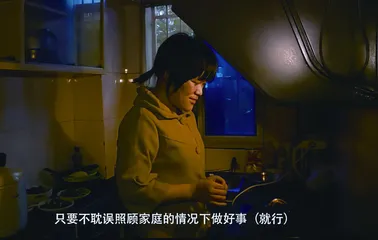
“你要为我证明,证明我受了冤屈。希望当时的见证者能给我提供帮助。”
陈思赶忙拿出笔,写下:王裕兴同志蒙受冤屈。时过境迁,证据失效,希望目击证人能提供佐证。署名陈思。
王裕兴神色稍缓,他不想死了。蒙冤多年,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信任。这封没有印章,无人公证的证明书让他觉得或许还有希望。
陈思救人的事情吸引了媒体的关注。自那以后,陈思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大桥守护者”。王裕兴的冤枉官司也顺利解决。为了弥补王裕兴的损失,赔偿给了他15亩地,包30年。
这次的救人经历给了陈思很大信心。之后每个双休日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陈思都守望在大桥上,搜寻那些神情仓皇、心事重重的徘徊者。
大桥全长4.5公里,骑车往返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骑行途中,陈思常常要留意行人的神色,一看到不对劲的,或是随即停下来沟通,或是伺机而动。他抱着“宁可误会,不可放过”的心态,见人在江边徘徊就上去搭话,被骂过无数次“神经病”,甚至有人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救人救多了,陈思的直觉变得十分敏锐。百米之内,只需一眼,他就能看出对方是否有轻生的念头,其结果也常常八九不离十。
最初在桥上救人时,陈思发现状况不对就拦腰抱下,然后打电话交给警察。因为救人,陈思接受过多家媒体采访,还获得过“道德模范”“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中国好人”等多项荣誉。被救的人都交给警察处理,得到好处的却是陈思。时间一长,难免让警察觉得不公平,他们评价陈思的做法是“沽名钓誉”。
自掏腰包办“心灵驿站”
轻生者离开大桥,并不意味着事件的终结。他们被带进派出所后两个小时左右被放出。想不开的人可能会再次自杀。陈思曾眼睁睁看到自己白天救助的女人,曾承诺要好好生活,又在傍晚纵身一跃跳入江海。

陈思感觉这么做“治标不治本”。他决定救人之后把轻生者带到附近的小旅馆,进行陪护疏导。没过多久,旅馆老板看到报道,认出陈思,把房钱退给他,请他吃饭喝酒,请求他不要再来了,说:“人要是死在我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2006年12月1日,陈思在大厂附近租下两室一厅,每月租金1000元,用来接待轻生者,取名为“心灵驿站”。驿站装潢简单,有男女宿舍两间共4张床铺,免费提供吃喝和心理咨询。
陈思一般先把人控制着,然后驮回驿站。轻生者起初会怀疑自己遇到了骗子,陈思就使用激将法:“你死都不怕还怕我给你卖了啊?如果我把你困难理清了,让你找到希望,你再跳也不迟啊。”劝人的方法也非常简单直白。在驿站的餐桌上,陈思贴上了“饭一定要吃,泪一定要流”的标语。根据多年救人的经验,陈思得出一条结论:能吃好,哭出来,这个人就好了一半。对待不愿吃饭的轻生者,陈思劝诫道:“你要是在桥上死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在我的驿站死我要坐牢的。”一般轻生者都会乖乖吃饭。
救下、带回、安抚、安置,陈思的救助工作在这里有条不紊地进行。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陈思的背后,是一整个志愿者团队。在各个高校导师的带领下,社工系、心理系的学生自愿加入陈思的志愿者团队,帮忙进行疏导;也有陈思朋友圈的老朋友和一些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愿意为劝生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据陈思介绍称,心灵驿站17年来共有五六千名志愿者。
除了心理疏导以外,志愿者团队还集资做公益。因没钱上学而跳桥自杀的学生,他们就资助过七八个。
劝生多年,陈思试着总结轻生者的心态。近些年,心理疾病、家暴和感情问题成了人们轻生的主要原因。陈思称:“自杀的人往往有多重困难,这只不过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大桥日记》中,陈思这样写道:我希望自己能做一支蜡烛,给他们一丝光明和希望。我相信人的力量,大家一起帮忙,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然而有些坎儿,终究得靠自己才能迈过,需要过坎儿的人当中,也包括陈思本人。
“我既救人也杀人”
那些在他无法守望大桥时轻生的人,甚至他已经救回的人所带来的愧疚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陈思的神经。
陈思曾经问过自己:如果只是周末上桥救人,那周一到周五上桥自杀的人,就这么放弃吗?他为此备受折磨。陈思每每看到有人上桥自杀的新闻,内心就无比内疚。他避免不了会想:如果我工作日选择去救人呢?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了?养家糊口和爱心驿站的支出都来源于工资,陈思知道自己不上班并不现实。他无能为力,每每想到只是徒增自责。
每次陈思救人,大桥上都会堵车——只要有一辆车看热闹,后面的车便一步也走不动。救人时间长了,车上的人不耐烦,就探出头骂:“妈的,赶紧跳。”公交车上的人会打开车窗,由一人领头,挥着胳膊,数“一二三”,接着全车几十号人齐声大喊:“跳!”轻生的人逐渐变成小点,消失在江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