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三叠”
作者: 李韬先说点你可能不知道的——
豆腐是汉朝人刘安发明的;
潘安开了“悼亡诗”的先河;
张飞的生日是阴历八月二十八;
最早采煤制陶的是大诗人白居易;
石榴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中国的;
浙江“义乌”的由来跟乌鸦是孝鸟有关;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制鸢高手;
胡芹因产于河南省柘城县胡襄集而得名;
少林寺因坐落于少室山阴茂密丛林中而得名;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八卦?有点“标题党”?
你还别不信,这些都有来源依凭和史料支撑。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有云:“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宏阔视野需要知识结构的不断搭建,口才便给需要横跨纵贯的文字组织。
“广文眼力自超然(宋杨万里《四印室长句效刘信夫作,呈信夫》),智谋勇略已过人(宋徐钧 《吴汉》)”。
张广智一如其名,博洽又淹贯,脾气还活泛,极富幽默感。
“休而不退”期间完成《豫东 豫东》《故乡炊烟》两本故乡散文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辛丑岁尾、庚子新正武汉疫情迅速蔓延全国,人人裹足,家家闭户,张广智又利用居家隔离的有限空间、春节前后的有限时间、捉襟见肘的有限资料完成专著《郑州 郑州》,钩沉历史,烛照古今;
“宜将剩勇追穷寇”,办理了退休手续后,终于“解放了”,本来完全可以放飞自我了,但又“退而不休”,文思泉涌,奔突不竭,以我手写我心、写我见、写我闻、写我思、写我感,又回到独擅胜场的故乡叙述,捧出散文集《龙子湖》,“雅正”于四方达人,“笑纳”于各界贤喆。
饱满的人生,原不计无数个阴晴圆缺;丰足的阅历,积淀下多少次起转承合。
别人眼里的云淡风轻,需要舍我其谁的笃定;看似范氏般宠辱不惊,烙下铁马冰河的曾经。
因为老乡和地缘关系,张广智“故乡散文系列”中的每一篇我都有莫可名状的亲近感:家长里短,俚语方言,苦涩青春,懵懂少年,藏在记忆深处,珍庋心间;人情世故,巷议街谈,鸡毛蒜皮,碎语闲言,无不日思夜想,梦绕魂牵。
一年一本,“匀速”前进;大著皇皇,文字熠熠;渐成规模,初具体系。
也到了该“总结归纳”的时候了。
知其所自,先望来路。
一叠从《豫东 豫东》到《故乡炊烟》
说起故乡,想起小河,想起炊烟;想起乡亲,想起玩伴:总有温暖,萦绕心间。耳边也开始回荡起《只有河南》:“一年又一年,往事如云烟。归来又走远,在天边。待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我们的故事,已千年。金黄的麦田,生长在家园。在那河之南,在人间。待你归来时,沧海变桑田。我们的故事,已无言。我的过去啊,我的未来啊,就在转眼间,化成金黄一片;那些往事啊,那些故人啊,来不及沉淀,风吹起又飘散……”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故乡已经成为“再也回不到的从前”。
再加上近两年疫情反复,一条条禁令,一道道关卡,连春节“返乡”都被异化成了“恶意”,“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宋之问《渡汉江》)。
故乡,最后仅为心灵深处最后一抹记忆,只有通过文字让她流传。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唐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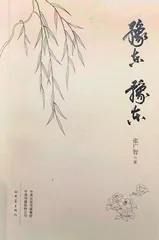
想念故乡,主要是想念那里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老少爷们,想念并不如烟的往事。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匆匆那年,并不遥远;张广智时常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
奶奶27岁就守了寡,屎一把、尿一把地把4岁的父亲和2岁的姑姑拉扯大,孤儿寡母苦不堪言。奶奶为了烧一炷高香,曾披星戴月步行到太昊陵;一双小脚,日夜兼程——来回可是400多里路程啊!
村里的朗爷会捏骨,给谁捏骨都不收分文,你要给钱,他给你急。“乡里乡亲,都是咱姓张的一家人。我不过动动手,收什么钱?要拿钱到别地儿看去。”
高中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环球响彻《东方红》。张月清老师让大家写一篇相关内容的作文,有个同学把《东方红》错写成“东发红”,老师气得不轻,同学抹着眼泪狡辩道:“东边不发红,太阳咋升起来。”老师“噗嗤”一声笑出声来:“发红就发红吧,你看这事。”
上大学时,张广智有句名言“有白面馍吃,还要菜,作得不轻”。他很会过,同寝室的室友都有了存放自己“金银细软”的专属箱子,他却一直舍不得买。最后是父亲亲手给他做了一个纯手工的木箱,用一辆二八永久自行车,从柘城运到开封,全程二三百里。“父亲答应着骑上自行车走了,已经转弯看不见了,我仍噙着眼泪,站了很久。”
看得人也眼泪汪汪的,眼前不由得浮现朱自清的《背影》,也不免想起当年自己上学时父亲给自己送东西的场景。此正所谓“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豫东 豫东》有篇《酒喷儿》说道:“没生活做基础,写不出好文章呀!”
虽为“酒喷儿”,存焉至理儿。
小时候看焰火,袄兜里装着父亲当劳模奖励的“英雄牌”钢笔,被挤成了几段,回家挨了父亲一顿暴揍;
有一年让玩伴赔东西,只穿条裤衩没地儿放,就用两手拢着把朝天椒放在肚子前,结果火烧一般,疼了三天;
一次带团出访,在迪拜机场经停,XO、威士忌、伏特加“三盅全汇”,吓得服务生直摆手“NO”个不停;
王蒙84岁来郑州讲学,席间有人劝酒,王蒙却之曰:“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可不能在郑州去了,在郑州去了,你们得赔。”
张广智从小就偏科,偏得厉害。
有次拿着奶奶给的一毛钱去买煎饼,他怯生生地问:“煎饼多少钱一张?”“五分。”“一毛钱两张卖不卖?”卖家诧异地看着这个小朋友,爽快地说:“卖!”
这次买煎饼的窝囊事,被小伙伴们好嗤笑了一阵子。先天的不足,铁定的弱项,那时候也没有“一对一”和“猿辅导”,高考时数学只做对了两道题,得了14分。
感谢那个文化无比饥饿的年代——不拘一格降人才!
件件真人真事,原音重现,恍如昨天;桩桩糗事趣事,毫不夸张,一大箩筐。
多年练就的“火眼金睛”,张广智善于观察生活,睹常人所未见;注重捕捉细节,知凡人所未知;勇于虚心求教,懂别人所未懂。
蝈蝈你能分清公母吗?
张广智就知道——
公的会叫,母的不会叫。
公的头上有两根很长的触须。
母的屁股上有很长的马刀形产卵管,产卵时把产卵管插入土中。
(《豫东 豫东·蟋蟀与蝈蝈》)
斗鹌鹑是用公鹌鹑还是母鹌鹑?
张广智小时候看过大人斗鹌鹑——
用于斗的都是野生的公鹌鹑。
并不是野生的公鹌鹑都能斗,按年龄、毛色,公鹌鹑分为处子、早秋、探花、白堂四种,只有白堂会斗。
(《豫东 豫东·斗鹌鹑》)
这种“爱学习”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他就曾向鸟类专家李教授“不耻下问”:啄木鸟那么高频次地凿击,为什么不头晕?
经过李教授一番讲解,他也能娓娓转述、化为己出:啄木鸟的头骨疏松而充满空气,头骨内部还有层坚韧的外脑膜,在外脑膜和脑髓之间有一条狭窄空隙,充满液体,可以消震。头两侧生有发达的肌肉,也可以防震消震。我们现在常用的防震帽盔,就模仿了啄木鸟头部的结构。
《豫东 豫东》《故乡炊烟》中有多篇人物特写,观察精微,肌理细腻。虽然文字不长,平易如邻居老张,近人如隔壁老王:敦厚实诚,俳谐达观;华光内敛,哲思在焉。远,不亚于曹雪芹对大观园各色人等的入木刻画;近,不输于冯骥才对天津卫“俗世奇人”的传神描摹——
大队干部穿大氅,一般不真穿上,而是披着。有点风一刮,衣摆鼓荡起来,一个人占几个人的位置。快滑落时,两个肩膀一耸,大氅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故乡炊烟·大衣》)
你闭上眼睛,老师傅把你的上、下眼皮也要伺候到,让你觉得,刮过后,你的眼睛清了、亮了;还有鼻子呢,鼻毛又不是胡子,露出来干啥。老师傅向上扒一下你的鼻头,两个鼻孔自然暴露无遗,那剃刀刃锋在鼻孔里转了两转,鼻毛纷落,你感到鼻孔一下变空了,变大了,顺溜得吸气都省一半劲儿。还有,耳朵,这可是见功夫的所在。你想,耳朵那构造,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可不像面部平整开阔。那剃刀可是锋利无比,老师傅用刀的角度、力度,都恰到好处,真乃运斤成风的高手。
(《故乡炊烟·剃头》)
运用对话,还原场景;生动真实,如临其境。
《豫东 豫东》有篇《退休经验》,有段与领导的对话——
“怎么样,退下来适应吗?”
“适应,适应。以前没有退休经验,知道退休挺好,不知道恁好。”
《豫东 豫东》还有篇《苏金洛》。河南农大的苏教授是林业专家,他到新县挂职副县长,那儿的银杏不结果,经苏教授“用手一摸就结果了”。挂职期满,苏教授回郑州前的送行仪式,有段对话让人笑倒——
县办公室主任:老苏这么神,树一摸就结果,我们新县姑娘一个漂亮过一个,万一哪天哪个姑娘给苏大教授握个手,怀孕了,你们说怎么解释?老苏掰扯不清,再受个处分,我可不忍心看领导出事。
苏金洛:你这人,平时开开玩笑,今儿在我们领导面前瞎掰,不够意思。
县办公室主任:俺是怕领导犯错误,还不被理解,我自罚一杯。
县长:老弟(苏金洛)你那手以后还真得放稳当点儿,别胡乱摸。
《故乡炊烟》有篇《接生》,里面有段接生婆与男人的对话,也让人喷饭——
“你有本事,媳妇给你生个带把的。”
“谢婶子(谢大娘)。”
“谢我干啥?那是恁两口子的本事。”
《故乡炊烟》里还有篇《猪年说猪》,有段对话,像赵本山、范伟在演小品,极富画面感,“笑果”很明显——
公社书记问二叔:这一窝下多少猪娃?
二叔一紧张:下了13个书记。
支书一听坏了,赶紧捣了二叔一下,二叔更紧张了,赶紧改口:不是,不是,书记下了13个猪娃。
他就像一位素描高手,临渊摹笔,高度概括;物象特色,轮廓凸显。这不仅需要超强的驾驭全局、写生提炼能力,更需要删繁化简、精准表达技能。
高中毕业那年春节,张广智为自家大门撰写一副对联:柘城无柘,好栽杨柳万株;洼张不洼,能蓄良田千顷。横批:家乡信美。吸引了不少父老乡亲,驻足议论。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是“文化自信”。
年轻时张广智也曾梦想着有一天,拿一本自己写的书,在故乡蒋河的臂弯里,或躺或坐,累了就用书盖住眼睛眯一会儿,懒洋洋地待上一下午,那该多么地惬意啊!
现在的问题是:《豫东 豫东》OR《故乡炊烟》,拿哪一本好呢?
二叠从《郑州 郑州》到《龙子湖》
如果说豫东是张广智的第一故乡,那么郑州就是他的第二故乡,工作、生活、成家、立业,直至退休,弹指一挥,四十载矣。
大学毕业分配到花园路东的河南省教育厅,退休至花园路西的河南省政协,直线距离不超过500米。从东到西,也终于明白了和收获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