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修改与“个人求助”的法律规制
作者: 刘斌2020年7月到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施行4年的《慈善法》进行了执法检查。后续的执法检查报告(即2020年10月1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发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特别关注了“互联网衍生的慈善新挑战”。该报告提及在互联网背景下,互助行为已经延伸到每一个网络用户,由于《慈善法》没有将“个人求助”纳入“慈善”范畴,“个人求助”行为不属于慈善募捐,但又影响巨大,目前存在法律规制的空白。因此,该报告建议在修改《慈善法》的方案中要增加网络慈善专章,在系统规范网络慈善制度的同时,填补“个人求助”法律规制空白。“明确个人求助的条件和义务,加强平台责任、审查甄别、信息公开、风险提示和责任追溯”。
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社建委启动《慈善法》修改计划,委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等5家机构起草专家意见稿。《全国人大常委会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慈善法》修改位列预备审议项目中,这意味着今年《慈善法》的相关修订工作有望进入审议环节。此次修改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网络慈善与“个人求助”的法律规范协调。
现行《慈善法》自2016年制定与施行以来,有关“个人求助”与“慈善”的关系问题讨论持续不断,不少事件和案例在社会中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016年底,“罗尔事件”开启了《慈善法》时代有关“个人求助”法律规制问题的大讨论,而轻松筹、水滴筹等为“个人求助”提供筹款服务的商业化网络平台则将“个人求助”的争议推向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仅2019年,水滴筹就出现了3次公共性事件,包括吴鹤臣“百万募捐”事件、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个人求助”首案以及水滴筹“扫楼”事件,而中华儿慈会9958项目也因“吴花燕事件”而引发争议。
“个人求助”行为的法律性质
那么,什么是“个人求助”行为,什么是慈善募捐行为,在法律上怎么区别呢?
2016年《慈善法》出台之前,两者的区别似乎并未特别引起公众注意,都被认为属于互联网筹款“公益众筹”。《慈善法》制定过程中,这一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并逐渐清晰,2015年《慈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已经出现“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不得采取公开募捐方式开展公开募捐”“没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和个人擅自公开募捐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表述基本为《慈善法》正式条款所继承(第26条、第101条)。因此,“个人求助”行为与《慈善法》上所否定的个人募捐是两回事。

《慈善法》确认慈善是具有公益性的民间活动。《慈善法》第3条界定的“慈善”范围与《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公益事业”、《信托法》公益信托的“公共利益目的”范围基本重合,从外延上等同于“公益”。但大慈善在内涵上却不等同于公益。公益是现代慈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指慈善活动的受益人为不特定的公众,即使最后落实到特定人(群),这些特定人(群)的筛选也要事先设定相应标准进行严格甄别。同时《慈善法》对从事公开募捐又设置了行政许可,只有获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才可以进行公开募捐活动,没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如果要进行公开募捐活动,那就需要和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进行合作。否则,就是《慈善法》给予否定评价的“非法募捐行为”。
《慈善法》对非法募捐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但是这里的非法募捐,包括非法个人募捐,只是主体不符合,其内容依然需要符合慈善的基本条件,没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如果想要从事公益性的慈善活动,为不特定的公众受益群体募捐,不能擅自进行,而是依法进行合作募捐。如果连这个目标意义的“慈善”都不符合,那就不是非法募捐行为,而是属于《慈善法》第33条规定的另一种禁止性行为,即“假慈善”。而《慈善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骗取财产”。
“个人求助”行为既不是非法募捐行为,也不是假慈善行为,而是个人由于自己及近亲属或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疾病、灾害等困难,致使生活陷入困境,从而向社会求助的行为。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因此,个人向社会求助就是合法正当的基本权利,在社会流动性不那么大的年代,这种求助行为基本上限于社区或者单位,城乡社区组织和单位也会开展一些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来帮助困难群众。随着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性急剧加强,这种求助行为就超越了熟人社区,尤其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之后,“个人求助”行为主要依靠网络媒体来进行,让“个人求助”行为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个人求助”行为的受益人具有特定性,拿出财产来帮助求助人的行为构成了民法上的赠予关系,这种关系与慈善募捐行为形成的慈善捐赠关系不同。慈善捐赠关系存在捐赠人、受赠人(慈善组织)和受益人三方主体,虽然捐赠是在捐赠人和受赠人之间进行,但作为受赠人的慈善组织并非捐赠协议的受益人,它们只是中介,依法依协议根据公益性原则和慈善目标,为捐赠财产寻找合适的受益人。因此,捐赠合同是一种特殊的赠予合同,构成了慈善领域的基础法律关系,法律为这种捐赠关系提供种种制度激励,例如捐赠人所得税抵扣制度。由于慈善组织这一中介的存在,在实现制度激励时,截断了捐赠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合谋可能。
“个人求助”行为形成的赠予关系,虽然也是赠予人为帮助求助人而自愿无偿拿出财产,但这种行为本身无法确证其公益性,不能成为赠予人获得慈善法激励的条件。但这种行为依然属于赠予合同,受到一般民法或合同法的制度规范。
自《慈善法》施行以来,个人求助行为一直被排斥在“慈善”的范畴之外,但因为其又是宪法基本权利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合法正当的行为,受《合同法》和《民法典》的规范调整。
在慈善募捐和个人求助之间,还有两类行为需要特别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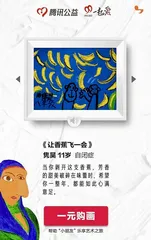
第一,为近亲属以外的他人进行求助。这类行为需要具体分析,如果筹款人的行为获得了受益人或受益人近亲属的同意,那么这构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在媒体上发布求助信息是以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活动,诸如水滴筹、轻松筹等提供“个人求助”信息发布的网络平台,实际上也是一种代理人或中介的角色。如果筹款人的行为没有获得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近亲属的同意,例如为陌生人转发“个人求助”筹款链接,那么这种行为就类似情谊行为,但有些人自身具有较大的公众影响力和信誉,例如网络大V、明星等公众人物,他们的转发会形成特定信任关系。因此,这种未经受益人或受益人近亲属同意的行为,依然可能需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后者对于求助信息真实性的甄别,同样很重要。
第二,慈善组织为特定的受益人从事募捐活动,到底是慈善募捐还是为“个人求助”提供服务。前面提到的“吴花燕事件”和“一元购画”都是与此相关。慈善组织在设计、运作慈善项目时,可以前置审核受益人,让特定受益人作为宣传案例进行慈善募捐,但必须明确告知捐赠人和社会公众,所募款项进行的是具有公益性的慈善活动,而不是为了那个作为宣传案例的特定人。
互联网背景下的慈善募捐与“个人求助”
从最广泛的涵义上,互联网筹款可以理解为个人与组织出于公益慈善或帮助特定个人的目的,借助互联网平台,面向社会发布的筹款项目及其过程。互联网筹款在2016年《慈善法》出台之前就已兴起,最初在网站和论坛上发布相关筹款信息。早期的互联网筹款并未区分筹款目的是为公益性的慈善还是私利性的个体。《慈善法》施行之后,互联网慈善募捐和互联网“个人求助”开始分流,但法律上的慈善观念(公益慈善)和日常生活中的慈善观念(无偿帮助他人)在公众眼中,依然难以清晰区分,造成实践上的一些困扰。同时,近些年在“个人求助”领域出现的如骗捐、诈捐、筹款使用不当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网络个人求助充分发挥其帮助缓解个人和家庭困境的作用,也冲击着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及相关法律体系,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在实践中,不仅出现了年均筹款超100亿元的水滴筹等大型互联网“个人求助”服务平台,影响力远超互联网慈善募捐信息平台,而且慈善组织也纷纷进行机制创新,尝试将个人大病救助纳入到慈善体系中。例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等共同设立的儿童大病救助基金,充分发挥慈善组织的专业性帮助个人进行网络大病求助;中华儿慈会9958儿童大病紧急救助项目,搭建在线平台整合资源,建设有效的困境儿童紧急救助体系。但由于法律法规和观念的限制,这些实践困难重重,而且颇受争议。
慈善法执法检查报告指出,2016年的《慈善法》仅仅将互联网视为一种信息传输渠道,忽略了其支付场所和生活场景的功能。因此,对新问题的规范不足,这个判断既对网络募捐有效,也对网络“个人求助”的法律应对同样有效。

2021年11月4日,民政部发布《关于指定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公告》(民政部公告第516号),新指定字节跳动公益等10家平台为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自此,现有的互联网慈善组织募捐信息平台增加至30家。根据调研,截至2022年初,水滴筹平台已经连续4年全年累计筹款突破100亿元,轻松筹自2014年成立以来,年均筹款也超50亿元。而同样为慈善项目服务的民政部指定募捐信息平台,2020年20家平台筹款总额才82亿元。其中,筹款量最大的腾讯公益,当年筹款约38.5亿元,超过20家平台筹款总额的四成,2021年腾讯公益筹款逾54亿元,但也只是水滴筹的一半。
业内人士多次指出,目前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存在制度障碍,不仅是执法检查报告中所指出的,限制了募捐渠道、影响了实际筹款效果,而且是目前法律上规定“指定”形式本身造成了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低效。一方面缺乏对“指定”形式的行政法确认,到底属于行政委托还是行政许可;另一方面,目前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混淆了信息发布平台和募捐服务平台的功能,掩盖了作为募捐服务中介的互联网平台的市场性,其准入与退出机制过于僵化。虽然2021年新增加的10家平台,可以通过短视频等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但由于市场机制的限制,筹款规模的增加幅度势必受到很大影响。
在互联网背景下,无论是为慈善募捐提供服务,还是为“个人求助”提供服务,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实际上就是中介的角色,与筹款人和捐款人一起构成了三方主体,确立中介合同关系(以前称居间合同关系)。因此,两者可以在同一逻辑之下进行法律规制体系的建设,从而跳出“个人求助”是否属于慈善范畴的争论。
以平台为中心的互联网筹款法律体系建设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曾将互联网公益慈善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基于门户网站和论坛的公益慈善信息传播阶段;二是在社交网络、电商、网络支付支持下的互联网捐赠阶段;三是公益借助互联网技术融入生活场景阶段。
《慈善法》文本针对的是第一阶段,该法中的慈善信息平台,指的是在平台中发布和传播公开募捐信息,使捐赠人能够通过信息,通过信息中包含的捐赠渠道实现慈善捐赠,2017年《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和《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出台时,对平台的定义也是“通过互联网为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发布公开募捐信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但事实上,第一批公开募捐信息平台被指定时,它们已经可以提供支付渠道了,也就是捐赠人捐赠给慈善组织的财产可以在信息平台中短暂停留,并且可以利用微信、支付宝等非银行网络支付通道,这已经处于陈一丹说的第二个阶段。因此,这些平台不仅可以提供募捐信息发布功能,而且还可以提供募捐服务功能。这两种功能的区分意义非常重大,第二个功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而《慈善法》规定的只是信息发布功能,对平台的合法性认定尚未确定是行政委托还是行政许可的“指定”方式,现实中采取的是成立遴选委员会,由委员投票的方式进行遴选。这是一种非常不经济的做法,对于信息发布功能并无太大影响,而对于募捐服务功能,则不利于形成一个成熟的市场。

因此,目前在《慈善法》的修改语境中,无论是互联网“个人求助”服务平台及其所属主体、慈善行业界、学术界和政界都想在《慈善法》的体系下对“个人求助”(尤其是互联网“个人求助”)和互联网“个人求助”服务平台的呼声非常高,进行适当规制。
然而,“个人求助”因为缺乏公益性无法纳入法律上的慈善范畴,《慈善法》对之进行规制显得有些合法性不足。目前已经有地方立法对“个人求助”进行相关规范,例如《江苏省慈善条例》《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办法》等,除将民政部等四部门发布的《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中“风险防范提示”和“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人负责”等条款进行确认外,也规定了平台对信息真实性的适当审核义务。但这种规定是建立在明确区分“个人求助”行为和慈善募捐的性质之上。因此,《慈善法》修改过程中,“个人求助”行为纳入慈善范畴的可能性不是太大,最多是将附则中群众互助互济活动条款进行扩展。
当然,从规范网络慈善的制度设计而言,首先要为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发展留出空间,应采取原则立法和配套制度的模式;“个人求助”行为本身不宜纳入慈善范畴,但互联网背景下为众多“个人求助”者提供服务的活动却具有公共性。
慈善组织可以想方设法创新设计大病救助的慈善项目,吸纳原本通过“个人求助”方式接受社会帮助的受益人群,慈善组织也可以与互联网“个人求助”平台进行合作。同时,为“个人求助”提供服务的网络平台,因其中介性将原本“个人求助”的点对点模式发展成为多对一,甚至多对多的模式,这本身就是公共性的具体表现。因此,互联网“个人求助”服务平台已经构成了一个公共服务市场,这种服务市场与网络募捐信息平台提供服务的逻辑并无不同,都是一种特殊的筹款中介,与目前存在的其他类型的互联网平台的“中介性”有共通之处,可以进行合并分类监管,形成准入和退出机制统一、健全的互联网筹款服务平台市场。
当然,这有待于社会公众和慈善行业人士积极参与《慈善法》的修订过程,共同推动互联网慈善的法治改革和制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