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有所寄》:为土地留存一份记忆“母本”
作者: 贺小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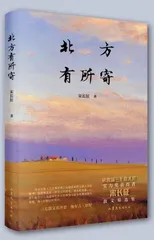
他是一名理发师,现在就居住在距离出生的乡村仅有十里的镇上。他深爱着文字与剪刀。他说,在给人理发的那一刻,剪刀仿佛长在了手上,每一个发型都是用心完成的作品;在写下文字的那一刻,笔就联通了心神,每一篇文字都与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村庄血脉相通。他是农民理发师、山东省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宋长征。
宋长征说:“写作这本书,我是为自己解惑,也想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提供一个可以按图索骥的母本,以便多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在纸上找到自己水草丰茂的家园。”书中,作者记录、描绘了许多乡村生活场景,并关注农民的生存与命运,尤其写到了乡情、母爱。他的乡村经验是丰富的、驳杂的、温暖的、深情的。
存在与失去,很好地界定了当下乡土文学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一边是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生活,一边是即将消逝的乡村与乡土——但我们又不能断然确定从此会失去乡村生活。这让作者有了一种“挽留式”的冲动,由风物进入,由记忆进入,由物与人进入到一种多层次、串联起时空的书写。
“我从来不以为痛与美是对立矛盾的关系,恰恰因为对美的追求,让我们对痛的感悟更为深刻。因为美,艺术之美,文学之美的存在,才让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为迫切。”在文学表达上,宋长征以对美的追求迎向生活的真实与疼痛,用痛苦将美之为美的含义再加深一层。他用美的笔触点染大地上的一个个痛点,去写北方被冻住了的天空下回旋着的猎猎长风,写天空下的人们,是怎样用坚硬而谦卑的骨头,扛起了一整个生生不息的人间。而在这样平凡而残酷的人世间,最坚忍温柔的字眼,是母亲。
他写母亲纺棉,“右手轻摇纺车,左手扯着棉线。一片小小的云朵,就成了农家日子的线索。沿着这根细细长长的线索,就找到了一个家的诞生之源”。写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对自己美学观念的影响,“母亲掌握了现实主义美学的基本法则,硬生生从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乡间妇女,成了不为人世所知的我一个人的美学启蒙导师”。写母亲临终前的日子,病床前时间的流速突然变得凝滞而缓慢,漫长的治疗融进输液管里不停滴落的药物里,难以计数已经过去了多少天;但终究还是相聚太短、太匆匆,“我母亲挨到了秋天,在谷物充盈的日子重返泥土的怀抱”,那个意味着安全、庇护与温暖的单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在空旷的老河滩。
剃刀、机杼、柴薪、土陶,梧桐、高粱、牛羊、秋水……这是一场沿着乡村生活的寻踪,戏台上是乡村人家最为平凡的生活日常,目之所及,是乡村生活的圆点或轴心。《考工记》《王祯农书》《齐民要术》《事物纪原》……他从古代农书一路走来,走进童年的生活记忆里,让柳林锻铁的嵇康,凛然站在了今天仍然是风箱鼓动、打铁声声的北方原野,锻打出青峰。他把古时的“号钟”“焦尾”“绿绮”“绕梁”四大名琴,它们的风雅和精魂,带给故乡朴素日月之下的梧桐,让它们想起那些深雅的际遇,轮回间,布衣秀士,一树清音。
“北方有所寄”,这是一个乡村之子飘荡在乡村上空拳拳眷眷的心情。他的神思仍游离在“安土重迁”这个语境的迷雾深处,想要拨开的仍然是这方土地上的物与人的面纱,以使自己走进乡野的更深处、文学的纵深处。
(编辑/崔秀娜 设计/蔺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