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学习史及其经验启示
作者: 裴恒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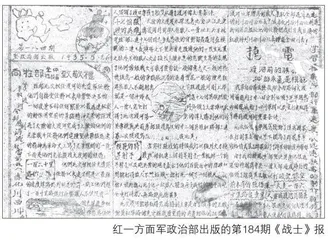
学习兴党,学习强军,学习强国。在百年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不断前进,创造伟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重视学习,加强学习,可以说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学习的历史。工农红军作为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非常重视学习,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学习。本文主要从梳理长征日记、报刊、回忆录等资料入手,结合相关文献,对红军长征中的学习史进行分析,以期弥补这一时期学习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进而探寻和理解党领导工农红军在艰难环境中克敌制胜的精神密码。
长征中的特殊学习环境
长征时期是党和红军所经历过的一段极端艰难的岁月,行军和打仗是其主要内容,常常夜行军、急行军,学习时间紧、不固定,同时指战员还不时面临生病负伤的情况。这些都给开展学习造成不利因素。但在行军短暂的宿营休息中,各级红军指战员仍然利用多种方式学习:识字,学习理论知识或国内外形势。正如陈伯钧在1934年10月25日日记中写道:“连日行军疲劳,甚又复多病,所以好几天的日记都未曾记载,一直到二十六日晚间稍微清醒,于出发时间较晚之机会,特将几日来行军里程简略记之。”赖传珠日记中也有不少反映长征中艰难条件的文字,1935年4月23日,他在滇东黄泥河抗击追敌作战中胸部中弹,身负重伤,仍在4月26日写下“因伤太重,到达地点没记”的日记。纸张、书籍等学习材料缺乏也是长征中艰苦学习环境的体现。如《长征日记》的作者萧锋所用材料是当时的土草纸和五颜六色的包装纸。红军长征到延安后,他才又花了3个月,凭着惊人记忆将污迹斑斑、字迹模糊的原始记录重新誊抄、修改了一遍。紧张的战斗,贫乏的物质条件,红军指战员们仍利用和创造一切条件学习。如陈云回忆红军到遵义后,几乎把街上可供书写的书籍、铅笔、笔记本等买空了,“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①,因为在长征中红军所经大部分地区是穷乡僻壤,荒山野谷,很难买到学习用品,红军很珍惜这宝贵的采购机会。随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的西方传教士薄复礼,对红军部队利用行军休息时间学习的场景多有描述,红军“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每个排还经常召开会议,会前先选一个议题,要大家作准备,开会时,大家踊跃发言,特别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励下,讲自己受地主剥削的亲身经历。每次发言之后,排长作总结,重申主要观点”②。红军还重视建设列宁室,“每到一地,不管停留时间长短,‘列宁室’是必建的。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③
在艰苦的长征环境中,党和红军尊重知识,优待人才,努力营造有利于学习的良好氛围。党的领导干部带头学习,为普通干部战士作了表率。毛泽东长征中带着一个书挑子,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他还利用行军休息时间如饥似渴地搜集阅读书籍报纸,写下《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等长征诗词名作。董必武、徐特立也是嗜书如命。行军休息时,董必武往往会拿出一本厚厚的俄文马列原著,高声朗读,研读马列真理。红军在遵义时,徐特立拜访书香之家,保护文物古籍。当时受徐老委托,集中保存遵义古籍图书工作的赵乃康先生曾写诗赞徐特立:“军中忙无暇,积极学文化,维护文物功,当不在禹下。”④红四方面军战士回忆长征中,廖承志给大家讲“列宁主义概论”“苏维埃政权建设”,张琴秋讲“国际妇女运动”“三八节的来历”,何长工讲“法国妇女运动”等。红军中还拥有一批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如用画作记录长征的黄镇,毕业于上海高等美术学校;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傅连暲、钱信忠;文学家成仿吾早年留学日本,是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创立者,长征中常给战士们讲自己的留学故事;长征中给大家跳苏联海军舞的李伯钊,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被称为“赤色舞蹈明星”……这些人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创造了条件,树立了榜样。
长征中的学习方式与内容
长征中的学习活动体现了因材施教,灵活多样。没有统一形式,红军指战员根据各自的知识水平,采取多种务实有效的方式开展学习,提高了理论修养。
识字扫盲。这是广大普通战士行之有效的一种学习方式。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指出,红军长征在川西一带征集粮食之余坚持识字,“每晚停止了劳作以后,还要上政治课、识字课和开各种会议,如党的支部会、小组会等”。识字还与行军战斗的生活实际相结合,优先学习一些常用的名词事物,如“打圈子”“渡河”“站好岗”等。萧锋在1934年11月12日日记中记录了周恩来对连队识字的鼓舞,“他指着岗哨上的战士背上背着写有‘站好岗’几个字的识字牌称赞说,既打仗行军,又识字,战斗不忘学习,这个办法好。我们工农现在打仗要文化,将来建设新中国更需要文化”。萧锋还在1935年3月12日日记中描绘了连队行军中,通过“识字牌”学习的情况,“我们行军识字做得好,七连班长刘新文一天行军识字十二个,就是那个打圈子的‘圈’字难写,我看先易后难总可学会。二排长说,明天把识字牌换成‘渡河’吧,每天都要渡河,把这个字先学会”。行军途中“看后背”也是一种有效的识字方式,即每人背后背一块写字板,供后面的战士学习。刘坚回忆红四方面军“行军虽然艰苦,妇女们学习文化的劲头却很大。有时认了几个字怕忘记,行军时就在前面走的同志的背上挂一小块布,上面写着刚学会的字,一路走一路记;到休息时,就拣个树枝在地下默写。不少人用这种方式认了不少字”⑤。此外,红军还通过课本学习识字。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锦屏者蒙村,留下许多书籍,其中一本《红军识字课本》,是红军总政治部于1934年3月编印的,分49课。课文言简意赅,如第一课“红军好,红军好”,第二课“红军要认字,要出操”等,是红军战士学习文化的启蒙读物。
书写长征日记。坚持写日记,把所见所思形成文字,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提高的过程。童小鹏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政治保卫局秘书,年仅20岁。从1932年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他坚持写《军中日记》,长征日记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日记中,他对学习的不足和意义进行总结反思,指出:“不及时的记载,不详细的描写,这是我去年记日记的大病,这非要求我能在今年的记载中来切实纠正”,他还记下自己革命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将同志们对于我的批评指示,与自己发觉的不应该这样做的事,郑重地写出,以作工作中的明鉴”。赵镕长征时任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作为战略骑兵的红九军团长征中任务重,责任大,他在日记中记录行军历程,总结所负责的供应工作,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惊人的学习毅力。特别是作为后勤工作负责人,他对长征沿途各地社会经济状况及红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多有记载和思考,如1935年1月18日日记反映红军在湄潭做冬装,组织得力,群众支持,成效明显,“组织了地方70多名缝衣工人及数百名妇女,采取歇人不歇机器、一天24小时三班倒的办法,终于在12个日日夜夜赶制出棉衣8000多件,夹裤8000多条,被子、绑腿、干粮袋、子弹袋等也均已做齐”。
阅读文件报纸杂志书籍。阅读文件方面,主要是学习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该决议是红军转战扎西期间由张闻天起草的,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文献。陈伯钧在1935年2月20日日记中写道,“晚看完《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草案》一书”。阅读报纸方面,主要是《红星》报、《战士报》等。《红星》报作为中革军委的机关报,在长征中坚持出版28期,邓小平、陆定一先后担任主编,以社论、消息、短评等形式,发表红军战斗消息、行军作战中注意的实际问题、群众工作的开展及成效等,及时传达党的声音,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内部团结,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学习提高的良师益友。正如《红星》报在创刊号中所宣示的:“《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的无线电台’‘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战士报》是红一军团的机关报,也是长征中战士们学习的重要资料,赵镕在1935年1月9日日记中反映当天红一军团送给红九军团,“5日出版的《战士报》若干份,全版都是关于红一师渡乌江的经过,连篇报道了渡江英雄的事迹”。长征日记中还有不少反映红军到各地搜罗报纸获取国内外消息动态的情况,林伟在1934年12月11日日记中反映军团司政直属机关驻扎在湖南通道县,“搞了许多《申报》和杂志,看到深夜才休息。报上登载有十一月九日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在国民饭店枪杀并逮捕我党党员吉鸿昌;十三日上海《申报》总编辑史量才在沪为国特暗杀等消息”。阅读相关书籍方面,陈伯钧长征日记记载了其在遵义期间阅读《淞沪抗战画史》《初恋》《石达开日记》的情况,1935年1月10日,“晚看淞沪抗日画史之一小部。查该画史系国民党借此来宣传它是反日反帝的,以更进一步在此烟幕弹下,来彻底地做卖国勾当,孝敬各帝国主义”。红二方面军的杨秀山也回忆了行军战斗间隙阅读书籍的情况,“《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这本书,是当年刘伯承同志在苏联学习回国时,带到上海翻译后印发给红军指挥员学习的。而我得到这本书,是我在部队整编前任红四师副政委时,师参谋长金承忠同志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留下的。《列宁主义概论》这本书,则是师政委方理铭同志送给我的。这两本书是我最宝贵的财产,它给了我不少智慧和力量,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政治谈话、政治集会学习。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长征情况时指出,在行军期间,红军时刻重视对士兵的政治和教育工作,“每天早上,或每天晚上,必举行政治谈话。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来教育红军兵士,教他们如何进攻、防守、防御以及使用各种武器等”。党和红军的负责人在重要会议之后往往到部队谈话,传达会议精神。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后来回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来到红三军团,在滥板凳(地处遵义南郊)给营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着重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红军各部队迅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极大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精神,丢掉了悲观情绪,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⑥。伍云甫在1935年2月10日日记中记载了部队进驻云南扎西期间学习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情况,“上午九时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洛甫报告五次‘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要点主要是强调“五次‘围剿’尚未粉碎”“我们的错误是单纯的防御路线”“我们有方法粉碎堡垒主义”。萧锋还多次在日记中提到红军首长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给部队讲形势的情景,1934年11月11日,“晚饭后,我们在祠堂里点了几盏猪油灯,挂上地图,我和团政委林龙发、参谋长彭明治等同志坐在首长周围,请周副主席和刘总长讲形势、全军野战行动及部队必须注意的事项”。他日记中还提及,11月13日午后,“谭政主任在我团召开政工会议,总结几天来的白石渡宣传赤化和扩红经验”。12月16日,在新柳“召开政工会,分析了全州战斗失利情况,总结了半个月来行军打仗的经验教训”。
流动的红军大学。中央红军的红军大学在长征开始后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如在干部团的宋时轮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休整间隙,“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如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等军事科目训练”⑦。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根据中央沙窝会议《关于“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的培养军事与政治的干部”的决定》,于1935年8月上旬在毛儿盖建立新的红军大学。下设指挥、步兵、工兵、炮兵、骑兵等专业科。主要开设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和军队政治工作等政治课程。这些课程对于提高广大红军干部的理论水平起到重要作用。红军大学是对有一定知识储备或实践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进行培训提高的重要方式。如红四方面军为适应北上需要,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水平,尽可能将干部抽调出来,送到设在炉霍的红军大学和党校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知识。除红军大学外,长征中还开设各种临时训练班培训从事专门工作的红军干部。中央红军转战黔北期间,为更好地在川滇黔边创造新苏区,总政治部抽调部分干部,在行军途中开办“游击队干部训练班”,由左觉农带领参训学员白天行军打仗,夜间由吴亮平、李伯钊等分别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和游击战争等课程。红四方面军北上期间,对不能入红军大学学习的干部,则用《干部必读》作教材,举办流动训练班,或组织讨论会、演讲会进行政治教育。对广大战士则主要通过《战士读本》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
军事技术和纪律学习。提高军事技术,应对长征沿线复杂的军事斗争环境,是红军指战员的首要任务。张宗逊在回忆中对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军事学习有具体描述:“‘走’是长征的一门主课,一是给学员们讲爬雪山过草地等不同地理环境的行军、宿营、警戒等各方面的知识;二是讲红军北上可能经过的地区情况,如地形特点、气候变化规律、沿途民情和物产分布,以及敌人的部署情况等等。‘打’就是可能遇到的不同战斗,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对付敌人。要求学会打骑兵、打平地战、打山地战、打河川战、打隘路战、打麻雀战。这些学习内容,既实用又生动具体。”⑧红军长征到藏区后,遭到国民党及反动藏骑的进攻,损失严重,各部队开展了学习打骑兵活动。为此,陆定一、黄镇在川西毛儿盖编写《打骑兵歌》,大意是:“敌人的骑兵不须怕,沉着敏捷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易射杀。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坍它!我们消灭它!我们是无敌的红军,打坍了蒋贼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寓教于乐,使战士们学习掌握了打退敌人骑兵的要领。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军阀主义倾向,红军狠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强调官兵平等和军民团结,反对打人、骂人。红军机关报《红星》报不时发布关于军事纪律、群众纪律的文章,供红军战士进行学习。如1934年11月11日第四期《红星》刊发《反对浪费宣传品的现象》;第六期刊发《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消灭坏纪律的现象》。1935年2月10日,第九期刊发《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2月19日,第十期刊发《找火把、禾草不要侵犯群众》。这些关于强化红军群众纪律的文章,摆事实,讲道理,短小精悍,对红军战士起到很好的警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