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魂王勃及其精神光谱
作者: 李劼上篇
说起华夏文化,世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史著或者哲学,而是诗歌。这是可以理解的。由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所构成的审美空间,既是赏心悦目的,也是让华人最引以为豪的。只是有关这个审美空间的解读,却有着教科书式的整齐划一。比如,最伟大的诗人是屈原,因为其《离骚》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按照儒家的标准,杜甫是当之无愧的诗圣,那种因“生逢尧舜君”而来的“葵藿倾太阳”的向日葵姿态,无人企及;李白因为被贴上了浪漫主义的标签,故而也能得到追捧。似乎诗歌本身写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成为一种典范,或者一种榜样。当这几位被抬上近乎诗歌皇帝的宝座之后,其他众多诗人便有如座下的臣民,众星拱月。座次是明确的,景象是庄严的。所有的论著,所有的论说,各式各样的课堂里,都必须按照这样的座次来讲说诗人、诗作,否则,就会被视作无知。然而,除了上述的爱国主义、向日葵姿态或者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类的评判标准,还有没有其他的审美趣味呢?
假若能将诗歌看作是审美,而不是什么观念或什么主义的体现,那么显然,美学是第一位的。假如能够确定诗歌评判是审美,那么美是什么?美是自由的呼吸——别尔嘉耶夫如是说。这是我所知道的有关美的最准确最生动的定义。一旦世人将美是自由的呼吸引入诗歌审美,我认为最精彩的诗人不是上述三位,而是《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
王勃当然不是诗圣,也不是因为爱国主义而显得伟大的诗人,更无法被所谓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所框架。王勃的《滕王阁序》乃是最自由的呼吸,从而也成为了整个辞赋诗词的审美空间的灵魂所在。作为审美的诗歌,无论是辞、赋、诗、词,以其是否呈现自由的呼吸,得以确认是否属于灵魂的吟唱。
自由,是王勃及其《滕王阁序》的关键词。有关此作的成文过程,《新唐书》有记载如是说:
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泛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
这段记载所描述的王勃大大咧咧,历历在目地彰显了王勃自由自在的个性。这与其说是王勃不通人情,不如说是王勃根本不把世故放在眼里,既然主人相邀就欣欣然提笔了,全然不顾人家只是走个过场。尽管王勃也会不无敷衍地客套两句诸如“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但马上便是一句不无淘气的无心快语“童子何知,躬逢胜饯”,这无疑会让那位都督大人读了哭笑不得。好在阎都督毕竟不是朱元璋王朝时代的粗人,既懂诗又识得天才。
有唐一朝,同样如此大大咧咧的诗人,恐怕也就是李白了。只不过,比起王勃,李白少了一份雅致,多了一点俗气。在《新唐书》里有记载如是说:“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后来,“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这《新唐书》是宋朝人写的,其中有诗人同行如欧阳修者。不知这记载是否属实,或许有些下意识的文人相轻?这段故事源自《旧唐书》,估计李白当年在朝廷里的人缘极差。及至宋人编撰《新唐书》时,又被津津乐道了一番。当然,不管怎么说,李白当年荣获唐玄宗诏见时写下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也确实失态:“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没有杜甫“窃比稷与契”的为臣理想,却颇有在其《侠客行》一诗里表达的“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向往。倘若唐玄宗了解李白有这种志向就应该给对方些许机会,比如让他去行刺一下安禄山之流,或许也就遂了李白的心愿。有道是,金麟岂是池中物;很不幸的是,李白恰好有点想做池中物。李白这样的小心思,唐玄宗没能弄明白。须知,作为诗人的李白,在朝中不会被当回事;一旦成为皇帝的剑客,那才令人刮目相看。但不管怎么说,李白对成为池中物的向往,无疑让其自由的个性打了些折扣。
相比之下,王勃不是池中物,也不想成为池中物。王勃具有李白所不具备的身心自由。失意时不会像李白的《将进酒》所写的那般买醉,身在庙堂也不在意如何为朝廷效力。王勃曾经入王府做沛王的侍读,但并不把王子们当回事,想开玩笑就开玩笑。瞧着王爷们斗鸡取乐,戏作《檄英王鸡》文。结果此文被人上达朝庭,《旧唐书》记载:“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于是乎,王勃旋即被赶出京城。彼时心境,其诗作《郊兴》有言:“空园歌独酌,春日赋闲居。”潇洒得很。又道是:“雨去花光湿,风归叶影疏。”空灵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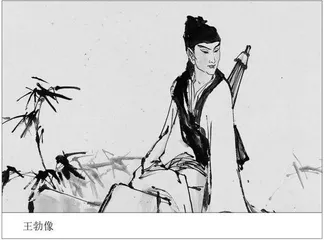
不知是不是因为皇上发了话,故而底下的臣子马上响应附和。自从李世民开了皇帝审阅史官史著的先例,此后的官方著史庶几如同奏折,史官们大多成为讨好皇帝的人。唐朝史官写的《旧唐书》中关于王勃的文字短得不能再短,却不忘给王勃贴上“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的标签。该传引用当时的吏部侍郎裴行俭的评语:“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这番话的意思显然是将王勃列入有文才而无器识之流,仕途黯淡,不如杨炯有望做个县令什么的。那句“勃等……”之人,无疑是王骆卢杨四子之中的骆宾王和卢照邻二位。该传引用裴行俭评语之后又加了“果如其言”四个字,以示这位吏部侍郎很有眼光。确实,骆宾王后来与反武则天的徐敬业走到了一起,兵败后不知所终。卢照邻也一生坎坷,郁郁不得志,最后投水而逝。卢照邻在其《长安古意》中的那一联“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可以看作是其人生写照。此二子虽然不像裴侍郎那样能够成为朝廷命官,但“浮躁浅露”却是无从说起的。他们或者有担当如骆子者,或者有风骨如卢子者。相反,为裴氏所赏识的杨炯,虽然最后做了盈川县令从而人称杨盈川,但其人品却了无裴氏所说的“沉静”资质。
杨炯编过王勃的文集并为之作序,但当宋之问将四子排名为“王杨卢骆”后,据《旧唐书》记载,杨炯表示:“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前面一句有发嗲嫌疑,因为卢照邻一生低调,足以让杨炯得了便宜还卖乖;后一句显然是了无自知之明,无论就人品还是作品而言,王勃与杨炯相较都有天壤之别。杨炯的名作《从军行》里看似豪迈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骨子里透出的,与其说是奔赴疆场的气慨,不如说是羡慕那些以军功升官的捷径人物。顺便说一句,那位裴侍郎也曾去边境立过军功,故而彼此之间会有如此相通。相比于王勃在王府里随便开王爷玩笑,杨炯看到武则天坐稳龙椅之后,赶紧献上《盂兰盆赋》以表忠心,谀辞汹涌。如此鲜明的对照,王、杨二子的人品,高下立判。更不用说,王勃处世一身正气,杨炯为官以酷吏出名,连《旧唐书》也不得不承认:“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该史书还说:“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可见,裴侍郎那句贬低王勃的“浮躁浅露”用在杨炯身上,倒是恰如其分。可叹的是,撰写《旧唐书》的朝廷巴结者在杨炯的那番表示后面,竟然罔顾事实,作出了“当时议者,亦以为然”的结论。可见,那位裴侍郎的高论显然是不能随便推翻的,因为背后有唐高宗李治之于王勃的震怒。
不过,王勃倒是专门写过一函《上吏部裴侍郎启》。当然,在《旧唐书》里,无论是关于王勃的部分,还是关于裴行俭的部分,全都只字不提;致使后世弄不清王勃此信是在听到裴行俭的那番评说之后写的,还是之前写的。从信中的内容来看,似乎是之后。因为该信如此开头:“猥承衡镜,骤照阶墀。本惭刀笔之工,虚荷雕虫之眷。殊恩屡及,严命频加。”大意是:“承蒙阁下对卑微的我作出衡量品评,犹如阳光突然照亮门前的台阶。我一向惭愧自己只有舞文弄墨的本事,枉担了些许雕虫小技的虚名。如今阁下屡屡施恩于不成器的我,好比严父般一再耳提面命。”言辞谦卑,却是绵里藏针。相信裴侍郎读了不会爽快。更何况,此信直言不讳地向裴侍郎坦陈自己对选拔官员的看法:“伏见诠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炫才饰智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栖遑于下列。”大意是:“我闻见阁下在选拔官员的时候,总喜欢将其诗赋上的才华作为首要条件,真心担忧阁下仅仅限于笔墨之间挑选国家栋梁,在书简当中寻求廊庙之材。最终难以获得杰出才俊,或者选取到高人贤达之人。结果会使英杰被长久地埋没掉,有真才实学者不再出现。夸夸其谈的平庸之辈将会招摇过市,有抱负有本事的才俊之士只能在底层挣扎。”
王勃的致信无疑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显然是专门与那位吏部侍郎探讨如何选拔人才之语。言辞间从容不迫又句句紧逼,锋芒直指裴侍郎的那番评判。相信裴行俭应该是收到了这封信的,但在《旧唐书》里看不到他做了什么回应。王勃此信表面上是对裴行俭的回应,骨子里却暗含着对皇帝震怒的不以为然。这无论是裴行俭,还是《旧唐书》的作者,全都心知肚明,但又全都装作看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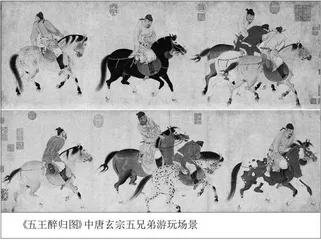
当然,比裴行俭更不堪的是唐高宗李治。李治并非看不出王勃的那篇《檄英王鸡》是玩笑之作,没有任何政治意图,但李治皇帝的小心肝却被这个玩笑无意间戳痛了。因为李唐王室有个痛脚,当初李世民是经由兄弟相残上位的。李治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其长兄被废了太子之位后,按说该李治的二哥顶上。但李世民担心这老二上位之后会不会对弟弟们不利。作为九子的李治看出了父皇的心思,故而在父皇面前极力表演成一个忠厚仁义之人,绝对不会做出兄弟残杀之类的事情,最终赢得了父皇的信任,成功接班。李治没有重演玄武门血案,更害怕看到他的儿子之间重演这类故事。这应该是李治震怒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李治从王勃的玩笑文章里,感觉到了王勃的漠然于向李唐王朝顶礼膜拜的“恃才傲物”。“恃才”的王勃不小心傲了李唐王朝这个“物”。《旧唐书》里的这四个字,对王勃触犯朝廷一事把握得精准,字字句句都戳在要害上。
不过,这无意间倒也彰显了李治的格局:上位时精明,在位时平常,比起连他自己都佩服的武则天娘娘,其才干、能力、心胸、格局,都差了一截。武则天也碰到过相类似的难题——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武则天读着非但没有震怒,还对着文中的“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哈哈大笑;及至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不仅不怒而且心生钦佩,询问左右,作者是谁;随即责怪宰相没有将如此人才招揽入朝,致使人家流落在外,怀才不遇。武则天不仅重才,而且识才。须知杨炯在《盂兰盆赋》里曾是那么的阿谀奉承,但她就是不为所动。骆宾王一篇骂她的檄文,却看得她心花怒放。不知那么在乎排名先后的杨炯,对此作何感想。
或许是为了替李治开脱洗地,曾经有人编造过李治读到王勃《滕王阁序》后如何的后悔,得知王勃溺亡之后又如何三叹可惜。这当然是不能当真的。就算李治真的读到过《滕王阁序》,也未必读得懂其中的意蕴。假如李治当初读《檄英王鸡》能够像武则天那样哈哈大笑的话,那么他读《滕王阁序》可能会读出共鸣。李治没有武则天那样幽默,更不懂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呈现出来的审美意境。
《滕王阁序》首先令人瞩目的是其惊人的文字才华,或者说在遣词造句上的鬼斧神工。即便是贬损他的《旧唐书》也承认,“勃文章迈捷,下笔则成”。这篇《滕王阁序》一气呵成。须知,当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尚有涂改之处,王勃挥笔却不加思索,不打草稿,便可妙语连珠,精彩纷呈。相形之下,后来贾岛那样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着实苦涩得让人忍俊不禁。王勃这种在文辞上的自由酣畅,颇类莫扎特作曲时的随心所欲。莫扎特可以将他人所作的平常旋律,随手改成一首美妙动听的乐曲。王勃也一样。庾信的《三月三华林园马射赋》中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王勃信手拈来地改作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