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未终,人不散
作者: 吴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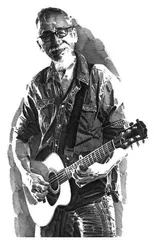
2025年6月14日,中国台湾音乐人陈彼得在成都逝世,享年82岁。
回看陈彼得的人生,他出生于四川成都,成长于台湾眷村,两岸恢复通信后,他辗转回到大陆,将音乐化为两岸“联手合弹”的乐章,先后在广州、北京歇脚,最后在成都落叶归根。在音乐世界里,陈彼得所经之处,都会生长出一个个小枝丫,一路生花,带来种种具备革新性的音乐风格。
音乐的生命力,是由人创造而后发扬的,而音乐也成为人永存的载体,代替陈彼得长存于人世间。
先锋
正如他那新颖的中西合璧的名字,陈彼得最初闯入大众视线时,就以音乐先锋的姿态,向彼时台湾地区的乐坛注入了一股带着融合风格的创新之风。
20世纪70年代,“二战”留给世界的伤痕逐渐愈合,经济文化的繁荣投射在流行音乐上,这是由“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披头士乐队以摇滚、迪斯科等风格缔造的欧美流行乐的黄金时代。在台湾地区,以中岛美雪的音乐为代表的东洋小调引领着音乐审美。
彼时,台湾岛内掀起了民歌运动,以罗大佑、蔡琴、齐豫、叶佳修等为代表的歌手,创作或演唱了《童年》《恰似你的温柔》《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等民谣作品。这些歌曲传唱不衰,成为经典。
在这一背景下,以歌手身份出道的陈彼得凭借专辑《玫瑰安娜》崭露头角。因为在年少时深受披头士乐队的影响,对于欧美音乐,陈彼得并非秉持顽强抵抗的姿态,而是另辟蹊径,在接收这股来自大洋彼岸的新潮风气的同时,摒弃台湾民谣里基调太过绵软的部分,吸收民歌的叙事性,开创性地将欧美新潮元素融入台湾本土音乐的创作中。因此,陈彼得创作了不少风格多元的作品。
《阿里巴巴》是陈彼得早年的代表作。这是一首迪斯科风格的舞曲,取材于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朗朗上口的歌词,配合俏皮的小调,一经发布就传遍了台湾的大街小巷,成为当时的“顶流神曲”,一改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甜美系歌手的演唱风格。
这首充满动感活力的舞曲,不仅开创了流行乐新的风格,还体现了当时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繁荣向上的步调。
在民歌运动的推动下,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迎来辉煌发展的时期,唱片公司和造星业欣欣向荣,歌手也走上了职业化竞争的道路。凤飞飞与邓丽君,刘文正与高凌风,陈彼得与罗大佑,歌手之间的竞争使得杰出的音乐人不断涌现。作为音乐人,陈彼得有过一个月做4张唱片、写40首歌的经历。而在此期间,他制作的歌曲包揽了音乐排行榜的前三名,他也成为唱片界成功的操盘手。
他为刘文正创作了《迟到》,使刘文正的演艺生涯踏上新的台阶。于是,台湾乐坛一度盛传陈彼得“以一曲捧红一人”的神话,他也因此与罗大佑齐名,被称为“台湾流行乐教父”。
回归
陈彼得在音乐艺术上兼容并包的气度,离不开他多元的成长背景。
1943年,陈彼得在四川成都出生。5岁时,他跟随父母移居台湾,与胞弟以及外婆遥隔山海。
天府盆地的乡土情结、台湾眷村的成长经历,还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化的开放气息,赋予陈彼得活跃、开阔、包容的音乐品位。
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事业高峰后,陈彼得并未停下追逐音乐创新的步伐,只不过,这一次,他从台湾迁移到了幅员辽阔的祖国大陆。
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政策后,陈彼得绕道日本飞回大陆。当他在上海上空俯瞰故土时,泪水如雨般落下。这种深刻的情感体验,直接转化为他在音乐创作中的动力与灵感。在1988年推出的专辑《归雁》中,陈彼得深情地唱道:“我是一只孤雁……终于找到了自己出发的地方。”歌词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近40年离散生活的心声。
凭着对祖国和故里的一腔热血,他将音乐当作桥梁,成为文艺界最早开拓两岸交流渠道的人之一。
陈彼得是最早回到大陆开演唱会的台湾音乐人之一,他在成都、重庆、武汉等地举办了20场“探亲演唱会”,受到当地民众的追捧。他认为这种热情,来自同胞之间的爱以及音乐魅力的感染。他对祖国的热爱,并不只是停留在音乐创作上。陈彼得还一手“搭台”,让年轻人“唱戏”。他在北京三元桥开设了名为“喜鹊棚”的录音棚,提供场地、设备,亲自下厨做饭,自掏腰包支持年轻人做音乐。何勇、窦唯、崔健、谢天笑等中国摇滚乐的代表性人物,当年皆受惠于“喜鹊棚”的培育。
回归故里成为陈彼得人生和音乐事业的转折点,他开启了为古诗词作曲的创作生涯。
还在台湾时,尽管陈彼得投身于西方音乐与本土民谣融合的探索中,但他并未因此割断具有东方韵律的创作脉络,而是尝试创作符合当代审美的中式音律。
1983年,他为电视剧《一剪梅》的同名主题歌谱曲,歌曲将费玉清温润的嗓音融入中式古典咏叹调的婉约风格之中。陈彼得借鉴四川民歌羽调式的小调旋律,融合竹笛和二胡的悠扬以及西洋弦乐的婉转,赋予歌曲典雅明亮的底色。
《一剪梅》的经典旋律,是陈彼得早期对“以曲谱诗”这种音乐形式的探索,可以视为陈彼得音乐生涯里古典基因的觉醒。这样的音乐作品,为后来周杰伦、林俊杰等新生代音乐人创作以《青花瓷》《江南》等为代表的“中国风”歌曲,提供了重要范式。
陈彼得的音乐,既有古典的雅致,又不失现代的韵味,连接着古今,也连接着两岸。到大陆后,他的创作重心落到了为中华古诗词谱曲上。这并非易事,因为他不仅要以现代音符嵌合古诗和词牌的韵律,还要传达出千百年前诗词作者的心境和时代背景。为此,陈彼得研读了不少唐宋文人留下的诗词。
在一众唐宋大家之中,陈彼得对苏轼情有独钟。他曾两次拜访位于眉山的三苏祠,在现场屡屡落泪。“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千古名句,暗合了陈彼得从大陆到台湾,再从台湾回到大陆的流离而又丰厚的一生。
文学和乡土情怀,是陈彼得音乐创作的灵魂。他曾说:“古今诗人皆入蜀,四川是天下文人的会客厅,苏轼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他应该是东道主。”在晚年,他也以“东道主”的身份与心境,回归故里,定居成都。他对乡土的深情,化作音符,流淌在每一首为古诗词谱写的曲子中。
不死
陈彼得到了晚年,依然坚守在创作和舞台的一线,不改当年的先锋做派。
在众多的文学作品改编中,陈彼得近年对辛弃疾诗词的重新演绎,更贴近现代审美意趣。
在2018年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陈彼得在演绎《青玉案·元夕》时表示:“辛弃疾所展现的英雄气概,正是当今流行乐歌词所缺乏的力量。”这种跨越时空的创作理念,使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而在《丑奴儿》中,他大胆引入摇滚乐和电子音乐,将其融入这位800多年前豪放派词人的名作之中,电吉他和架子鼓加强了音乐的韵律和节奏感,使之更铿锵有力。
陈彼得最后一次公开演出,是在2024年12月31日的B站(哔哩哔哩视频网站)跨年晚会上。他以一曲《黑神话:悟空》中的《不由己》,留下了自己在舞台上的绝唱。
《不由己》是《黑神话:悟空》火焰山篇的片尾曲。彼时已81岁的陈彼得,声线似乎因承载了太多岁月的尘埃而变得有些颤抖,但这种不完美反而使得这首谱写牛魔王因不服天庭权威而遭受贬谪的歌曲流露出更多沧桑感。人生在世,七情六欲,不过是过眼云烟,轻我、贱我、恶我、骗我,皆是红尘间的是非恩怨,油枯灯灭之际,也是烟消云散之时。
去世的两个月前,2025年4月12日,陈彼得还预告了他的新歌——《客至》。这是一首以杜甫的《客至》为词,配上了带着民谣风格旋律的歌曲。与早几年豪迈的嗓音相比,此时陈彼得的声线已有衰弱之迹。
离世之前,陈彼得还计划于今年8月他的生日时发布唱片。然而,因为基础疾病等问题,陈彼得还没来得及录完唱片就溘然长逝,留下了尚未画上句号的乐章。
回看陈彼得的一生,可以说他身上浓缩了半部流行音乐史,他的一生是一首写满乡愁与热爱的长诗。作为来自台湾地区的“乡愁一代”,他和费翔、罗大佑、邓丽君等人,用音符跨越“一湾浅浅的海峡”,从《归雁》的孤寂到《我和我的祖国》的泣诉,他的演唱中始终流淌着“吾爱吾国”的赤诚。
直到离世,陈彼得置顶的微博,还停留在2019年春节期间,他在成都宽窄巷子参与的《我和我的祖国》的“快闪”活动。他将这次歌唱祖国和故乡的机会,视作一生最大的荣耀。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时,回忆起在故乡歌唱的场景,鬓须花白的老人一时情动,掩面哭泣。他的人生,必然也会定格在这一动容时刻。
晚年的陈彼得说:“音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而他一生都在破译这串密码,音乐不死,文化不息。
曲未终,人不散。这不是告别,而是另一种永恒的开始。
(怀 沙摘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本刊节选,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