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浅析孔子美学思想
作者: 李佳琪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美学思想。自汉代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美学思想逐渐确立为中国传统美学体系的主导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艺术理论与审美实践的基本走向。历代文艺理论建构者与美学思想家均通过系统化阐释与创造性转化,将孔子艺术精神内化为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理论范式,在双向互动的传承机制下既保持核心命题的承续,又在诗教传统与礼乐文明的融合中发展出新的价值取向。孔子美学作为伦理型审美范式的典型代表,通过历史进程中的持续性阐释,逐步完成了对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深层建构。其首先在审美认知层面塑造了“中和为美”的思维方式,在审美实践领域培育出“比德观物”的鉴赏传统,在审美价值维度则确立了“尽善尽美”的评判标准。儒家美学思想以孔子美学作为内涵和基础塑造中华民族注重伦理意涵的审美趣味,更催生出具有东方特质的审美范畴体系,最终使儒家美学成为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最具统摄性的阐释框架。
一、孔子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
先秦时期的思想流派普遍受到原始思维模式的制约,在哲学观念上大都遵循“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学派在承继这一思维传统时,不仅延续了原始认知中的整体性特征,更将追求万事万物的适度与平衡作为核心原则,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
(一)轴心时代的伦理美学建构
作为中国轴心时代的核心思想群体,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建构深受早期宗法社会的思维范式制约,其整体认知框架根植于三代以来形成的天人同构观念。在周代礼乐文明解构与重构的背景下,儒家学派率先对“天人合一”这一命题展开系统性阐释与理论升华,通过《易传》《中庸》等典籍的哲学演绎,将其转化为具有伦理美学特质的理论范式。先秦诸子学说在多元发展的表象之下,“大都遵循‘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学派对‘天人合一’的探索沿袭,是认同了原始思维的模式”(张超《孔子美学思想初探》),不仅成为各派理论建构的深层逻辑起点,更通过持续的学术争鸣推动原始宇宙观向哲学体系转化,最终完成了对天人关系的系统性理论重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将这种哲学思辨引入审美领域,赋予“天人合一”命题以新的美学维度:在认识论层面,强调客观自然与主观精神的交互关系;在本体论层面,主张主客二元在审美活动中实现本质统一,而主张“天人合一”无疑是强调主客观、主客体的统一。孔子创建的“中和”美学体系,既继承了传统天人观的整体性思维,又通过辩证思维的引入,构建起把握审美限度的价值标准,通过主客体的有机融合,形成具有系统性与思辨性的审美认知框架。
(二)“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审美主客体的关系
孔子通过《论语·雍也》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经典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儒家伦理美学的建构逻辑。作为审美感受之“乐”是如何发生的,“乐”的活动中主客体关系如何?首先从孔子的原意中我们能够认识到作为审美主体的“知者”和“仁者”之所“乐”的并非自然景观的山、水,而是山、水之外的“知”和“仁”。这句话的意思是:“智慧的人,性情像水一样活泼,不停流动;内心仁义的人,像大山一样静谧,深厚祥和、稳重不移。”从审美发生学视角考察,主体获得的审美愉悦并非源于自然物象的表层特征,而是源自其承载的道德象征意义。作为审美客体对待的山水,对“知者”“仁者”来说才有审美意义,才能成为审美的对象。其次,作为自然物的山水能变成审美客体,关键在于它能反窥出审美主体的“知”“仁”的审美蕴义,能表现出审美的理想、情趣。孔子通过这种意象化表达,既实现了自然审美与道德教化的有机统一,更建立起“观物比德”的审美范式,使得山水意象成为沟通天人、融合主客的重要媒介。
孔子美学思想的核心特质在于强调通过艺术教化陶冶情操,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其美学思想的深层价值在于构建起完整的修养体系:通过自然意象的人格化诠释,既满足感官层面的审美需求,更指向精神境界的超越追求。在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体系中,孔子“中和”观通过对“天人同构”理念的创造性转化,进行相应的变通和融合,建构起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审美发生机制。这种以“和”为价值中枢的美学架构,既突破原始天人观的混沌性局限,又避免陷入机械二元论的认知困境,最终实现审美体验从感性直观向理性思辨的哲学跃进。孔子将“中和”理念作为统摄性原则,在保持天人关系统一的前提下,通过辩证思维消解审美活动中的二元对立,最终形成以和谐为核心的美学价值体系,实现了感性体验与理性认知的深度融合,展现出东方智慧特有的圆融特性。
二、孔子美学中的“比德观”体系建构
在中国哲学视域下,自然现象与人类内在精神的相互契合与异质同构现象被阐述为“天人合一”的理念,其核心在于自然属性与道德价值的异质同构。通过玉、山水这类自然物象来映射人格德行,建立“物德同构”的伦理美学,这种“观物取象”的认知模式,实质是对原始“比德”传统的理论升华。中国古人最初是以实用的、功利的观点看待自然美的,自然物进入人的精神领域首先是“比德”,即将自然物看作某一品德的象征,人们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来观照和阐释高尚的人格品质。“胡家祥先生曾经这样界定‘比德’的概念:‘将自然现象与人的精神品质联系起来,从自然景物的特征上体验到属于人的道德含义,将自然物拟人化。’”(洪茂宁《从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看“比德”说》)通过自然实体与人的道德品质之间的类比与象征,自然对象被赋予了道德意蕴与人格特质,抽象的伦理观念亦得以生动呈现,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审美愉悦与情感体验。
该理论的文本渊源可追溯至早期典籍记载。《礼记·玉藻》:“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其确立了“君子佩玉喻德”的象征传统。《荀子·法行》亦有详细记载孔子以玉之物理特性对应“仁、智、义”等德行维度,构建起系统的类比体系。值得注意的是,《管子·小问》虽提出以禾喻德的先例,但其影响力远不及儒家建立的玉德理论。从理论建构层面考察,孔子通过系统性阐释与创造性转化,使零散的类比传统升华为具有哲学深度的美学理论。
在中国艺术创作传统中,“比德”思维作为持续在场的审美范式,其符号生成机制呈现出跨时代的理论生命力。植物意象始终承担着德行符号载体的功能,这种将自然物象转化为伦理指涉系统的创作路径,本质上构成了中华艺术独特的隐喻结构。魏晋时期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被唐人张彦远于《历代名画记》中评价为“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魏晋之际的社会动荡,促使士大夫群体转向山水自然寻求精神慰藉,山水审美逐渐演变为文化精英的集体意识。这种审美群体意识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被各朝文人士大夫发展为一种“以静寄情”的审美潮流。南朝宋艺术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详尽论述了“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像”及“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理论,主张通过山水画鉴赏以领悟宇宙之道,同时赋予山水以“仁智之乐”的深刻内涵,标志着山水艺术哲学内涵的体系化。其主张通过解构山水形态把握宇宙规律,赋予山水以“仁智之乐”的深刻内涵,将视觉体验升华为“仁智交融”的认知活动。
三、知者和仁者的审美主体性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仁”作为核心伦理范畴,其内涵建构具有多层次特征。从人格修养维度考察,“知者”指具有理性认知能力与明辨是非智慧的理想人格,而“仁者”则指向具备道德自觉与利他情怀的德行典范。孔子思想中“仁与知”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是“仁”,在二者合说的情况下,“知”是包含于“仁”中的。例如,《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里仁》:“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在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仁”的德行结构呈现为庄重、宽厚、诚笃、敏睿、慈惠五重伦理特质的有机整合。这五种德目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忠恕之道”形成价值互渗的认知网络,使得其他道德范畴自然渗透于道德实践过程。仁者通过德行确证获得本体安定,知者则以认知自觉推动道德完善,二者构成“仁智双彰”的修养路径。但《论语》在具体辨析时往往采取差异化策略,例如《论语·宪问》有云:“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其将“不惑”“不忧”分属不同的德行维度,以此建构多向度的理想人格模型,展现儒家伦理思想的辩证特质。
在孔子美学思想体系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命题蕴含着德行主体与自然客体的交互阐释机制。知者因明理善辩的认知特质达致“不惑”之境,仁者则凭借敦厚包容的德行修为臻于“不忧”之态,二者共同构成君子人格的双向向度。该命题通过物质性存在的山水构成生命基质,将作为精神性存在的智仁表征为生命形态。这种将自然属性与道德品格进行异质同构的思维范式,本质上是对“比德”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孔子将“比兴”的传统观念融于他的审美实践中,通过“观物取象”捕捉自然的自由形式,又借助“托物言志”实现人格的对象化显现,紧密相扣山水的自然特征与人的高洁品德。这种双向建构过程不仅彰显自然的人格化升华,更实现了人性的自然化回归,形成天人互证的审美阐释循环。
四、山水意象的价值合一
自然景观的审美体验根植于人性本源。或临川观澜而得其趣,或登高览胜而畅其怀,各适其性,各美其美。朱熹于《四书章句集注》中解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时指出:“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仁者爱山,志在山的稳重博大来积蓄锤炼自己深沉宽厚的仁爱之心;知者乐水,通过望水内省让碧波清流濯洗自己的理智和机敏。此论深刻揭示了儒家自然审美的深层认知逻辑:仁者于山之厚重中涵养德行,知者借水之灵动启迪哲思。这种审美认知模式的核心在于建立自然物象与主体精神的镜像投射关系,人们从主观道德的角度通过“化景物为情思”方式领悟自然之美,即自然美是人的主观精神的映射,满足了主体的某种需要,它是善的,也是美的。
在此认知框架下,自然物象被赋予主体精神特质,其审美价值生成于物性特征与人性理想的异质同构。当山水形态暗含的道德隐喻与观者精神诉求产生共鸣时,自然景观便升华为承载价值判断的审美介质。这“以物比德”的审美机制,通过将主观情志投射于客观物象,实现伦理观念的可视化传递,既满足主体的精神需求,又完成自然审美的价值赋形。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命题实质揭示了审美主客体关系的价值同构机制。知者与仁者的精神取向看似相异,却在山水意象中实现了德行象征体系的辩证统一一水之灵动与山之敦厚构成互补性的自然隐喻,恰如智慧与仁德在君子人格中的共生关系。这种通过自然物象投射道德境界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对“天人合一”哲学范式的审美转化。从发生学视角考察,该命题建构起三重生态伦理维度:在人际层面倡导“仁智相济”的德行互补,在社会层面强调礼乐文明的协调共生,在自然层面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在此视域下,强调天、地、人系统的整体和谐,山水意象的价值同构不仅实现个体精神提升,更指向构建生态共同体的实践诉求。
孔子美学思想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石,其理论构建始终根植于儒家思想体系,而儒家美学体系的发展又深刻体现着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孔子思想的智慧在于其植根经验世界又具有形上超越性一—既从物质存在中汲取审美资源,又通过伦理提升赋予艺术以精神深度,这种“即物超越”的特质完美契合艺术创造的本质规律。在中国现代美学理论体系的当代建构中,“美”的本质认知需确立:源于物性但超乎形质本身的立场。艺术创造不仅要实现对具象形态的超越性突破,更需回归人本精神的价值锚点,这种辩证关系要求审美活动既保持对现实维度的深刻观照,又需在形上维度实现主客体的有机统一。通过追溯孔子美学思想可以发现,其“观物取象”的认知路径不仅建构了艺术与现实的本源性关联,更通过“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确立起超越性价值尺度,这种既植根生活实践又具有形上超越特质的思维范式,恰恰为当代解决审美异化问题提供了历史参照系。儒家美学将伦理道德理想熔铸于艺术本体之中,及其“文质彬彬”的辩证思维方法,至今仍是构建具有人文深度与时代张力的美学体系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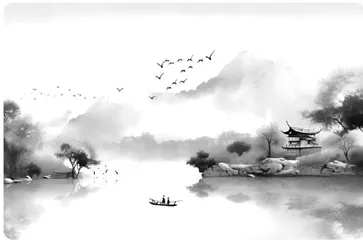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484.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