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压与凝视
作者: 龙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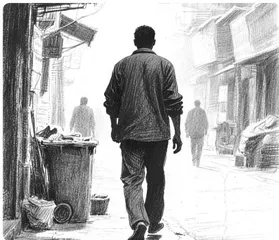
陶丽群是活跃于广西文坛的青年女作家,她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目前对她的创作研究主要围绕“土地”“女性”“温情”“出走与回归”“底层”“苦难”“桂军”等关键词展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从作家人生经历出发,对女性命运、女性形象、女性意识的分析,以及作者对女性群体深切的同情与关注;二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其乡土书写和作品中的地域特色,将地方知识融入文学创作,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三是从整体创作主题与风格分析其小说中的底层书写和对人性的展示与探索;四是从小说创作的叙事技巧和语言风格分析其小说创作的特点,她的小说展示了苦难,但同时不失温情和诗意。
总的来说,对陶丽群作品的分析,大多围绕乡土书写、女性意识、地域文化等主题展开,对其笔下人物形象的分析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女性作家在进行写作时,往往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感受为基础,诉说自身性别的人生感受与精神价值,因此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刻画细腻生动。学者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也更加注重分析女性形象,相比之下,对男性形象往往忽视或弱化,对陶丽群创作的研究也是如此。然而男性形象作为小说美学元素中的重要部分,不应被忽视,其对小说情节的发展和创作思想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对男性形象的探讨不仅是对作家作品研究的拓展,也可以反观社会转型期男性面临的生存与精神双重困境。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将男性放在被凝视的位置,对两性的关系及两性权力结构变化的研究具有现实社会意义。本文将从性别视角转换的角度,将男性放在被凝视的“他者"地位,探索陶丽群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一、乡村转型下的守旧与突破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也是一种空间的艺术,因为小说本质上就是讲述在时间的流淌中发生在空间的故事。小说中的人物活动空间可以分为大空间和小空间。大空间是指故事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主要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构成,构成小说人物活动的宏观环境。陶丽群的小说主要展现广西地区城乡转变过程中的社会的变迁、人民生活的困境和人性的挣扎,所以可以将陶丽群小说的叙事定位分为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在空间叙事的定位下对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一)乡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救赎
人们想象中的传统乡村生活,是一幅幅宁静、诗意的田园风光,但在这背后,隐藏着现实生活中男性们不为人知的艰辛与挣扎。他们以土地的耕作为主要经济来源,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却往往难以摆脱生活的困境。与此同时,父权制文化的阴影如同无形的枷锁,紧紧地束缚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使他们在传统文化的严苛要求与现实生活的重重困难之间徘徊挣扎。陶丽群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笔触,深入挖掘了这些男性角色内心的复杂情感与挣扎。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男性在父权制文化的重压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如何寻找自我的救赎,以及他们在这困境中绽放出的人性坚韧与不屈的光芒。
在小说《一塘香荷》中,李一锄的田地被廖秉德夺走,妻子因此离世,李一锄为强权所迫,忍气吞声,独自把儿子拉扯长大。然而,妻子含冤离世,自己却无力为她讨回公道,这份遗憾与愧疚深埋在李一锄的心底。后来廖秉德在李一锄妻子的二葬葬礼举行之时“负荆请罪”,在李一锄面前哭着道并想要回李一锄现在的地。面对廖秉德的忏悔,李一锄的内心经历了剧烈的挣扎与冲突,但最终他选择了宽恕,将土地以主动的方式交给了廖秉德。父权制强调男性的权力、尊严,以及他们作为保护者和责任承担者的角色。李一锄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种性别角色设定,因此,当他面对田地被抢时表现出的怯懦,与他内心秉持的男性应强大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要接受自己被欺辱却无能为力的痛苦。同时,妻子的离世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精神煎熬。正是在这般痛苦与煎熬的交织中,李一锄的人性光辉得以熠熠生辉。他并未选择沉沦于怨恨或报复的泥潭,而是在经历了剧烈的内心挣扎后毅然选择了宽恕。这一选择,不仅是对他个人品德的极高赞誉,更是对人性中宽容、善良与和解力量的深刻诠释。他的宽恕,不仅是对廖秉德的释怀,更是对自己内心痛苦的解脱与释放,最终通过宽恕找到自我内心的平静与解脱。
(二)乡村转型中的自我追求
现代农业方式冲击下的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农业方式打破了原始的传统农业农耕方式,机器的出现提高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乡村受到了时代发展带来的冲击,不同的人面对新的生活有着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生活状态。
一部分人受到城市的吸引,去城里打工生活,跟随时代的脚步追求自己的个体独立性和个人价值。在小说《冬日暖阳》中,老抽的儿子在乡长姐夫的支持下购买了卡车,三年挣了十多万后想要带着老婆和孩子去城里生活,却始终遭到父亲反对。一方面是父亲担心儿子去城里就脱离了土地,在遇见困难时能否有生活保障;另一方面是儿子在社会地位和成就上的崛起,无形中构建了一种对父亲传统权威与尊严的潜在挑战。父子之间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有着不同的人生观念与想法,形成了难以调和的思想隔阂。最后,老抽在经历了心理挣扎后,还是对自己观念中的传统父权和土地情怀释怀,同意儿子去城里买房生活。而儿子离开老抽带着妻子、儿子去城里生活,不仅是希望能在城市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实现个人的价值,也是对个体独立和自主的追求。
一部分人在农村度过了生命的大部分历程,对农村简单、淳朴的生活已经习惯,所以尽管几女已经去城里生活,自己依然不舍得离开故乡。因此,坚守在老房子里,对于父亲而言,是一种对过往罗月的致敬,对自己作为家族引领者身份的固守,也是对那份不容侵犯的个人尊严的捍卫。
陶丽群的乡村叙事中写出了乡村生活真实的面貌,也表现出了人物的多面性。她笔下的乡村空间中的男性不是以往的封建、善良或人性恶的单纯描写,而是反映了时代变化中乡村男性更加复杂的特征和生存境遇,具有社会现实意义与现实批判精神。
二、城市崛起中拼搏的边缘人
在现代化进程的强劲冲击下,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实现了飞跃式的提升,然而,这一进程并未能完全消解长久以来存在的生存压力。相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会竞争的加剧,人们逐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理负担,心理问题也日益凸显,男性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面临的生存困境依然严峻,不仅承载着社会上的重重压力,还需在家庭中扮演多重角色,这种身心的双重负荷往往使他们更容易陷入心理的困境。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489.pd原版全文
(一)物质生存压力中的坚韧与奋斗
当那些来自乡村中的人来到城市,他们往往没有受过专业教育,缺乏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这导致他们只能局限于从事一些基础的技术工种或体力劳动,只能领取微薄的薪资,生活在社会结构的较低层级。这样的现实境遇,无疑使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物质压力,努力在都市的丛林中寻找立足之地。《醉月亮》中的刘三年是骑三马仔拉人的,这么多年省吃俭用也只攒了八千多元;黄学匠是在煤气站搬煤气罐的,挣的钱要养活一家四口人;刘桂香的前夫大发在工地干活儿一天三十元,几家人合住在一个院子里。《水果早餐》中的老代是一个桶装水送水员,妻子是家庭保洁员,两人为了治病花光了积蓄,多年来过着重复而又苦涩的生活。《起舞的蝴蝶》中的周新荣的女儿是兔唇,自己靠开电器维修店和夜市摆摊赚钱,生活质量与以前相比直线下降。陶丽群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虽然都面对着生活的艰苦和物质的压力,但这并没有困住他们,无论是底层的送水工、三马仔、煤气罐搬运工,还是摆摊的小贩,他们都在用双手和汗水努力打拼着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勤劳与坚韧,不仅是对自己命运的反抗,也是人性美的体现。
(二)精神困境中的自我宽恕与心灵治愈
陶丽群的小说中展现的都是底层人民的生活,他们不仅面对物质条件的生存压力,还面临着精神方面的困扰。《夜行人咖啡馆》是描写人心理问题最突出的一篇,文中老史和丽妃经营着一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店,这处小小的空间在夜幕的掩饰下,成了老史和朋友们的治愈之地。老史和他的朋友们都是在孤儿院里度过的童年,长大后的他们都有各自的困扰。调酒师与比自己小六岁的同性相恋,却不得不面对世俗的偏见,他们在夜里一起牵手漫步在大街上寻找自己的幸福与自由。超市小老板,看似拥有幸福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实则背负着沉重的过去。他曾因冤屈入狱五年,而在他服刑的第三年,二女儿却出生了,这份屈辱与背叛,让他在人前强颜欢笑,却在人后默默承受。老史从孤儿院出来后在以捡垃圾为生时曾遭受过恶意羞辱,然而,他并未因此沉沦,反而在夜晚的咖啡店里,通过治愈那些同样在夜色中徘徊的夜行人,也治愈了自己内心的创伤。最终,他决定向丽妃求婚,勇敢地迈向新的生活。陶丽群通过《夜行人咖啡馆》这篇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城市边缘人的情感与精神困境。她以细腻的笔触和真挚的情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角色在生活的重压下如何艰难求生,又如何在夜晚的咖啡店里寻找片刻的安宁与慰藉。他们的故事,是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深刻反思。
三、凝视下的性别反思
福柯认为“凝视”背后是知识与权力的运作。“凝视就是一种话语,一种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凝视,永远是权力化的视觉模式。凝视作为一种观看方式,目光的投射,是视觉主体施加于客体的一种行为,其背后有一系列的权力运行系统,父权制就是众多权力体系其中一种。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相对于男性一直处于“他者”的位置,处于第二性的位置,是被凝视的一方,相反,男性则通常占据主体的位置,享有权力的优越地位。然而,当我们将凝视的焦点转向男性,使他们成为被观察的对象时,这种传统的权力关系便遭遇了颠覆与解构。男性不再是那个不可撼动的权力中心,而是成为被理解、被剖析的客体。这样的转变,不仅削弱了凝视所蕴含的权力意味,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男性在父权制下真实处境的契机。
回溯至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变成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女性主义者们致力于将女性从历史的边缘推向舞台中央,让人们目睹了在父权制下女性的悲惨遭遇,并为她们发出了强烈的呼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往往聚焦于女性所承受的伤害与压迫,以此为她们争取更多的关注与理解。
然而,步入21世纪后,随着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蓬勃发展,我们开始意识到,男性同样也在权力的枷锁下挣扎。陶丽群的小说,便是对这一现象的生动描绘。她笔下的男性形象,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阳刚与强大,而是融入了更多的怯懦、猥琐、脆弱等复杂特质。男性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权力掌控者,而是同样承受着权力的重压与凝视。同时,陶丽群在塑造男性形象时,并未采取尖锐的批判态度,而是从更为深刻的人性层面去审视他们。她给予了男性充分的理解与同情,将他们还原为真实的世俗个体,并寄予了无言的关怀与体恤。这种男性关怀,不仅是对男性个体的深切同情,更是对整个性别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新构建。
陶丽群还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女性自身价值的深刻理解与追求。她看到了父权制背后的男性真实面貌,也目睹了女性所承受的苦难。因此,她选择将男性从神坛上拉下,赋予女性更多的主体性与话语权。在她的作品中,女性形象逐渐焕发出强势与主体的光芒。她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价值与幸福。这种两性性别权力的微妙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与女权运动的蓬勃兴起,更体现了人们对性别关系的新认知与新理解。
最后,两性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应成为划分高低贵贱的依据。男女性别之间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结、相互影响、相互包容的。因此,文学创作应致力于破除凝视背后的权力机制,站在人性的高度上,给予底层生活的人民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促进两性的和谐发展,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
陶丽群笔下的男性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承受着生活的物质与精神的困境,在乡村,他们追求自我价值,适应时代变迁;在城市,他们以不屈的精神应对物质挑战,同时在精神困境中寻找自我宽恕与疗愈。陶丽群站在人性的高度,以深切的同情和充分的理解,不仅描绘了底层男性的真实生活与内心世界,洞察了人性、社会与时代,颂扬了人性的美好与坚韧,更表达了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追求与促进两性和谐发展的希望,引人深思、令人动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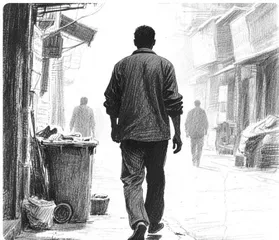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489.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