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的文化记忆研究
作者: 熊一宁当今所论的“记忆”,不仅是个人的心理机能,它已超越个人心理范畴,深植于社会集体之中,形成一种文化记忆。它不仅隐藏在个人的行为和思想中,而且保存在遗迹场所和地方性标志等物质符号当中,具有一种文化的象征意义。20世纪80年代,扬·阿斯曼与阿莱达·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20世纪80年代末,迟子建步入文坛。她聚焦于民间百姓的生活,以东北的漠河、哈尔滨等地为背景,用女性作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过去与当下的社会变迁与人生百态;她从个人童年记忆的细腻描绘出发,逐步扩展至东北地域内民族与家庭的文化记忆,进而跨越至特定历史时期下多民族、跨国界的文化记忆范畴;她从文化持有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深刻剖析并揭示了20世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挑战,展现了其对于文化记忆与人类命运的深刻洞察与独到见解。
“风土”塑造的个体记忆
(一)自然对个体记忆的制约
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在《风土》中写道:“牧羊人与渔夫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然,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想象的世界,生活在炎热国度的人是创造不出圣诞老人的故事来的。”在他的概念中,风土是指某一地方的气候、地质地形、景观等自然的风土,更是指人文的风土,即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的相互关联。个体在回忆故乡风土相关的记忆时,会受到其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的影响,从而对记忆进行不同的解释和重构。东北风土为迟子建的创作提供了记忆的背景和框架,使个体在记忆过程中能够将这些信息纳入其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记忆。迟子建早期作品中,诸如《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及《原始风景》等作品,多将童年岁月与故乡风貌作为叙述的核心元素或背景设定,蕴含深厚的回忆色彩与抒情笔触,展现出鲜明的个人传记特质。迈入21世纪,迟子建的文学创作聚焦于都市社会的现实图景,她深入挖掘那些被时光遗忘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她的作品不仅精致地勾勒出其个人家庭背景、童年回忆、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及成长历程,更尤为珍贵地保存了东北地区独特的地域智慧与文化精髓,深刻地折射出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风貌,同时,也寄托了她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无尽沉思。
1986年,迟子建以其《北极村童话》初登文坛,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讨论。大兴安岭宏伟的自然景观对作家的心灵与品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赋予了她冰雪般纯净的特质。近期问世的《会唱歌的火炉》文集,收录了迟子建对往昔童年生活的诸多回忆,其中,《北极村童话》标志着其早期自传体文学创作的开端。该作品借助一位孩童的视角,细腻地捕捉了童年时期的纯真情感及对家庭与周遭环境的初步认知。这部自传体小说凝聚了青年迟子建对北极村故乡的深切眷恋与对童年的深情追忆。迟子建在北极村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这里的木屋、白夜、极光等图景深深刻入了她的心灵。她在访谈中回忆了与姥姥一起生活的往事,以及童年时在供销社买糖果的快乐时光。北极村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为她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无穷的活力,这是她的出生地和成长的摇篮,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
(二)“风土”中的自我发现
和辻哲郎把风土现象看作人们自我发现的一种方式,他认为超越是风土的表现,即人在风土中发现自我。“从个人立场来看,那是身体的自觉,但对于更为具体的基础一人之存在来说,它表现为共同体的形成方式、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式以及生产方式和房屋建造式样。所有这一切都是作为人之存在的超越性所必须包括的。”(《风土》)如此看来,具有主体性的人将自己客体化的契机存于风土之中。例如冬天,我们用服装、房屋、柴火等工具来保护自己,而当我们自身进入其中后,风土本身就成为可用的工具。寒冷会提醒人们增添衣物、加厚被褥,同时寒冷的温度也保存了冻肉、制作出了冻豆腐。人们正是在这些关系中接近风土,并由此认识我们自己。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定义了三种记忆,其中把这种将个人生活史作为对象的记忆称为个人记忆,因为它们定位并且涉及个人的过去,人们在自我遥观本我的过程中来获知他们自己过去历史的事实以及他们自己的身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认为每个人都是对他自己的回忆,个人是由回忆的材料借助想象的力量自我创造,并在文学作品中加以表现的。迟子建笔下的《北极村童话》,有着广阔的森林、清澈的河流、宁静的湖泊和壮丽的极光。这些自然景观不仅为她的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让她在描绘中实现了对故乡自然环境的深刻感悟。她通过细腻的笔触,将北极村的自然风光描绘得栩栩如生,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在迟子建早期的作品中,个体记忆主要源于她对故乡风土相关的记忆,这些记忆不仅是她构建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更是她情感归属的重要来源。迟子建在回忆和讲述故乡风土相关的记忆时,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依恋感,这种情感推动着她发现“风土”和在“风土”中塑造自我。
二、声音承载的家庭记忆
(一)哈喇泊家族喝汤的声音
迟子建在四十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中,从《北极村童话》至《碾压甲骨的车轮》,她始终将声音作为不可或缺的叙事元素融入其中。声音在迟子建的笔下,不仅是个人情感的载体,更是家族记忆的回响,声音穿透文字,直击读者心灵深处,激发起强烈的共鸣。声音,作为人类情感的共鸣载体,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与读者进行心灵的交流。
在《喝汤的声音》中,哈喇泊家族对声音的描述主要聚焦于他们喝汤时发出的独特声响。“在万吉镇,晚炊时分,你若走进他家院子,没风的日子也像有风,自屋里传出呼呼呼的声音,偶尔汤匙触碰瓷碗,这风声中就多了几声清脆的哨音。”当叙事主人公“我”即将离开时,耳畔忽然响起一阵喝汤的声响,初时犹如穿越幽邃山谷的狂风,裹挟着一种震撼山河的磅礴气势。紧接着,这喝汤的声音又渐渐转变为深沉且富有韵律的节奏感,仿佛乌苏里江的水流哈喇泊家族喝汤的声音不仅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写照,更是遥远历史的回响,也暗示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这声音不仅反映了哈喇泊家族的身体特征,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情感;这声音“像穿越幽谷的强风”,试图以它的穿透力保持记忆,反抗遗忘,它代表着哈喇泊家族对历史的铭记和对国仇家恨的深刻体验。尽管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和痛苦,但依然坚韧地活着,用喝汤的声音表达着对生命的热爱和珍视。
(二)温情的“杂音”
宇文所安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中提到:“声音从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声音。声音属于某个人,标志着个人的身份并印上他的特性。声音常常有一个名字和一张脸,而且当声音变得熟悉,聆听它,可以把我们带回到与这个人经历的沉默过往。”“文化记忆展示了日常世界中被忽略的维度和其他潜在可能性,从而对日常世界进行了拓展或补充,由此补救了存在(Dasein)在日常中所遭到的删减。通过文化记忆,人类的生命获得了在文化进化的任何阶段中都可保有的双重维度性或曰双重时间性。”(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阅读迟子建的作品不难发现,她的小说常常为读者带来一场场饱含声色的视听盛宴,声音是迟子建小说创作中常用的叙事元素,她会以细腻的笔触捕捉各种声音,勾勒出自然、历史、人文的面貌。从《北极村童话》到《喝汤的声音》都有极其丰富的声音描写,而声音所承载的个人与家族记忆也直达读者的内心深处。例如,《白雪的墓园》中火炉的嘅啪声、《花瓣饭》中炒豆子的声音、《炖马靴》中讲故事的声音,都是家庭生活的“杂音”,洋溢着温馨的家庭氛围,还原了亲情本真。在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中,声音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巧妙地利用声音,设置伏笔,在故事真相尚未完全显露之际,便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为整个叙述笼罩上一层神秘的氛围。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步展开,读者要么会因自己先前的猜测得到验证而感到满足,要么会突然领悟,原来那些先行呈现的声音早已微妙地预示着情节的奥秘。更为精妙的是,声音伏笔与后续情节发展的相互呼应,使得小说的结构更加严谨和精巧。迟子建善于描写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思想上的碰撞,也正是因为把这些思想紧密放在一起,并重新结合,才能够形成整体的家庭记忆。
三、文化记忆的功能性意义
(一)作为个人经历的记录
齐格蒙特·鲍曼在《共同体》中透彻地总结出身份认同之所以在当今社会如此流行,那是因为“它的引人关注和引起的激情,归功于它是共同体的一个替代品:是那个所谓的‘自然家园’的替代品,或者是那个不管外面刮的风有多么寒冷,但待在家里都感觉温暖的圈子的替代品。在我们这个迅速被私人化个体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这两者,无论是哪一个,都是不可实现的,而且正是这一原因,他们中无论是哪一个,都能被安全地想象为一个充满确定性与信赖的舒适的庇护所,正是这一原因,它们才成了人们热切追求的东西”。
迟子建在作品中书写了她快乐而又纯真的童年生活、温馨的家庭与亲人、记忆中的故乡景致与都市风貌、四季更迭中的自然变迁,以及雄伟的山峦与蜿蜒不息的黑龙江、松花江等河流。这些元素是贯穿她生命的“核心要素”,共同编织了她个人成长的记忆画卷,无疑成为她独特个性与身份特征的显著标志。这种意识在她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逐渐形成并巩固了她对自我形象的认同,即自我身份的认同。在莫里斯·哈布瓦赫看来,记忆是一种重塑机制,借此我们可以构建作为整体的自我,“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迟子建是东北黑土地的女儿,她所有的生命感悟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从纯真的童年到成熟的中年,从文学创作初期对童年与故乡的深切怀念到在居住城市对往昔与今朝的密切关注,迟子建的文学作品中记录了一位作家的文学成长轨迹。
(二)对抗遗忘,理解现实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站在时间层面上来理解这句话,它指称的是时间的单向度性和人类经验的不可复制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可能被逐渐遗忘。鄂温克族的古老文明明显处于不利的位置,在强势文化的包围下,必然被削弱、冲击甚至面临被解体的危险。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重新审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思考现代文明引发的危机,谱写了鄂温克民族族群的变迁史。迟子建对民族创伤记忆的描写勾连起无数生命个体的创伤碎片与时代印痕,构建独特的“创伤记忆场域”。迟子建的作品通过文化记忆书写,保留了东北地域的历史记忆,让读者能够从中了解到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命运。
迟子建的小说以东北地域为背景,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这片土地上的百年历史与现实。她的作品不仅呈现了东北的自然风光、风俗习惯,还深刻地揭示了东北人民在历史变迁中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她笔下的故事往往与东北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通过讲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展现了东北人民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精神品质。这些故事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东北文化的魅力,还激发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归属感。迟子建的小说作为一种记忆媒介,深刻地融合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多元面貌,并通过东北地区作为记忆的地理与文化场域,开辟出广阔而深远的意义阐释维度,往往能够唤起读者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或事件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可能是关于战争、灾难、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也可能是关于日常生活、亲情友情等平凡而珍贵的瞬间。
文化记忆不仅是人类不同的身份印记,地域特色之鲜明印记,更是民族时代精神之核心坐标。它好似桥梁般地连接着过往与现今、个体与集体,还深刻地指引着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形成路径与社会话语体系的建构框架,从而展现出无可估量的重要价值。迟子建文学创作的整体性成功地架起了沟通东北地区百年历史现实的桥梁,其小说作品起始于个体记忆的细腻描绘,继而超越了个体视角的局限与狭隘,最终实现了对集体记忆与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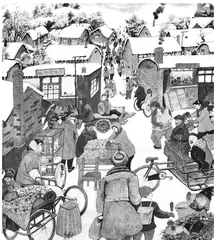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490.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