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视角下《鸡蛋的胜利》中父亲形象的悲剧溯源
作者: 王文杰舍伍德·安德森(下文简称安德森)是20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被福克纳誉为“美国现代文学之父”,他推动了美国文学向现代主义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海明威、福克纳等人。现代主义文学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潜意识,并在文体形式上大胆创新。在《鸡蛋的胜利》中,安德森以“我”的视角,通过儿时的回忆讲述父母的奋斗经历。父母为改善生活,先后经营养鸡场和餐馆,但均以失败告终。小说情节简单,语言朴素,几乎没有景物描写,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屡遭挫折却执着逐梦的父亲形象,深刻地揭示了普通人在现实中追求理想的无奈与悲哀。随着小说的发展,父亲的心理也逐渐发生变化,由快乐的本我转变成了压抑的超我,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处于矛盾中超我的父亲又迫于现实被吞噬了自我。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对父亲的精神进行分析,从心理层面解读小说中父亲的人物形象及造成其悲剧的原因。
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本我遵循享乐主义,追求欲望满足而不顾现实;超我以道德准则约束行为,追求善良;自我则在二者之间协调,既要满足本我的需求,又需遵循超我的道德标准,遵循现实原则。对于心智健全的人而言,这三者应保持平衡。自我在满足欲望的同时,也要符合道德规范。当本我、超我、自我之间出现冲突时,人便可能产生焦虑和压抑,陷入内外矛盾之中,从而影响心理健康和个人发展。
《鸡蛋的胜利》中父亲这一人物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实现了由本我到超我,最终自我崩溃的不平衡状态。
二、利用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结构理论对人物父亲进行精神分析
(一)快乐的本我
本我遵循“快乐原则”,其核心在于减少紧张感,或在无法彻底消除时,将紧张维持在最低水平,从而达到趋乐避苦的目的。弗洛伊德曾指出:“我们整个心理活动似乎都在努力追求快乐、避免痛苦,并且自然而然地受到快乐原则的支配。”本我是无法避免的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在结婚前,父亲正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快乐的人。他是一个淳朴的农场工人,拥有一匹属于自己的马,过着自给自足、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他的日常是规律而轻松的:白天耕作,晚上和同伴们在镇上的酒馆里喝酒、聊天儿,享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交流。他不需要去思考未来的生计,也无须承受社会期待的压力。在这个阶段,他的心理状态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现出一种近乎原始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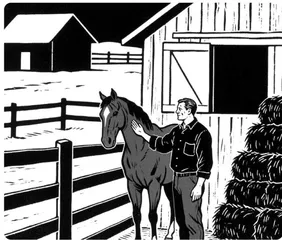
这一时期的父亲,完全顺从本我对即时满足的追求。他的快乐源于简单的劳动、自由的时间、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他无须承担复杂的社会责任,也未曾思考过“成功”或“失败”的意义。对他而言,生活是直接的,是可以触摸的,就像他驾驭的那匹马,只需要在阳光下驰骋,无须考虑远方的终点。
然而,这种平衡是脆弱的。本我的满足是短暂的,当社会责任、婚姻、家庭乃至外部世界的价值观侵入时,它不可避免地会被超我所压制,最终陷入与现实的冲突之中。而这一冲突,也成了父亲悲剧的开端。
(二)压抑的超我
超我遵循的是“道德原则”。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道德化自我,由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社会文化和道德教育逐步形成。弗洛伊德指出,超我有三大功能:一是抑制本我的冲动,尤其是社会不容的攻击性行为;二是引导自我,以符合社会规范的目标取代低层次的现实目标;三是促使个人追求理想,实现人格的完善。通过内化道德准则和社会价值观,超我在个体心理中发挥着监督、批判和约束的作用。
在小说中,父亲的超我源于妻子的规训引导,也源于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结婚后,原本满足于乡村生活、遵循本我快乐原则的父亲,受到了妻子对“更好生活”的向往的影响,他开始相信:只有成功,只有财富,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在那个年代,“美国梦”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信仰,它告诉人们一只要努力奋斗,就能实现阶级跃迁,获得幸福。然而,这种信仰不仅塑造了父亲的雄心,也成了他无法挣脱的枷锁。
为了摆脱农场工人的身份,父亲决定创业,投身“美国梦”的追逐。他先是开设了养鸡场,试图通过鸡蛋贸易改变命运。然而,现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美好,饲养鸡只的艰辛、市场的不确定性、经济的困境,让他屡屡受挫。当养鸡场失败后,他并未放弃,而是继续寻找其他致富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父亲的超我逐渐取代了他的本我。如果说本我时期的父亲仍然是一个单纯快乐的人,那么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怀疑、焦虑、痛苦。他的目标不再是“享受生活”,而是“证明自己”。他不再能享受简单的日子,而是不断被“如何成功”的问题折磨。
“畸形鸡”的出现是父亲心理转变的关键节点。面对经济压力,他产生了一个扭曲的想法如果正常的养鸡无法盈利,那么展示“畸形鸡”
或许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带来财富。这一刻,他的超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道德约束,而是社会成功逻辑的扭曲体现。他开始相信:只要能够盈利,不择手段也是合理的。
后来,失败让父亲变得越发绝望,他不断调整策略,试图迎合社会需求。开旅馆后,他努力“讨好”客人,希望借助娱乐性的表演来吸引生意。他不再是那个驾驭马匹、自由自在的农场工人,而是变成了一个为迎合他人自光而表演的小丑。
他的本我被完全压制,他的自我被超我主导,他不再追求快乐,而是被社会的成功逻辑所驱使。然而,这种被动的迎合并未带来真正的成功,反而让他的精神逐渐崩溃。
在弗洛伊德看来,当超我过度压制本我,而自我又无力调和二者的冲突时,个体可能会陷入精神痛苦,甚至人格扭曲。父亲的结局正是如此他从一个淳朴、自由的农场工人,变成了一个扭曲、畸变的失败者。他不仅没有实现“美国梦”,反而被其吞噬,成为社会价值观的牺牲品。
小说的悲剧在于:父亲最终成了他曾经展示的“畸形鸡”。畸形鸡是扭曲的,是社会异化的产物,而父亲也是如此。他被社会的超我塑造,却最终被其毁灭。
(三)被吞噬的自我
自我遵循“现实原则”,通过个体的后天学习,以及与环境的接触逐步形成。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无意识的,无法直接面对现实世界。为促使个体与现实互动,自我由本我中分化而出,成为其与外部世界的中介。作为理性且具现实感的部分,自我在调节本能冲动与现实要求之间发挥着关键作用。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社会进入了高速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彼时,美国涌现出大量白手起家的传奇企业家,他们的故事成为一代美国人心中的信仰。这种叙事塑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一只要努力奋斗,就能跨越阶级,实现梦想。
父亲的妻子一“我”的母亲,便深深地沉浸在这种“美国梦”的幻想之中。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母亲虽然过着平凡的生活,却对那些白手起家的商业巨子充满敬仰。在她的灌输下,父亲的自我开始觉醒,他不再满足于乡村工人的平静生活,而是开始怀揣更大的抱负,想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实现社会价值。他不再是单纯追求快乐的本我个体,而是一个被现实拉入梦想旋涡的普通人。
然而,理想终究敌不过现实的残酷。父亲并没有任何商业经验,也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源。他的第一步创业一一养鸡场,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成功,反而因经营不善导致严重亏损。他拼尽全力维持生计,努力学习如何管理生意,但现实却一次次向他展示资本社会的冷酷无情:市场并不仁慈,努力并不必然带来回报。当养鸡场失败后,父亲的自我开始动摇。他不再是那个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男人,而是开始产生焦虑与恐惧。他的内心矛盾加剧,一方面,他仍然渴望成功,不愿意放弃梦想;另一方面,他开始质疑自己的能力,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条道路。
“畸形鸡”的出现,使父亲的心理发生了进一步的裂变。在现实压力下,他不得不采取一些异化的方式来获取金钱,甚至违背了原本的道德感。这正是自我在无力调和本我与超我时的畸变表现。
后来,父亲转向开旅馆,以为这次能够东山再起。然而,现实依旧无情,他的旅馆生意冷冷清清,根本无法支撑家庭的生计。为了吸引顾客,他甚至不得不靠滑稽的表演和一些离奇的噱头来博取注意一他“把鸡蛋立在柜台上,它朝一边倒下。他尝试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会在手掌中搓动鸡蛋,说一些关于电流的神奇之处和重心的规律的鬼话”,不仅如此,他还展示畸形鸡、将鸡蛋塞入瓶子等方式取悦客人,努力扮演一个合格的“商人”。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未让他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反而使他越来越像一个为了讨好他人而扭曲自我的马戏演员。
“美国梦”的承诺最终破灭了,父亲的现实处境越来越糟。他的身体疲惫,精神压抑,他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全力以赴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他已经倾尽所有,但命运却似乎在与他作对,让他的每一次尝试都走向失败。
最终,父亲跪倒在母亲面前,像个孩子一样号陶大哭。这不仅是一次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自我的彻底崩溃一他终于意识到,现实世界的逻辑远比“美国梦”更为复杂,而自己只是这个社会体系中的一颗微不足道的棋子。如果说养鸡场的失败让他产生了怀疑,旅馆的失败让他感到痛苦,那么这一刻,他终于彻底认清了现实的残酷,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自我不再是那个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挣扎的存在,而是最终被现实完全吞噬。“他最终变成了他曾经展览的‘畸形鸡’”—现实让他变得扭曲、绝望,而社会却冷漠地看着他的挣扎,无人施以援手。
《鸡蛋的胜利》中的父亲在两次生意失败后,变成一个“畸人”,他的悲剧不仅源于个人性格的缺陷,更与社会背景和心理结构的失衡密切相关。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父亲的人生进行分析解读,可以发现他的命运与本我、超我、自我有着密切关系。一旦本我、超我、自我的平衡被打破,父亲便陷入精神崩塌的旋涡之中,最终导致梦想破灭。这种文学镜像启示我们:人们应当对自己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在平凡生活中求真务实、乐观处世,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平衡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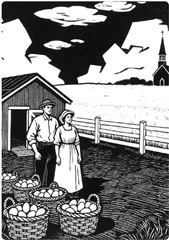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499.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