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狐记》,制造人类的新朋友
作者:黑麦 在人类的叙事里,狐狸的野性常常被简化为“狡黠”,但狐狸的本质,远不止如此,自然环境塑造着它们的习性与智慧,北美赤狐会模仿郊狼的步态,以避免被捕食者注意;北极狐的毛色会随季节更替在雪白与灰褐间切换伪装;狐狸的狩猎策略也充满弹性,它们懂得侦查、伏击,甚至合作驱赶猎物。
在人类的叙事里,狐狸的野性常常被简化为“狡黠”,但狐狸的本质,远不止如此,自然环境塑造着它们的习性与智慧,北美赤狐会模仿郊狼的步态,以避免被捕食者注意;北极狐的毛色会随季节更替在雪白与灰褐间切换伪装;狐狸的狩猎策略也充满弹性,它们懂得侦查、伏击,甚至合作驱赶猎物。除了能计算生存的风险,狐狸也在人类社会的扩张中学会了在楼宇间穿梭,并在人类丢弃的厨余中寻觅可食用的部分。这种适应性,似乎也代表了一种野性的进阶,对变化世界的敏锐回应替代了原始的蛮勇。
在《狗的家世》一书中,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揭示了人类与狗之间互动的历史演变,以及狗从狼到家犬的驯化过程。那么既然狐狸与狗都同属于犬科动物,这些已经开始接近人类生存圈的狐狸,会否成为人类的新朋友?或者说,把狐狸“打造”成一条狗,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在莱斯诺伊,这个位于新西伯利亚细胞遗传学研究所附近的一处实验农场里,被驯化后的银狐,如宠物一般亲近饲养者,更为显著的是,它们在外形上也产生了与狗相似的特征。那么,这些“成果”,这些“友善”的狐狸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德米特里·别利亚耶夫(Dmitry Belyayev)是苏联遗传学家,他被科学界誉为现代遗传学的先驱人物。二战后,这位曾应征入伍,并在负伤后获得数枚军功章的研究者,终于回到了实验室,进入了莫斯科毛皮养殖动物研究所工作。
德米特里·别利亚耶夫(Dmitry Belyayev)是苏联遗传学家,他被科学界誉为现代遗传学的先驱人物。二战后,这位曾应征入伍,并在负伤后获得数枚军功章的研究者,终于回到了实验室,进入了莫斯科毛皮养殖动物研究所工作。
在上世纪中叶,苏联的皮草贸易成为计划经济下的新产物,国有农场垄断了貂、狐狸等毛皮生产,将这些“劳动人民的奢侈品”作为硬通货出口,换取外汇。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百货商场里,皮草专柜需凭特殊票证购买,成为苏联精英的身份图腾,而在西方的市场上,苏联货也意味着皮毛的顶级品质。
银狐是赤狐(Vulpes vulpes fulva)的变种,由于基因突变导致毛色呈现银灰色或纯白色,形成独特的“霜雾”效果。这种皮毛密度高、柔软轻盈,稀有性进一步推高了市场价值,因此银狐皮草也被称为“软黄金”。
对于皮毛市场而言,银狐是珍贵的“原料”,对于别利亚耶夫而言,银狐则有着不同的价值。70多年前,一个大胆的假设在别利亚耶夫脑海中展开,他提出一个假设:温顺、对人类表现出最强亲社会性的个体,能否被驯化,那些“温柔”的特征,是否能证明“温顺性相关的基因”的存在,并与后代存在遗传关联。
简单说,别利亚耶夫试图用人为育种的方式,观察、培育狐狸,重现1.5万年前,人类把狼驯化为狗的全过程。他坚信,一旦实验成功,一系列遗传学问题将迎刃而解。
上世纪50年代初,就在这项研究刚刚启动时,别利亚耶夫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当时地位显赫的苏联农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出于政治考量,把来自西方的遗传学称为苏维埃的敌人,他批判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说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内容”,也正因此,若干科学家遭到了逮捕和杀害。
在这样的环境下,别利亚耶夫仍然撰写了一篇关于银黑狐银色皮毛的变异和遗传的论文,并始终坚信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他将自己的遗传学研究伪装成动物生理学研究。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遗传学家的迫害有所缓和。也正是在那一时期,别利亚耶夫和他的学生柳德米拉·特鲁特(Lyudmila Trut)正式启动了驯狐实验。他们把驯化基地设立在距离莫斯科约3200公里的西伯利亚,在那个冬季气温达到零下40℃的地方,找到了一片自由的学术天地。 时间来到1960年秋天,实验团队已经陆续培育了八代狐狸,然而它们的变化仍然相当微小。当有人靠近笼子时,大多数狐狸都表现得非常凶猛,小部分狐狸缩在笼子后面,但也绝不安静。从这些狐狸中,特鲁特和别利亚耶夫选出几只看似温顺的个体,将它们作为亲代来繁育下一代。
时间来到1960年秋天,实验团队已经陆续培育了八代狐狸,然而它们的变化仍然相当微小。当有人靠近笼子时,大多数狐狸都表现得非常凶猛,小部分狐狸缩在笼子后面,但也绝不安静。从这些狐狸中,特鲁特和别利亚耶夫选出几只看似温顺的个体,将它们作为亲代来繁育下一代。
不久,两只明显与众不同的小狐狸诞生了。与同伴比起来它们明显更为沉静,特鲁特看到它们时十分惊讶,因为这两只小狐狸已经允许科研人员将它们抱起。这一举动让别利亚耶夫信心倍增。
给宠物命名似乎也是人的天性,特鲁特给它们起名“拉斯卡”和“吉萨”,意为“温柔”和“猫咪”,自那之后,给实验室的狐狸起名就成了一种习惯,在特鲁特的回忆中,每个同事都似乎急切地盼望着给小狐狸起名,他们似乎也在期待着某种“变异”的降临。
即便是在很多年后,特鲁特仍旧记得那只名叫“恩贝尔”的小狐狸。那是在1963年4月的一个早晨,她走向围栏里的一窝小狐狸时,一只名叫恩贝尔的雄性小狐狸开始使劲地摇它的小尾巴。这是狗回应人类的标志性行为之一,在那之前,整个团队都从未听闻过这种行为。
特鲁特清楚地了解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要想让动物获得一种新的行为,它必须经过多行为相关的刺激”,但恩贝尔的行为与每种条件反射都不相关,它只是自发地开始这样做,如同她的导师预测的那样,这只小狐狸“具备了全新的特征,与生俱来的,如同狗一样的特征”。特鲁特将“卷曲的尾巴”“耷拉的耳朵”“圆脸和钝鼻子”等特征统称为“驯化综合特征”,是温顺动物的副产品。一只特立独行的狐狸
在《蚂蚁的社会世界》一书中,作者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没有生存问题时,一些蚂蚁会假装打架来消遣。这种行为就像小鸟喜好玩弄小树枝或亮晶晶的玻璃碴儿,小海豚会玩自己吐出来的气泡圈等。
小狐狸似乎也不例外,它们格外喜欢皮球,狐狸喜欢用鼻子推着球转,偶尔还在上面跳来跳去。就在实验进行到第十年时,狐狸群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变化迹象,特鲁特说它们不仅摇尾巴,还像狗一样呜咽、啜泣和舔舐,当它们面对人类时,甚至“渴望陪伴”,一些小狐狸甚至会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抬起头。
毫无疑问,观察狐狸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特鲁特特别偏爱观察一只名叫“小毛球”的狐狸,她发现“小毛球”极其渴望得到人类的关注,它似乎已经对人类产生了很强的情感联系。例如在玩抛球游戏中,“小毛球”会特别卖力;当特鲁特弯下腰,“小毛球”会跳到特鲁特的背上嗅她的头发和耳朵,轻轻地咬她的鼻子、脸颊;“小毛球”还会像猫咪一样发出与众不同的咕咕声,特鲁特说它有交流的欲望,“总是跟我‘说话’”。
1974年的某天,“小毛球”在地上发现一块饼干,叼起来就跑,它的兄弟姐妹们在后面追逐,它只好跳上沙发,把饼干藏在特鲁特背后,随后转过身怒视它的同胞;另一次,特鲁特正坐在屋外的长凳上休息,突然外围栏附近的脚步声惊醒了“小毛球”,特鲁特从未见过它对人类有那么大的敌意,“小毛球”在暮色中朝着假想中的入侵者扑过去,发出一连串的吠叫,像一只护家的狗。特鲁特小时候养过狗,她又懂动物行为学,即便如此,她仍旧对狐狸学习的“新技能”感到震惊。
几年后,别利亚耶夫在莫斯科举行的遗传学大会上为他的科研项目做了总结,他的结论显示,狐狸种群的驯服分数,每一代都在持续提高。此外,驯服的狐狸在后代中表现出的变化不仅是行为上的,也是生理上的。“经过8到10代,驯服的狐狸开始长出多色的皮毛,这种特征在家养动物中比在野生动物中更常见;随后,它们长出了类似某些犬种的松软耳朵和卷曲尾巴;经过15到20代,少数驯服的狐狸的尾巴和腿变短,并且出现了反颌。此外,家养狐狸比野生狐狸晚几周才出现恐惧反应,这种延迟与血浆皮质类固醇水平的变化有关。不止于此,家养雄狐的头骨逐渐变窄,更接近雌狐,也渐渐失去了狐狸独有的麝香气味。”简而言之,经过40多代的繁殖,别利亚耶夫在实验室中培育出了“一群友善的家养狐狸”,与其他家养动物极为相似的新特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以适应驯化”。
别利亚耶夫在1985年去世,之后,特鲁特仍旧在坚持着这场“未完成的漫长实验”。她在2016年时完成了这本《驯狐记》,并将它称为“西伯利亚的跳跃进化故事”。这的确是一场跳跃的进化之路,古人用1.5万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对狼的驯化,而狐狸的演变速度,完全超乎了遗传学家的想象。《驯狐记》出版后,84岁的特鲁特对《科学人》杂志讲述起自己一生培养过的近5万只狐狸,讲起“小毛球”之后的第43代,如猫狗一样憨态可掬。她说自己的思绪常常会落在《小王子》的故事里,在书中,狐狸告诫小王子:“你永远要为你驯服的东西负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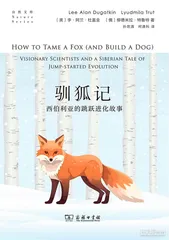 本书的译者之一柯遵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他的办公桌上堆着几本尚未被翻译完的动物书籍。他坦言,“《驯狐记》的引进,和自己养的一只名叫QQ的小狗有关”。
本书的译者之一柯遵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他的办公桌上堆着几本尚未被翻译完的动物书籍。他坦言,“《驯狐记》的引进,和自己养的一只名叫QQ的小狗有关”。
这是一只梗犬,也是柯遵科养的第一只宠物。他仍旧记得2009年,当太太抱着这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狗走进家时,自己手足无措的样子。“我从来没养过小动物,但当你开始和它近距离接触时,你就会开始被这个小生命的习性所感染。”英国哲学家马克·罗兰德写过一本《哲学家与狼》,记录了自己与狼共同生活11年的真实经历。书中的一些内容与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的柯遵科的养狗经历颇有些相似,他们似乎都喜欢透过动物的行为,审视哲学学科与生命的关联。
渐渐地,柯遵科开始发现这只“小心眼”的狗特别爱闹脾气,他常和太太说“它的性格像一只小狐狸”。几年前,柯遵科偶然在科学史学会的网站上发现了这本《驯狐记》,于是和自己的学生完成了该书籍的翻译工作。“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浪漫得像一部好莱坞电影,就连标题用的都是tame(驯服)而不是domesticate(驯化),读第二遍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在那些美好的故事之下,还隐藏着更加现实与残酷的内容。”柯遵科说。
在柯遵科看来,驯狐实验室是建立在皮草工厂上的,狐狸的大规模养殖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甚至更早。“故事中那些被优选出来的狐狸,只是养殖场中的一小部分,而大量的没有表现出驯服状的狐狸,则要经历屠宰和制成皮草。在今天看来,仍是很血腥的背景,”他继续说,“如果我们翻下地图,就会看到莱斯诺伊有一个国家级科研中心,那是一个平地而起的研究机构,我的意思是,正是在这样的体制和环境之下,才促成了别利亚耶夫的驯狐计划。”
“近70年的科研,才浓缩成一本书,不难想象,驯狐或许是个极其乏味的工作,特别是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狐狸的那些变化,可能都微不足道。”柯遵科说,“另一方面,驯化一个物种,又是漫长的过程,放在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把自己的一生铺在一个不那么确定的项目上去研究,但也正是这样的故事,才让整个事件变得有意义,才在上世纪90年代后吸引了他国科学家的参与,变成一项牵动全球的研究项目。”
柯遵科提到原版书的标题为“如何驯化狐狸,并且塑造一只‘狗’”,他认为标题的后半段很有趣,因为在分类学当中,并没有“狗”这个物种。我们所认识的狗,无论是大麦町、藏獒这种超大型犬,还是吉娃娃、约克夏这种小型犬,实际上都是狼(Canis lupus)的一个家养亚种。柯遵科最近在翻译一本名叫《达尔文的狗》的书,在翻译时,他总在思索,达尔文是如何看待“狗”这个社会学名称的呢?它可能是来自汉代的沙皮犬,也可能是起源于维京时代的猎鹿犬,它也可能是狼,是狐狸,柯遵科说:“换句话说,被驯化的狗,或许只是我们的一个幻觉。”
驯化被认为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里程碑事件,自进入全新世后总共约有2500个物种受到过人类驯化,其中被完全驯化的动物只有20~25种。在别利亚耶夫离世前,他曾想过写一本名为《人类在制造一个新朋友》的书,以此记录正在被实验性驯化的狐狸。在柯遵科看来,驯化可能是人的一种天性,我们在驯化物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自我驯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