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夫》: 一把月光引导的杀猪刀
作者: 杨殳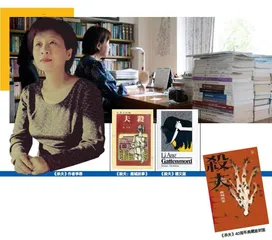
案发十多年后,故事在旧派通俗小说家陈定山的掌故系列《春申旧闻》中“复活”,题为《詹周氏杀夫》。死者由旧货贩改作屠夫,詹周氏则被写成“神经有病”的逆伦者。小说充满细节想象,写詹周氏的供述,说她怕看杀猪,却被绑在凳上强迫看,她越怕,丈夫越乐,后来杀夫分尸,用的是杀猪刀,手法是屠宰方法,是想“替猪报仇”。陈氏将事件定论为奇案,无疑是小报叙事的集大成,正是在这篇的基础上,女性作家李昂在1983年写出了颠覆传统奇案叙事的《杀夫》。
杀夫背后
李昂将故事发生地换到了自己的家乡台湾彰化县鹿港,一个封闭原始的村镇,将詹周氏改名林市,嫁给了屠夫陈江水。小说倒叙进入,开篇先说杀夫案已发生,用伪纪实风格引用了“几则新闻”,强调警方虽未查明,但理应有奸夫。即便无奸夫,逆伦女子属罪大恶极,判处枪决,并游街示众,以挽救“日欲低落的妇德”。除此,整个鹿城的“私下传言”对作案动机另有解释:此乃林市之母复仇。
开篇不确定叙述就像提出了一个设问:果真如此吗?叙述便围绕这个设问展开,从林市的角度讲述,讲她祖父如何,父亲如何,家道如何中落,只剩孤女寡母因无宗族地位而忍饥挨饿地活,母亲如何为一口吃的遭人凌辱而被族长“处置”,自己如何被“安排”给叔公,成年后又如何被叔公“交易”给屠夫——后果是最喜听女人哀号和猪仔惨叫的屠夫陈江水,自此有了专属自己的女人可以“整治”。
就像典型的社会派小说,小说搭建了一个模拟传统社会的舞台,其中的人物关系——宗族、母女、夫妻、邻里,以及丈夫与妓女、妓女与她供养的婆家——正是现实社会关系的缩影。所有人物无论性别,其观念和行事逻辑无一不处在“男权—妇德”的框架内。
小说人物关系中,核心是夫妻。夫妻关系有层,一是身体,二是经济,一个场景便交代清晰。过门当天,丈夫陈江水请客,客人散去,便趁醉“履行作丈夫的义务”。这一过程,妻子林市是何感受?先是饿得虚脱,却不能上桌,之后承受着丈夫的身体,连声惨叫,几乎昏死,最后“昏昏沉沉,兀自只嚷饿”。
于是,丈夫取来带皮带油的猪肉,塞入妻子口中。饿急了的林市边咀嚼边落泪。堪称是惊悚恐怖的新婚日,成为林市婚后生活的日常。有性虐倾向的陈江水日夜施虐。
陈江水为此付出的,是隔三岔五带回的一些米和菜。但这已足够让林市无力摆脱这种生活。由于从没有过“吃饱”的经验,因此在身体遭罪之后换来一顿饱餐,还会偶有“快乐”的感觉。她羸弱瘦小的身体在嫁人之后也确实“胖”了,而做家务伺候人,是令她心安的“熟悉的工作”。
习惯被使唤的林市伺候丈夫吃饭,自己却不敢随便添饭。丈夫赌博赢钱心情好,让她陪酒,一时兴起丢出几枚烂铜钱,“老子今天赢了,当你这个臭查某(女人)开苞钱。”而当林市得知丈夫赌博,劝了几句,便遭到挨饿的惩罚,后来实在挨不住,试着找零工,不但无人敢雇佣,还引起陈江水暴怒:这是在骂我养不起你吗?
这种关系模式正是女性主义的基本议题,没有经济权的女性便只能按照男性的规则生存,以“客体”的存在换取生存,并在规训中自我认同。
为人之尊严 难逃父权逻辑的框架
那么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女人,处境又如何呢?与夫妻关系对应,陈江水常年交往着一个妓女金花,两人颇能交心。金花说自己打算回乡种田。她不想年纪大了做娼头,逼迫别的女人,另外,老家的婆婆也要她回去。陈江水一句道破:他们要的是你的钱,当初你男人死了,还不是他们逼你出来?金花无奈,吝惜地摸自己肚皮,“那是因为我没生小孩……”仅仅几段轻描淡写,便勾勒出了另一种女性的处境。
其实,这种妓女与恩客的关系又是父权传统的典型。附属于父与夫的女人自有其功能,心理和身体都不能表现主动的欲望,而男人各个方面的需求,却可以分别诉诸家庭、职业、朋友和妓女。金花面前,陈江水形象一转,会“无助、软弱”,会一次次说起自己的凄惨童年。他作为儿子的童年故事中,有一个作为母亲的女性形象随之浮现出来:她终日要做工谋生,心疼儿子总是在哭。虽然只是片段闪回,已足够令人遐想背后的“结构”成因。
可见,李昂并没有简单把男性施暴者处理成“复仇”的对立面,而是描写不同侧面,写出人物的复杂。试看这个丈夫,出身卑微,幼时饱受欺辱,学会以暴制暴,在屠场手握猪刀时自信、游刃有余,在同性同行面前争强、霸道蛮横,在“红颜知己”面前放松、真情袒露,回到家中却俨然毫无人性的暴君——这个形象典型得几乎叫人不寒而栗。
戏剧逻辑上讲,陈江水是个死有余辜的反派,但却似乎又不是真正的元凶。因为,还有一股罗网般席卷的强大暴力,来自三姑六婆的闲言碎语,即小说开篇所谓整个鹿城的“私下传言”。
林市有个一墙之隔的邻居叫阿罔官。守寡多年的她有两大爱好,一是喜欢偷听别人夫妻生活,二是危言耸听迷信理论。
林市常因受虐而惨叫,阿罔官先是同情,赠送药膏,并像过来人那样加以指导。但背着林市,她喜欢品头论足,大谈林市不知检点,“太贪男人”,早也要、晚也要的“嚎叫”,“败坏我们女人的名声”。这一观点得到所有听众——都是女性——的认同。在同性的指控中,女性遭受虐待的感受彻底反转,变成了十足的过错。这无疑是贞节牌坊压抑真实欲望造成的扭曲。
小说有一段阿罔官为主角的插曲。儿媳指名道姓骂婆婆守不住寡,与某“奸夫”有染。阿罔官当场跌坐在地,“嘴唇发白直颤动,就是出不了声音。”显然,“淫妇”的终极侮辱足以令女人失语。当天,阿罔官就上吊自杀了——但由于绑绳结的方式被认为死心并不坚定,也不排除是一场自杀表演。可无论真假,自杀可获得至高的道德优势。于是,当阿罔官再次编排林市时,更为理直气壮,骄傲地宣称自己“有担当”,可以表明心志,“死给你们看”——而这正是林市母亲当年没能做到的,一个女人在遭人侮辱时不能以死明志,便是不可赦的罪,也是林市从母亲那里“祖传”下的原罪。
这番议论传入林市耳中,成了悲剧的转折点。她不堪承受目睹母亲受辱的恐怖记忆和荡妇耻感,于是第一次有了主动性,首先,她再不去水井边听那些长舌妇八卦。其次,任丈夫如何百般折磨,她都一声不吭。
沉默引发了陈江水的无能狂怒,变本加厉地施虐。林市咬紧牙关承受,齿缝渗出丝丝气息,“像小动物在临死绝境中喘息”。可这种绝境中的反抗,远非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热衷谈论的娜拉式觉醒,她的主动性是动物本能对痛苦的反应,是为人之尊严对羞辱的躲避,却仍未逃脱父权逻辑的框架。
而这一切都是精神崩溃的前兆。
让奇案故事拥有女性的主体性
在李昂笔下,林市的精神崩溃是创伤与迷信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发生的。由于经历接连的暴力和惊恐,她只有在昏昏睡梦中逃避,可最终连梦也变成了噩梦,无路可逃。
阿罔官上吊是林市救下的。照当地习俗,需及时拜拜才能请走到访过的“吊死鬼”。林市便拿猪脚拜拜,可陈江水不信这套,逼她吃下拜过鬼的猪脚。丈夫的不敬鬼神,让她屡屡想起阿罔官的警告:屠夫杀猪罪孽深重,需要多拜拜,否则将来下地狱就是“夫妇同罪”。这正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因得到恐吓式的关怀而陷入不得解脱的困局。
金克木先生曾评论《杀夫》,认为林市就像祥林嫂之女,但女儿比母亲强,模仿施害者举起了刀,有了个人意志,离觉醒不远了。那么,也许可以这么说,祥林嫂是毫无主体性的牺牲,出走的娜拉是有能力有意识地获得了主体性,而林市正处于祥林嫂与娜拉之间,是半梦半醒之中获得主体性的“疯女人”。
李昂贴着这个“疯女人”的内在视角写,捕捉其微妙的身体感受和心理体验,写出了一种鬼气森森的阴郁。这使得小说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具有了“写实其形象征其义”的现代主义美学效果,就像一份兼具心理学、社会学的病理报告。
这份病理报告中,有几场噩梦的描写几乎可视为心理分析样本解读。
第一场噩梦,是在因被迫吃下拜过鬼的猪脚,林市梦见暗红色的猪血和面线化成的条条“紫红色的舌头”,自己却无法自控地吃起来,吃得“眼睛往上吊”“喉咙越勒越紧”——像在上吊。第二场噩梦,发生在林市开始反抗丈夫后的一夜,她逃出家门,却撞上形似“吊死鬼”的阿罔官。回去便发高烧,梦见被捆在柱上的母亲,因饥饿难当,从自己腹肚中“掏出血肉淋漓的一团肠肚”,自己吃自己。
有学者认为,李昂在《杀夫》中有意无意承续了古典小说鬼神叙事的小传统,运用乡土恐怖民俗元素写出了不无严谨的象征结构,包含了因果报应和冤孽的母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围绕猪的一组象征结构,丈夫杀猪与性虐待的对照,反过来妻子杀夫,又与为猪“复仇”的呼应。

第三场噩梦,就是杀夫。连番噩梦后,林市已然虚实恍惚,眼中的世界似幻似真,情节走向了不确定的超自然叙事。她幻想自己攒钱买米,用陈江水“赏”的烂铜钱买了几只鸭苗,却遭陈胡乱砍杀,血肉模糊,还被带到屠场被迫观看杀猪。最后的希望破灭和极度惊恐之下,她觉得自己被男人带进了地狱,自此便真的疯了。
最后一晚遭凌辱,林市的行为变得不由自主。
李昂写道:她“定定地凝视着那月光,像被引导般,当月光侵爬到触及刀身时……伸手拿起那把猪刀。”之后,她将刀刺向丈夫,眼前闪现双重幻想,一重是欺凌母亲的人,一重是嚎叫挣扎的猪仔。斩杀肢解过程中,林市恍然觉得刀下是猪肉,连续四次自我确认,“大概是做梦了”“一定又是做梦了”……不确定的主观叙述让所谓“个人意志”变得不那么可信,似乎也摇动了整个故事的现实根基。然而,在身处黑暗且无力辨识光明的林市眼中,噩梦不就是真实吗?
李昂用一把月光引导的杀猪刀,让奇案故事拥有了女性的主体性,但《杀夫》绝非复仇爽文。甚至,整个故事下来,没有一个情绪出口,读来令人窒息。李昂曾在创作谈中表示,隐瞒与遮掩社会、政治、人性的真实性和黑暗面,假装看不到问题而认为问题不存在,是最不道德的行为,是一种虚假与伪善。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