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相机学习
作者: bt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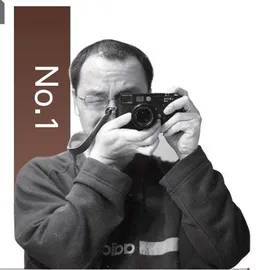
这是一份关于街拍的私人指南
我生活在上海,所以主要以上海为例。当然世界如此相像,将“上海”替换成类似的大都市也可成立。
而这又是一个摄影高度民主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拥有手机。在很多时候,用手机拍照迅捷而便利。当然我也用相机拍— 一个可以直接揣进口袋的索尼黑卡RX100VII— 一方面它可以变焦,以免惊动被摄对象;另一方面,画质仍比手机要好一些。
我不是器材党,曾经用过的最高级的相机是一个莱卡M6胶片机。回头看十几年前拍摄的胶片,的确色彩更美,更有质感;但考虑到如今胶卷价格不菲,冲洗也颇不便,拍胶片实在不可持续。所以这份街拍指南要聚焦的,其实是按下快门之前的一切— 或者毋宁说,是城市漫游和观察指南。正是在漫游和观察之中,我发现那些促使我想按下快门的东西。
街拍的独特性或许有赖于你发现的眼光,但地方本身的独特性也很要紧。根据《上海话大词典》,“野路子,上海话,非正统,非科班出身:搿个演员是野路子来个。”野路子往往意味着不受规训,趣味丛生。
为什么要街拍?为什么要在路上观察?
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或许会告诉你,“因为城市就在那里”。而日本艺术家赤濑川原平或日本插画家南伸坊——路上观察学的两位大师——会将之视为学术或艺术。法国小说家雷蒙·格诺在他的诗歌《美好的世纪》里说得更明白——
历史更替
它覆于城市之上
痕迹若隐若现
就像是阅读晦涩的作品
而我会本能地回答,因为街头好玩。城市街头是我们大写的自然,充满钢筋森林的都市是我们的新自然。街头是舞台,也是乐园;它适合漫步,也适合采风;它是人们相遇相聚之地,也暗藏着惊喜、秘密和危险。作为一个常常拿着照相机在街头游荡的人,我感觉自己有时是个记录者,有时则像猎手,有时像在做一场白日梦,有时则被现实中的超现实迷住。
我喜欢看字
招牌上的字,招牌拆除后露出的“隐字”(上海的隐字爱好者们还出了一本《隐字上海》),墙上、信箱上、橱窗里、大门上的民间手写字(五原路一扇大门上写着“请勿在大门前小便”,带有修辞学的正义),稀奇古怪的告示(贴在门上的法院判决书),各种标语或猫狗失踪的悬赏纸……
如果你更喜欢观察树皮的纹理、窨井盖的种类、窗框的纹样、柏油路面的印记、墙上的涂鸦、弄堂的牌匾、沿街晾晒的被单,那么就将之作为观察的起点吧。

合适的速度很关键
在上海的五原路、永福路、湖南路、高邮路、复兴西路等历史区域,适合步行或骑车。因为你无法要求出租车司机停车两分钟,只为让你拍下张充仁的聂耳像。沿着苏州河或黄浦江,你则可以跑起来,试试赢过那缓行的大船。乘摆渡船去看看江上风景也是好主意,不过乘观光旅游船往返长江入海口则过于硬核了,除非你想组织同事们搞一场无法早退的团建。至于淮海路,坐在911双层巴士上层前排会感觉不错。就在那里拍上半天吧,用不一样的视角,你总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街头观察者哪怕总是走同一条路也不会令人厌倦。或恰恰相反,重复走一条路更容易发现新鲜的东西。
聚焦边界和尽头
在陕西南路近淮海中路一带,一度曾有各种拿着“A货”目录、诱人深入弄堂采购假货的游击销售员,他们知道城管来的时候可以“偷渡”去马路对面——那里隶属于另一个区。不妨以更正面或隐喻的方式,理解这种边界处的活色生香。边界总是生活拥有更多可能性、最适合街拍的区域。
或者试着乘地铁到每一条线路的终点站观察:滴水湖真的很圆吗?美兰湖真的很蓝吗?或者像那位搭乘十几辆公交车去苏州的阿伯那样,以一种看似迂回、但充满探索意识的方式,以“慢游”定义“漫游”。


走一走“野路子”
在上海,穿弄堂可算一种“野路子”。 从地图上看,城市像一张由纵横交错的道路织就的、绵密的蜘蛛网。凑近(或用拇指和食指“扒开”)细看,你又会意识到,在路与路合围的区域里,总是存在着一块块空白,它们可能是小区、弄堂、花园或住宅之间的飞地。地图从不会巨细靡遗地标出每一地块的内部道路。事实上,它们只存在于精通本区地理的快递员或当地居民的脑海中。发现这些秘密道路,像希腊神话中的阿里阿德涅那样在都市迷宫里穿针引线,观察街区肌理里的野生风景,街拍便拓展了新的领地。
穿弄堂的进阶是发现那些“三通”甚至“四通”的弄堂——可以自由穿越到合围它的三条或四条马路上。比如,从富民路已倒闭的保罗酒家旁的弄堂一头扎入,可以蜿蜒曲折地绕到长乐路672弄(弄口彩票点总是挂着“今晚双色球”),再从毛细血管般狭窄的小路可一路通到襄阳北路锅贴店旁。不过,该区域目前已挂出喜气洋洋的红色横幅,“抓住城市更新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在弄堂穿梭的乐趣也是稍纵即逝的。
用上帝视角宏观地“街拍”吧
街头观察可以从微距到广角,从水管上的迷你贴纸到街头的大幅广告牌,从最微小的事物到最宏大的视野。蹲下来看一群蚂蚁或一只落下树梢翻不过身的肥胖知了是有意思的,但爬到屋顶看其他屋顶,登上上海中心看金茂大厦同样有乐趣。尤其当你觉得一栋楼丑,就更应该登上它,看看周边风景,那是看不见那栋丑楼的唯一方式。
甚至可以在飞机上体验一下上帝视角。从虹桥机场往南起飞或降落时,你可以从高空看见蜿蜒曲折的黄浦江;从浦东机场往南起飞或降落时,你则有机会看见那个绝对圆形的人工湖滴水湖。

利用“外接器官”
街头观察不只靠眼睛,还要调动听觉、嗅觉、触觉(必要时)和味觉(特别馋时)。街头观察既是五官科综合体检,也是沉浸式7D大片。合格的观察者能在尖厉的刹车声、保安“没有出入证不能进医院”的无调性复读、杂乱的鸟叫、玻璃幕墙反射出的午后光影、共享单车发烫的坐垫、仿佛越闪越快但事实上只是数字在逼近0的人行红绿灯之间辨别出35米之外的葱油饼里加了喷香的猪油。
街拍这一动作本身也对街头观察不无裨益。电子设备早已成为我们身体的延伸,它们是外接的数据采集眼,或拓展的记忆储存条。不必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你肯定错过了一张照片里的大部分细节,更何况情绪、天气、湿度、前晚的宵夜都会影响我们的感知力。甚至重看一张街头快照时,你也可能发现拍摄时没有清晰意识到的东西,那就意味着拍摄这一动作本身也是某种潜意识作用下的“观察”——观察和街拍在此时具有了同一性。
除了预料之外的惊喜或突如其来的顿悟,路上观察和街拍的意义总是与时间和记忆有关。每张照片都包含了一小段特殊的时间,正是在那几十或几百分之一秒里,一些记忆将永远存在。


试一试用截屏的方式来街拍
试一试在家利用在线地图的街景图来进行“街头”观察。在线地图的360度街景图里,城市凝固在过去某一时点,而你滑动鼠标控制屏幕上的小人儿在大街小巷东张西望或从高处俯视,就像1925年的电影《沉睡的巴黎》中描绘的图景。“于是这群资产阶级男女,作为巴黎唯一能行动的人们,开始了自己的冒险。”
甚至可以抛开电脑,仅仅坐在窗前。窗是天然的取景框,而窗框的限制并不会使你看见得更少。仅仅注视窗框外的一小方天地,你会觉得城市从你面前经过,这是街头观察的相对论。甚至可以弄个望远镜来细看或用长焦镜头拍下一切。
混用你的“工具包”
我写小说,也做一点翻译;我拍照,也写展览评论,并主持一档播客节目。有时我感觉它们并无分别:写作是翻译出心里的想法;播客是声音剧场或集体写作;摄影是挪用一小块现实世界的现成品,让图像在新语境里成为语义暧昧的词;写评论是抽身而出的检视,是思维练习。


媒介的边界并非与生俱来,它们本来就在同一个工具包里,供创作者自由取用。因而不存在取舍,只有各自特性。比如写作近乎免费,打开一个Word文档,敲击键盘,不需要项目立项、投资人、制片人、策展人、导演、演员,就可随时开始。文学翻译更像一种风格练习,要说的念头已然在那儿,只需在另一种语言里寻找适当的词语、风格和节奏,以便让自己的工作隐身。做摄影则像编排一组完全崭新的词,它们尚未被磨损,缺乏清晰的、确定的所指,甚至可以在一个蒙太奇里,就能改变自身意思。
所以用街拍来写作是可能的;用文字来创作一张“快照”同样可行。
借鉴“他城”的经验
比如,观察巴黎的方法很多适用于观察上海。法国小说家乔治·佩雷克在《详尽描述巴黎一个地方的尝试》一书中创造了穷举法:他把街头想象成自己的仓库,把观察和记录想象成一场盘点,记下一切事物和一切事件——或按佩雷克的说法,记下“在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开始一场“低到尘埃里”的冒险。
保持游戏感
街头观察是少数服务器关闭后仍然可以进行的游戏。你尽可以发挥想象力,创造属于自己的街头观察游戏。比如“穿红衣的人”:只要心里带着这个预设,你就会发现很多穿红衣的人。比如“颈椎仰角接力”:凝视一栋楼顶几分钟,直到很多路人停下脚步想看看你在看啥,等人数愈来愈多时趁机溜走。比如“系统默认跟踪者”:随机跟踪一个人。比如断章取义地拍摄路上文字(比如拍一张“请不要随意倾倒”垃圾)。
试试重复走同一条路
就像一段你熟悉的乐曲,每个小小的变奏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可以说,我看着延庆路大福里弄堂口的杂货店如何从代售扫墓班车票到代收快递、黑板上出现四个大字“禁止拍照”,再到卖起遮阳帽以及尚未被买走的遮阳帽遮住了“禁止拍照”的“禁”字——像一部发生在我脑内的延时短片。
路上观察和街拍适合独自进行
但多人一同漫步、观察城市也有益处。他人的观察兴趣点可以弥补一人观察的盲区,而新的兴趣点或许正是从“这有什么好看(拍)的?”开始萌生的。当然,多人同时窜入一条老弄堂又举着手机、相机一顿乱拍,会给人一种“这里是不是要拆迁?”的错误印象,或容易引发被观察街区的不安情绪。
向大师学习
比如,向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学习照片拼贴的艺术,对同一主题、人物或场景拍下一系列视角或景别略有差异的照片,再根据线条、形态及主观感受进行拼贴——可以是整齐的矩阵,也可以彼此堆叠,构成不规则的图形,重构出一种包括了一段时间的、展现多重视角的、更忠实地还原观者主观感受的立体主义图像。
甚至可以向文学家学习。比如,向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学习记忆的显影术。他认为人类的记忆过程有时跟宝丽来照片的记忆过程相同。而莫迪亚诺的小数《狗样的春天》里的虚构人物冉森不啻美国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化身,而三个手提箱也确有其事——1939年后被认为已遗失的、有4500多张35mm负片的“墨西哥手提箱”于2007年末重现于世,其中包括罗伯特·卡帕拍摄的大量西班牙照片。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