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玫专访:每一部戏都是一段心路历程
作者: 何映宇尽管父母都是音乐家,她却走上了一条导演之路。1958年9月,胡玫出生在北京一个音乐家庭,父亲胡德风是著名指挥家,曾任总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母亲马璇是歌唱家,胡玫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艺术熏陶,学习钢琴和声乐。
1978年,胡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与张艺谋、陈凯歌等人是同学,从此开启了追逐电影梦想的旅程。毕业后,她和同学李晓军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1985年,27岁的胡玫与李晓军合导电影《女儿楼》,该片1985年被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报评为全国十佳影片,被国际影评界评论为中国新时期第一部女性题材影片,胡玫导演被评为中国十大青年导演,获评双十佳电视剧导演。

1998年,胡玫凭借历史剧《雍正王朝》,在中央一套播出时创下央视收视的高峰,最高收视率16.7%。一个女性导演,驾驭这样一部波澜壮阔的电视剧,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翻云覆雨的朝堂争夺,都在影像中得到生动的营造与刻画。
最近,胡玫来到上海开放大学开设“胡玫表导演创作班”,希望将她导演生涯中的经验与教训都无保留地告诉那些热爱电影的学生,让他们少走弯路。
在上海教育电视台的休息室里,胡玫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自1985年拍摄第一部电影至今,胡玫走过了整整40年的光影人生,对她来说,每一部戏都是一段心路历程。
被北电导演系和表演系同时录取
《新民周刊》:你的父亲是著名指挥家胡德风,母亲也是一位歌唱家,生在一个音乐家庭,父母没有期望你走音乐这条路吗?
胡玫:他们当然是有的。我们家是三兄妹,两个哥哥和我,从小就接受音乐教育。那时家里买了一架钢琴,我从4岁上幼儿园时起就开始学钢琴,因而我的童年特别枯燥,经常哭闹。我们这些小孩要按时练琴,开始是半个小时,后来延长至一个小时。别的孩子都在玩,我却得呆在家里弹钢琴。

后来我对钢琴产生了恐惧感,我弹不好的话,我妈妈会拿小棍子打我。我发现可能我的性格真的不太习惯长期坐在一个地方做一件事。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我会打毛衣,我也会去拆装缝纫机和自行车,对所有新鲜事物都感兴趣。除了学钢琴,我还喜欢唱歌,拉小提琴、手风琴,弹竖琴,学了很多乐器,但每个乐器都不精。包括声乐,著名歌唱家郭淑珍老师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从小歌唱得好,也曾参加过很多歌唱大赛。我十六七岁时和吴祖光、新凤霞夫妇的女儿吴霜都是郭老师的得意门生,后来郭淑珍举办音乐会,她说她除了有29个获得国际大奖的学生,还有半个学生,那半个学生没有坚持到底,改做了导演,她就是胡玫。
《新民周刊》:是你父亲建议你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
胡玫:不是。那时我的第一愿望是想当兵,当时当兵很受欢迎。1974年左右,国家停止招兵,只有总政话剧团的《万水千山》在招小演员。我爸把我推荐去参加考试,当时跟我们一起考试的有龚雪、黄梅莹、陈佩斯、洪学敏等人。我的考试成绩很优秀,因为我会弹钢琴,能弹奏钢琴协奏曲《红灯记》,声乐好,舞蹈也不错,小时候跟中国芭蕾舞团的老师学过一点。就这样我进入了《万水千山》剧组。陈佩斯是道具组的组长,我和洪学敏等人都在道具组负责点袜子、绑腿。我们既要演出,上台演小红军,又要负责道具工作。这些早期的演戏经验给了我很好的历练。我从小比较独特,作为独女有点霸道,是个比较拧巴的孩子。
后来我爸恢复了工作,回到北京。那时候,我赶上了78级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北电就在我们家旁边,隔着一堵墙。我们是总政大院。此时我已经在总政话剧团上班,每天骑自行车路过北京电影学院,那里人山人海,每天围了很多人。其实我很想去看看,但不敢。那时候刘晓庆、李秀明最火,我想我这长相当不了明星,因为我周围都是龚雪、黄梅莹那样特别漂亮的人。我觉得我不行,怎么能上电影学院呢?因为这我一直没报名,但招生季有60天,到最后还差3天时,我犹豫了。我想错过了可能就没机会了。当时总政话剧团准备培养我,我已经开始在戏里有台词了,他们准备让我当台柱子,当主演。我就在犹豫是要提干还是要去上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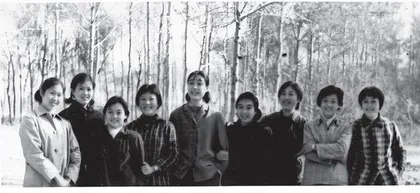
最后还剩3天,我去上班时拐了个弯进了北电,拿了一份招生简章看看,这完全是偶然。我本想去学表演,从来没想过要当导演。可是翻开第一页是导演系,后面才是编剧、摄影、美术,最后一页是表演。看完导演系的招生简章后,我就没往下翻,直接奔向导演系的报名处。当时一位老师在收学生报名表。他问我要报导演系吗。我说对,我说我觉得挺适合的,他问我怎么适合。我说我从小就喜欢写东西,我们部队演出的小品都是我写的。我还负责《万水千山》后台的黑板报工作。他说:“你是总政的?那你填个表吧。”我就填表了。这时一个人在后面拍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是马精武老师,他问:“同学,你是哪的?”我说:“我是总政话剧团的。”他说:“你怎么报导演系?你走错门了。让我看看你的表演,你不是学表演的吗?”
我说:“是的,我是演员,但我改主意了,想报导演系。”他说女孩子不适合当导演,然后把我拉到一边说:“你把这个也填了吧,我告诉你,你要考的话,我们表演系会要你。”我当时很震惊。可能是因为报考的人不多,我又穿着军装,一个小女兵的样子比较显眼吧。后来我表演系和导演系都报了。我觉得是得益于我的性格,一般女孩子都会听话。我回去告诉我爸说我报了导演系,我们家都炸锅了,说我:胡闹,怎么想起学导演来了。因为我们在总政话剧团时,给我们当导演的总政文化部领导陈其通,是将军,他们认为我当不了导演。
《新民周刊》:但是两个系都录取了,你选了导演系?
胡玫:我就没理会马精武老师。后来马精武一直耿耿于怀,说:“老师把通知书给你发了,你怎么这样?”
《新民周刊》:当时导演系里是不是男生特别多,女生特别少?
胡玫:不是,我们班28个学生里有9个女生,所以比例不低了。我原本是总政的编制,但是我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以后就得转业,因为总政话剧团不是搞影视的。他们跟我谈说要我转业,我想转业就没工资,等于归零了。后来我想了个主意,给总政文化部部长刘白羽写了一封信,说我特别热爱影视艺术,我是总政培养的,转业很遗憾。我提到总政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建议让我去那里,学完后为八一厂效力。没想到他在后来的总政的干部表彰大会上讲了这件事,说八一厂送去考试的四个人都没考上,而总政话剧团的一个孩子考上了,没必要逼她转业,我们应当为部队留住人才。就这样我转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毕业时,我和李晓军被分到八一厂。但后来,我意识到在八一厂创作会有局限,因为作为女导演,我想拍情感戏,而他们要拍的是钢铁长城般的意志,要拍战争片。当时我很郁闷,正好那时张艺谋、张军钊、陈凯歌、何群他们毕业找不到机会。这时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韦必达向他们伸出橄榄枝,说:“你们到我这里来,给你们一部戏让你们拍,你们随便挑。”

他们就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了《一个和八个》。这片子一拍出来,整个中国电影界都轰动了。影片放到我们这边时,我去看了,当时看得热血沸腾。旁边有些年纪大的观众却拍案而起说:“什么破电影,什么乱七八糟的!”说完呼啦啦走了。后来又放映了第二部《黄土地》,简直让我痴迷,我觉得太棒了!电影语言的运用已经达到了中国电影从未达到过的高度!
从八一厂导演到
广告公司经理
《新民周刊》:1984年,你执导了反映军队女性情感生活的探索性故事片《女儿楼》,怎么会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
胡玫:此时邓小平同志正提出解放思想,起用年轻人,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八一厂这边萧穆厂长找我说:“胡玫,我们现在让你带头成立一个青年摄制组。”机会就这么来了,真是天上掉馅饼!那时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会计都是团级,而我只是个排级,要是按资历排辈,怎么会轮到我来拍电影呢?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李晓军告诉我,他找到一篇特别好的小说《女儿楼》,他觉得不错,很适合我。我看了这篇小说,作者是丁小琦,她父亲当时是沈阳军区的宣传部长。丁小琦特别有才华,她写的处女作就是《女儿楼》。然后我就和李晓军一起把它改编成了电影,由我们俩人联合执导。接着我们又拍了《远离战争年代》这部片子。当时被国外影视界注意到,作品被选到国际电影节去。

《新民周刊》:你曾经获得去法国留学的机会,但后来没去成,从八一厂出来成了个体户?
胡玫: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了意大利的萨尔索国际电影节。虽然是个小众电影节,但选片人马可·穆勒说特别喜欢这个片子。还有当时的巴黎电视台台长杜阿梅(马可·穆勒前妻),他们两人把我带到了意大利。
在意大利我结识了法国人类学电影家协会主席,他很欣赏我,他给我一笔法国的国家奖学金,让他的秘书到中国把我接到法国去留学。我要去法国的话,我就要从八一厂转业,涉及军籍问题。我写了很多封申请信,最后把事情说清楚了,他们才放我走。
可是后来发生了些变故,我留学的事黄了,没去成。我也没有了单位,这可怎么办?我又去找八一厂。当时副厂长拍着桌子对我说:“我们八一厂也不是大车店,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太没面子了啊,我想算了,那我就走吧。
这样呢,我就变成了一个特别早接触社会的个体户。当时我的同学什么的都还在公家的单位呢,而我就没单位了,我就开始担心,哎呀不能生病,因为生病了要花钱去看病,不能生病!我还想,我得挣钱,这是我第一次对钱有了全新的认识。出于无奈,我成立了一家广告公司,之后做了10年的广告公司总经理。
我和歌手苏小明小时候是同班同学,那时候,我和苏小明一块出去拉广告。小明特直爽、仗义,说话特直,很真实,真帮我。我们给温州特陶厂做广告卖尿盆、卖马桶,广告一放,嘿,零库存,那马桶全卖光了啊,很牛吧。就是这样,十年,接了好多广告,挺火的,也赚到了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段经历使得我换了一个角度看电影,对电影有了新的思考。就是说电影它也是个产品啊,你片子好不好,一个拷贝你都卖不出来,哎呀你真丢人,作为一个商品你应该卖得好啊。因此,我开始关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