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大学才能证明你自己
作者: 聂辉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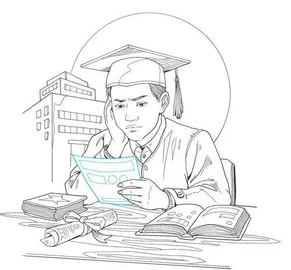
1973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斯彭思,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发表于国际顶级的《经济学季刊》上。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信号发射模型的经典之作,斯彭思也因此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看上去非常“无聊”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求学读书呢?
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境:你和你周围的小伙伴们都想去本地一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上班。这家公司需要很多聪明人,并且根据聪明程度来支付薪酬。你的小伙伴们有些很聪明,有些一般聪明,你们知道各自的聪明程度,但是公司在招聘你们之前并不知道。因此,你们和公司之间存在一种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每个人都希望进公司拿高薪,但如何证明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呢?大家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去读书。一个人要想在学校考高分,必须有很好的记忆力、推理能力和计算能力,而且越是聪明的人学起来越轻松,越是不聪明的人学起来越吃力。
当读书成为一种证明自己的信号时,你会怎么选择呢?这就要说到做出最优选择的两种规则。
首先,你需要权衡读书的成本和收益。读书的好处是,你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聪明人,毕业后就可以到企业拿更高的薪酬。读书的成本是,你耽误了几年时间,还要缴纳学费,而这几年去上班本来可以挣到一笔钱,这笔钱就是你读书的机会成本。
其次,你需要考虑其他小伙伴和公司的策略。当公司把读书作为挑选员工的手段时,如果有很多自认为聪明的小伙伴都去读书了,那么你就需要比他们多读几年书,这样才能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当聪明的小伙伴们都这么考虑时,博弈的结果就将是,读书的年份越来越长,比如从大学本科读到硕士,从硕士读到博士。
两种均衡
在这场读书博弈中,斯彭思教授推断,最终将形成两种均衡。
第一种均衡叫“分离均衡”,就是不同类型的参与人通过发射不同的信号分离出来。很聪明的一群人先去读几年书,然后进公司工作,并且在公司上班后直接获得较高薪水;而一般聪明的另一群人干脆不读书了,一开始就进公司工作,从而获得普通薪水。总之,不同聪明类型的人通过是否读书发射了不同的信号。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大家都是通过读书来发射信号的时候,想要证明自己聪明的人,究竟要读几年书才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取决于群体的智商分布,以及相应的分离成本和收益。如果一个群体中大部分人智商一般,那么少数很聪明的人只要上大学就足以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了。如果一个群体中多数人都比较聪明,那么极少数超级聪明的人为了和比较聪明的人区别开来,他们必须读完硕士或者博士。因此,读书作为一种信号,实际上是一种连续变量,可以将两种乃至多种人区分出来。
但分离均衡并非唯一的结果。如果有人发现,虽然花费了很高的代价去读书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智商,但是多读书得到的高工资并不足以弥补读书的成本,此时他就会减少读书的时间,直到读书的收益刚好等于读书的成本。
当人们发现读书带来的好处和成本一样多时,所有人都不再读书了,或者所有人都去读同样多的书,然后宁愿被公司当作普通人支付普通薪水。这样的结果叫作“混同均衡”,即所有类型的求职者都发射同样的信号,公司无法区分求职者的真实类型,只好按平均类型和平均工资来对待了。
过度证明
如果一个群体里大多数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同于少数人,而投入大量资源去证明自己,比如都去读博士,虽然信号发射会成功,但是从社会最优的角度讲,这可能导致过度证明,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因此,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应该避免每个人过度证明自己。
数年前,中国有两家主要的网约车公司:一家叫“滴滴”,另一家叫“快的”。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网约车司机,都希望选择实力强的一家。但是当时的市场形势并不明朗,对于大家来说,两家网约车公司的实力强弱都是不对称信息。于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有实力、市场规模更大,滴滴和快的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开始了长达几年的“烧钱”游戏。
后来,两家企业宣布合并为一家企业,名称就叫滴滴。为什么两家水火不容的企业突然就合并了呢?马化腾透露说:“我支持滴滴,马云支持快的。我们就像打仗,我们最高一天亏4000万元。谁也不敢收手,一收手就前功尽弃了。最后我跟马云沟通,在很多资本方的撮合下合并了。”
对于企业来说,价格战就是一个发射信号的囚徒困境。如果不敢打价格战,企业就会被市场认为是弱者,从而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是打价格战又是一种双输的结果,这就是过度发射信号。
除了读书,大家去考取各种证书,企业参与社会慈善活动,以及企业家担任一些社会荣誉职务,都属于发射信号。总之,只要你能做到别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你和别人就区分开来了,这就是分离均衡。
但是发射信号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发射信号的成本和区分之后的收益是差不多的,那么所有人都会选择同一种信号或者干脆都不发射信号,这就是混同均衡。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过度发射信号,这会导致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