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白品评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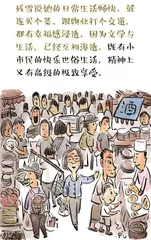
编者按:本文是作家墨白在过去20年间(2000—2019)的阅读痕迹,大多是在不同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我们既能从中能看出墨白对作品的见解与对文学的真诚,又能窥视到墨白的文学观。本刊从本期开始分三期连载,以飨读者。
作家的写作就是面对自我
作家张宇在《软弱》后记里说,自己的写作进入一种休闲状态,是轻轻松松地讲故事。这是张宇的智慧,你要是相信他,那你就上了他的当。在他的骨子里,你仍然感觉到他并不轻松。
作家李佩甫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他自己的作品里无处可藏。在《软弱》里,就印证了这句话。我们在读完《软弱》之后,我们在于富贵、王海那里,在公安局局长和他的小本子里记下的那些话里,在那个收了人家自行车贪赃不枉法的老公安何满子那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作者的那种精神自传式的内心独白。
张宇曾经私下里对笔者说过,一个作家,写到最后,面对的就是他自己。这话笔者信。莫言也曾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 :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所以,我们不能相信张宇在《软弱》后记里说的那些话语。他在他的作品里,偷偷地注入自己的血肉和灵魂,他不会成为那种只注重讲故事而忘记自己创作的人。
(本文是作者于2000年5月间在张宇长篇小说《软弱》研讨会上的发言)
内心的焦虑与理想的生活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每一个陌生的女人都是一座神秘的房子,当你没有走近她的时候,她就对你构成神秘。同样,一个陌生男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也是如此。面对一座神秘的房子,我们都会产生一种了解这所房子或者进入这所房子的渴望。在作家杨东明的长篇小说《问题太太》中,乔果和卢连璧就是这种关系。引诱乔果走出正常生活秩序的除了性的神秘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对隐秘世界的渴望。隐秘的行为和事件与神秘不同的是,神秘的力量来自我们生命本身,是自然的;而隐秘的力量则来自社会、政治和文化,是人为的。在《问题太太》里,乔果和刘仁杰的关系就属于这种关系。对自然生命的神秘和对人为的隐秘世界渴望,是现实生活中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产生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笔者认为《问题太太》是一部关注人性、关注人类个性解放的小说。杨东明把性赤裸裸地置放在我们所谓的伦理道德之上来进行拷问,这本身就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一种疑质,一种反抗。在我们的传统道德里,性在作为一种人类繁衍的手段的同时,更多地添加了沉重的文化内容。在传统的文化里,从来没有把性作为人类个性显现的行为和身体的愉悦来看待。因为,在中国,性成为一种理性,属于理学,是一种哲学;在西方,性成为一种神性,属于神学,是一种宗教。理性和神性的目的都是禁欲,都是对人的异化。西方宗教是把精神枷锁套在人的脖子上,而中国理学则把它套在人的心灵上。所以,显现人类个性解放的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性的问题。在《问题太太》里,当性想从伦理道德里挣脱出来的时候,它是那样的撕心裂肺,是那样的惊心动魄,是那样的焦虑不安。
杨东明是一个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起码在《最后的拍拖》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这部作品里,他把我们的日常生活,把每天所环绕着我们的那种琐碎世俗的、单调无聊的、让人不堪忍受的、为了生存而拼命奔走的生活也排除在他的小说之外。他所讲述的是关于欲望、关于激情、关于爱情、关于人的个性解放这些关联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最根本的问题。可以这样说,他用虚构的翁行天和桑乐这样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女的恋爱故事,以此来表达他的理想。
在《最后的拍拖》里,如果说,使我们震动的是翁行天对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挑战和反抗的话,那么,这种挑战和反抗的激烈更来自像桑乐这样更年轻的一代。如果说,年轻的翁行天对性的启蒙是那个远在乡下的赵婶,那么,他就是被动的。而我们看到的桑乐对翁天行的性爱却是主动的。但从这一点上看,或许杨东明想让我们明白,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桑乐对个性解放是无意识的,这恰好正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当然,翁行天的挑战是没有结果的,或者说是失败的。但他失败的原因并不具有社会学意义,而是来自生命本身的不可抗拒,他老了。从翁行天和桑乐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那就是,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就像世上所有的生物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向生命的终点。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仍然会对死亡产生恐惧,这或许就是人类与世上的其他生物不同的一点。但我们并不因此而绝望,因为消亡的是个体,而人类永远都是年轻的。理想就是我们的信念,或许从这一点上,才真正地体现了《最后的拍拖》这部小说的意义。
(本文是作者于2003年2月28日在杨东明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问题太太》,杨东明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最后的拍拖》,杨东明著,群众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残雪小说的后现代特征
在残雪小说《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从未描述过的梦境》,作家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里,我们能看到明显的后现代特征。
一、对确定事物的不确定性表达
(一)时间的不确定性。在小说《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的开篇,残雪就告诉我们,她讲述的这个故事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当然,“我”记忆里的时间是确定的:上个星期四;当下的物理时间也是明确的:今天早上……整整一个上午;但是,从记忆到达现实的过程的时间是模糊的。我们不知道从上星期四到今天上午已经过去了几天,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二)人物的不确定性。从小说的题目我们可以确定小说的主人翁叫阿梅,可是当我们读完小说后发现,小说里没有一处出现过“阿梅”这两个字,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小说题目里的阿梅,任意改成另外一个名字。譬如叫她阿雪,或者叫她阿红,或者叫她阿蓝,都是可以成立的。这是对人物名字的确定,却是对实质的人物本身的不确定。在小说的第一自然段里,出现了一个人物:那个在墙壁上捣洞的邻居。但是,一直到结尾那个捣洞的邻居再度出现时,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邻居”是男是女,是老还是幼,这个邻居没有具体的形象。在这里,人是确定的,但具体是什么样的人不确定;这个邻居,是外部世界的象征。同样,小说里的几个重要人物也都没有明确的形象。我们只知道那个大狗同他父亲一样,长着一个肥大的屁股 ;“我”的母亲的眼睛总是肿得像个蒜苞……,两只胖手……,口里喷出浓烈的大蒜臭味儿……,就连形象最明确的老李,也只不过是个矮子,脸上有许多紫疱……我们不知道母亲和老李具体的年龄,也不知道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以什么为生。
(三)事件的不确定性。那个在墙壁上捣洞的邻居所做的事件是确定的,但他为什么要在墙壁上捣洞?我们不知道,在谁家的墙壁上捣洞?我们仍然不知道;在小说中,“我”常常在写信,写完之后还要寄出去,可是信是写给谁的,又是寄给谁的,我们不知道,在这里,写信和寄信是确定的,但信件寄往何方,寄给何人,是不确定的。
二、对秩序的消解
(一)对伦理道德的消解。在小说《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里,没有丝毫的道德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一种无序的状态。“我”的母亲和老李两个人常常关在厨房里,做一些不为人知的勾当;而后,老李又来向“我”求婚。等“我”和老李结婚生了大狗之后,母亲仍然和老李保持着那种不明不白的关系。这无疑是对我们所信奉的道德秩序的挑战。
(二)对亲情关系的消解。在小说《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中,母亲常常和外人对“我”说三道四;同样,自从大狗生下来长到8岁,从来就没有叫过“我”一声“妈妈”,而是像他父亲一样向“我”说:“喂!” “我”的心脏病也是因此落下的。小说里出现的母亲和儿子,都与“我”形成敌对关系。
(三)对婚姻的消解。老李向“我”求婚的理由是“我”的母亲有一套房子。而结婚后,老李又不同“我”住在一起,他在“我”家屋角搭起的阁楼里住了三个月,就离开了,然后只是作为一个外人常常来拜访。一个丈夫对妻子来做一种礼节性的拜访,而来到之后,拜访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的母亲,这就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正常婚姻构成颠覆性。
三、叙事的实验
我们不妨先把《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当作一篇仿梦小说,当作一个没有正常逻辑思维的精神病患者的臆想。你看,一个女人在唠唠叨叨地讲述着她和母亲的关系,讲述着她和儿子大狗的关系,讲述那个好像和她没有婚姻事实的老李的关系,讲述着老李和她母亲在厨房里做出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只是在我们猜想之中的事件;你看,老李来到这个家,好像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我”的母亲;你看,“我”的母亲、老李,还有那个在墙壁上打洞的人,那个已经长到8岁的大狗,这些人都是一些与“我”正常的现实生活没有逻辑关系的人,这些人仿佛都是梦中的影子。残雪这篇小说的叙事策略接近于梦境,所以小说里的神秘气息四处蔓延。这篇小说的叙事策略给我们带来了陌生感,对读者的阅读构成挑战性。这篇小说叙事语言的实验性,对旧有的文体具有强烈的颠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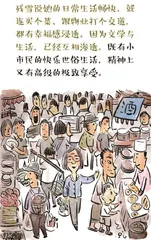
同时,《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具备了短篇小说的重要特征:小说的空间感。因为有了空间感,就给读者建立了关系。所以,在阅读中,我们不得不参与,或者说,我们不得不进入“我”的日常生活和“我”的精神世界。在残雪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情绪,那就是冷漠。正是这种冷漠,构成残雪的叙事风格。小说里的“我”在无声地接受着来自外部世界的冷漠,而她的抵抗就是无言,无言是另一种冷漠,倔强的抵抗因为外部冷漠的增添而激烈。在这里,生活的沉重和精神的压抑是难以表述的,我们只能去感受。这种冷漠成为残雪认识和感受世界的方法,这种冷漠是残酷的。因此,这种冷漠也强烈地震动着我们这些有着参与意识的阅读者的心灵。
或许,我们这些“正常的人”会把这篇小说看作是一个人的胡思乱想,而恰恰是这种胡思乱想,才真正进入“我”的精神世界;而“我”的精神世界,恰恰更接近我们的生存现实。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现实生活对我们的压抑,我们因此而看到了生活的真实,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人性的真实。我们说残雪的小说接近梦境,倒不如说她的小说更接近我们现实生活里的神秘,对于残雪的小说,我们更感兴趣的应该是她隐藏在文字背后的那些更接近我们灵魂的东西。
残雪曾经说过,她的小说表达的“形象是内部的,与外部的表现是有区别的,里面的形象是怎样的,就按照它来写作”。笔者理解残雪的这种表现内部的形象,就是人的无形的精神。“我”在逃避现实,并渴望在幻想和回忆中营造自己的时间之塔。在《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里,残雪超越了政治和文化的局限,直接进入对人类的精神世界的书写,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小说精神。
《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最初发表于1986年第6期的《天津文学》,那正是新时期先锋文学崛起的年份,而残雪这篇具有后现代的叙事特征的小说,更具有先锋性。
(本文作者创作于2005年)
穿透历史和人性的镜子
读田瑛的小说《大太阳》(《大太阳》,田瑛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使我想起了夏加尔。
夏加尔说:“什么样的画都可以,请把它倒过来看看,这样才可以了解其真实的价值。”田瑛的小说就有这种颠覆我们正常思维的力量,他用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带给了我们新奇和刺痛。
田瑛的叙事语言具有诗的质地。你看他写乌鸦:“乌鸦浑身漆黑,想必它的叫声也是漆黑的。”
你看他写酋长手里那把杀牛的刀:“刀光比火光还红,它们知道那是用什么颜色染成的。”
准确而有力量,细腻而有光泽。这样的叙事语言,在田瑛的小说里随处可见。我们甚至可以听到他文字的声音,就像一朵盛开在阳光下的罂粟花,鲜艳而诱人,有一种穿透纸背的力量。
田瑛的小说具有多重的文本意义。
说田瑛的小说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是成立的。在《大太阳》里,牛贩子的头颅被砍落在了地上,一路往低处滚动的时候,他的嘴里还吹着口哨,他的头颅在水里漂浮了许多天后,他的眼睛还睁着;睡了一星期的龙洞人,在醒来之后全都得了遗忘症;天象连日有昼无夜地晴朗起来……诸如此类,还不魔幻?你想想,如果我们的生活里没有黑夜,或者没有白天,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说田瑛的小说是寓言,也是成立的。一个氏族因为一个梦而迁徙,又因为毁掉自己种植的树林炼一座金山,去购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的世界,最终因为水源的消失而灭绝,诸如此类的故事,还不是寓言?但,笔者更觉得他的小说是仿梦的,是一个梦境,是一个关于我们人类的梦。他从牛的视角,来写人对牛的屠杀,当杀牛的刀插入牛的脖子之后,田瑛这样写道:“……牛耐力著世,忍痛力也著世,其负痛方式是咬牙,当然也流泪,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