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世中的荒诞传奇
作者: 杨世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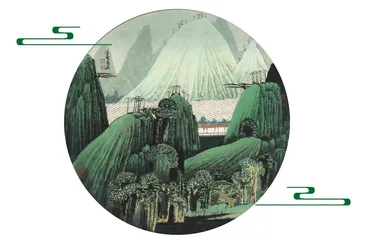
摘要:在《一日三秋》中,刘震云承接其幽默叙事风格,以笑话作为全书的表层主线,而笑话中隐藏的被迫、恐惧、不得已等感受则作为小说的暗线,同时作为幽默的反面,揭露环境的荒诞与非自主生活的悲剧性,表现小人物在大环境中自相矛盾的生活方式。在书写这一喜剧与悲剧同构的故事时,刘震云在情节、人物、结构等方面均有意识地向中国古代传奇靠拢,但其一以贯之的白描式叙述使得其在靠近传奇叙事的同时,用琐碎与重复等方式达到反传奇叙事的效果,构成了一部荒诞的民间传奇。
关键词:刘震云;《一日三秋》;悲剧;传奇
幽默是刘震云一以贯之的风格,在《一日三秋》中,他直接将笑话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试图写一本“笑书”。与《故乡天下黄花》《我叫刘跃进》等作品相似,《一日三秋》中的笑话没有停留在表面的包袱笑料上,从寻找笑话到讲述笑话,整个过程充满了反讽和悲剧意味。小说以笑话为叙述的主体,却时时映照着小人物身处的荒诞环境与其因不得已而成为悲剧的命运,与笑话本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参照之下营造
戏剧张力,使生活的无力感与命运的悲剧性更加浓厚。作为一位极具文体意识的作家,刘震云沿袭《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中的“喷空”式叙述,将奇幻情节与现实相糅合,完成文本的游戏与虚构。一方面,刘震云在叙述中回归中国传奇叙事传统,用虚构、省略和留白构造中国式魔幻氛围;另一方面,其典型的琐碎和絮叨的叙述,又拓展了传奇叙事所能承载的主题及内涵,使得叙述回归日常生活,构成反传奇的叙事效果。外表的喜剧与内核的悲剧相融合,跌宕的传奇叙事与琐碎的反传奇叙事交织,共同构建一部兼具哭与笑、俗世中的荒诞传奇。
一、悲剧意识:荒诞人生的不得已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鲁迅对悲剧与喜剧的定义形成对彼此的参照,无意中概括了《一日三秋》中悲喜交织的叙事安排和美学风格。当每个人都无法把控自己的命运,随机和偶然性占据了生活,事不遂愿,悲剧性随之而来。如果给悲剧内核套上一层喜剧外壳,以喜剧的形式叙述悲剧,以喜剧解释悲剧,沉重感和轻松感交织,悲喜交加的效果就得以实现。
《一日三秋》中故事的发生地仍未走出延津,这次刘震云赋予延津一个新属性,每个生活在延津的人都要在梦中接受花二娘的突袭,讲不出好笑话就面临杀身之祸。笑话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本是茶余饭后用来消遣的戏谑之道,在小说中却变成求生的手段。在延津生活的人成为笑话的奴隶,为博花二娘一笑去寻找笑话,其中又有不少人因讲不出笑话而葬身梦中。为保命而搜寻笑话,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死亡和欢笑这两个差势极大的概念被放置在同一天平上,形成强烈的荒谬感和讽刺感。《一日三秋》以这样荒谬又充满喜剧色彩的一幕作为小说的开头,作者无疑是在向读者施加某种压力,在这种充满压力的环境下,人物是不自由的,生命是不自主的。不妨跳到小说结尾处,在“精选的笑话和被忽略的笑话”一章中罗列着几条延津人搜寻的笑话,跳出故事,以当下的审美标准判断,这几条笑话并不十分好笑,甚至还没有寻找笑话的过程本身能令人发笑。利用反差手段构造矛盾的环境是喜剧常用的手法,如传统相声《白事会》中大肆夸张丧事的规模,却以没有坟地无法下葬为结尾,利用前后的反差造成荒诞的结果,前面一系列的铺张因结果而变得无意义,对无意义的事情进行夸张铺陈,自然是可笑的。当延津人为了不被花二娘压死而去寻找并不好笑的笑话时,其行动逻辑就具有戏剧性,众生为了笑话而挖空心思,却不知道在别人眼里,自己已经成了最大的笑话。书中列举的笑话都有一个相似的逻辑,即都以试图为不可为之事而引人发笑,其本质是螳臂当车与蚍蜉撼树,试图用微薄的力量改变或掌控命运,从而显得荒诞不经,在引人发笑的同时让人体会到个人在命运中的艰辛。在这些笑话中,可笑和可怜这两种情绪交织,构建了一个矛盾的生存环境。
对荒诞环境的表现是刘震云一以贯之的手法。有学者将《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称为刘震云的“存在主义三部曲”,而面对这个不可掌控的世界,人究竟能不能打破荒诞的魔咒,刘震云抱有怀疑的态度。[2]底层人物的微薄力量无法改变环境,并因此受到环境的限制和报复,这是西绪福斯式的神话,但与加缪理解的征服者形象不同,正如他对征服者的描述:“征服者知道行动本身是没有用的。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彻底改变人和大地。我永远也彻底改造不了人们。然而,必须做得‘仿佛如此’。因为斗争的道路使我遇见了肉体。肉体即便受到屈辱,它也是我唯一可靠的东西。我只能靠它来活着。”[3]加缪描述的征服者同样无法彻底改变人和大地,即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但与延津人不同的是,征服者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不因此而气馁。延津人对自己的行动并没有深度的认识,同样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滑稽的。戏中人是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的,作者在开头就用前言的形式告诉了我们。作者在前言中交代自己的写作缘起是六叔的画作,所有的人物都在六叔的画作中,这幅画作为艺术品具有观赏的价值,同时与现实世界相隔,画布就像一个舞台,画中人被困在画里,被外人观赏品鉴。作者在故事中告诉读者这是故事,坦白自己的创作是将六叔的画作拼接起来,其实就是通过一幅画还原一台戏剧,将画中人变成戏中人。延津人无法跳出作家构建的魔幻环境,从而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打量自身。从自身的生存环境中跳脱出来并上升到生活之外的高度,需要的条件是理性,拥有理性的人才能认识到行动的无意义,由此避免机械行动带来的滑稽和可笑。征服者反抗命运,清楚地认识绝望,明白自身行为的荒诞性,正因如此,荒诞拥有了庄严的意义,征服者也拥有了勇气,在没有前途的牺牲中实现伟大;延津人随命运漂浮,认识不到自身行为的荒诞,推动他们前进的是众神的责罚,而非加缪所说的意识到生命的无意义,正因如此,他们才在命运的推力下显得滑稽可笑。这就是平凡人物的生存困境,身处荒诞环境中时,既无力反抗,又无法对自我作清晰的判断和认知。宏大的悲剧在反抗和失败中令人感动,即鲁迅所说的对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而小人物的悲剧是琐碎的,当他们的自我以一种同样荒诞的途径被模糊时,甚至无法判断是喜剧还是悲剧,这就是小说结尾所说的“笑书”兼“哭书”,小人物的生活从台下搬到台上,变成一场表演,外人看来是滑稽可笑的喜剧,戏中人亲身体验的是无可奈何的悲剧。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刘震云,《一日三秋》,悲剧,传原版全文
《一日三秋》中的悲剧性还表现在具体的“不得已”上。有了小说开头建立的“契约”,主角在一个又一个推力下出场。樱桃死后,她的魂魄附在李延生身上,李延生无法正常生活,被迫借钱踏上武汉之旅;陈长杰在秦家英的压力之下,不敢光明正大地给明亮寄生活费,又被迫断掉了生活费。李延生迫于胡小凤的脸色,被迫同意明亮离开家;明亮夫妇不堪延津人的眼光,被迫离开延津前往西安,又因受到孙二货的排挤,被迫离开道北去往南郊。细究书中人物的行动逻辑,不难发现他们背后都有一股神秘的“推力”,人物并非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在各种压力之下,被迫地、不情愿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像文中那只中年猴子,体力不支无法表演,只得在卖艺人的鞭打下跳叫,戏中人都是卖艺人鞭子下的那只猴子,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威胁和逼迫下艰难前进。
这样的“推手”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屡见不鲜。在《我叫刘跃进》中,推力以巧合的方式出现,一个装着秘密的U盘让刘跃进被多方追寻,他被迫逃往河南,又被迫从火车上被带回北京。错综复杂的事件以一场车祸收尾,但推力并未消失——故事结尾处,瞿莉又找上了刘跃进,让他帮忙找另一张卡。这样的安排固然有文本影视化的趋向,但不难发现刘震云对这种推力的青睐。为什么要让人物都处在这样的推力之下呢?不妨对人物行动的推力做定性分析:刘跃进被吴老三追打,是因为刘跃进在色欲驱使下和其老婆调情;刘跃进被韩胜利追讨,是因为欠了他三千六百块钱;被多方势力寻找,是因为掌握了重要的秘密。总结下来,小说人物被迫卷入漩涡的原因,无非金钱、权力和欲望,这些因素被具体化,寄托在一系列的承载物上。这是一个将“自我”剥离和外化的过程,当自我被从具体的人身上抽离出来并以金钱、权力和欲望的形式展现时,人的异化就完成了。这也是有学者将小说概括为“寻找自己”的过程的原因,将人的价值寄托在外物上,失去了自主性,注定无法找到期盼中的价值。[4]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并非主动的,也不以认知自我或寻找人生意义为目的,而是被寄托在钱和权上的自我推动着,以巧合为契机,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走在寻找的路上。这样的安排构造了两重悲剧。第一重悲剧是自我的缺失,在资本介入的社会,什么事都可以用钱来解决,无论是伦理上的冒犯还是欲望的缺失,最后都能以钱的形式具象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物而非情为纽带。把严格和贾主任的关系改成严格救过贾主任的命,功能性效果并无变化,贾主任同样会感激严格,但主题却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人在资本席卷一切的时代俨然成为金钱的奴隶,作为人应具有的情感与感受被压抑和掩盖,主体性被物替代,这宛如卡夫卡《变形记》中人的异化,人的身份并不重要,主体意识和思想也不如生产力重要。第二重悲剧是追寻过程中的被迫,连失去主体意识后的追寻都是被推着向前行进,基于这样的被迫动因,所有陷入追寻过程的人物都显露出无力和弱小。无论是穷困潦倒的刘跃进,还是身家过亿的严格,或是大权在握的贾主任,他们的寻找过程充满恐惧,害怕被迫害、破产、事情败露,在另一个能够压迫和制裁自己的对象面前,所有的外壳都被揭开,露出弱小的颤抖着的卑微自我。这是刘震云揭示的第二重悲剧,每个人都是相对意义上的小人物,在更强大的力量面前只能不自愿地行动。
从《我叫刘跃进》到《一日三秋》,同样是被迫和不得已,也都是带有悲剧意味的人生,悲剧性却发生了转变,或者可以说,在后者中,悲剧性得到了缓释。通过对掌握着强大势力并以此对弱势方进行胁迫的一方的定性分析,可以看出作者是如何通过对不得已关系的处理来改变悲剧性内核的。李延生被樱桃附身,无奈前往武汉,两个人的对话却充满了温情,与刘跃进被冷漠地威胁甚至绑架不同,李延生和樱桃更像是互相帮忙的旧友,樱桃时而委屈,时而透露出不得已而为之的内疚,而李延生也回应以安慰和感慨,这种有温度的对话让本来在樱桃威胁下的旅程从胁迫的氛围中脱离出来,掺杂了李延生的自愿意味。在这种处理方式下,樱桃并不被定义成强大势力一方,反而透露出些许弱势,主动权转移至被胁迫的李延生手中。如此处理,一强一弱的关系界限被模糊化,地位被拉至同一水平线。其他上文举出的不得已的动因都是如此,胡小凤因陈长杰中断生活费而停止抚养明亮,却在明亮的婚礼上哭了;欺负明亮夫妇的孙二货跋扈嚣张,晚年因老年痴呆症生活无法自理,还将明亮认作最好的朋友;妓女香秀因10万元而陷害马小萌,最后因病毁容后自杀。在每个被迫的旅程背后,都有一个“始作俑者”,在《我叫刘跃进》中,这个始作俑者是强大且冷漠的,强弱双方地位差势明显;在《一日三秋》中,胁迫方和被迫方都因各自的难言之隐变得弱势,双方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势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不得已的悲剧意味,当推力的强制性被削弱后,悲剧意味也随之下降。
如上文所说,刘跃进和严格等人被迫卷入漩涡的原因是金钱、权力和欲望,而在《一日三秋》中,这个原因变成了人情,对亲情、友情或是爱情的重视代替了前者中推动人物行动的物,换言之,人物追寻的并不是寄托在物上的自我,而是追寻作为自我的一部分的诸多情感。李延生带着樱桃南下,又收留回到延津的明亮,六岁的明亮独自乞讨走回延津,推动他们走完这些路途的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善意和温情。
由此,前者中构建的两重悲剧(追寻路上的被迫和自我的缺失)分别被削弱,当外在的物被替换成内在的情感时,无论是被迫南下还是离开延津,追寻者都不再是错误地寄放了自我,相反,对情感的追寻更像是对自我的构建。放弃情感转向物造成自我的缺失,放弃物转向情感则构成自我的补全。从《我叫刘跃进》到《一日三秋》,资本的重要位置逐渐挪移,让位给从前被忽视的温情,在后者中,钱权交易被约定和承诺取代,对存在的拷问变成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叙述也完成从外在到内心的转向。
二、叙述的回归:传奇与反传奇
唐宋以来,“传奇”一词多被用于指称某种文体,随着时代变化,实际内涵也有不同,有被称为唐代传奇的唐代文人的文言小说,有宋元以来的篇幅较短的白话小说和明清时期的长篇戏剧体裁,或被用来指称元杂剧。但在看似随意、宽泛的使用情况下,“也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不同于史家客观载录史事的一些特征,如游戏、虚构、新奇、离奇或奇幻之类”[5]。故事内容上的惊奇、叙事方式上的奇异和人物塑造上的传奇,共同构成中国传奇叙事传统的特点。作为重要的古典小说叙事资源之一,无论是本来就以“寻根”为目的的寻根文学[6],还是以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为特点的先锋小说[7],都对传奇叙事有不同程度的借鉴。就《一日三秋》而言,与其将其中魔幻的内容归为魔幻现实主义,不如转换视角,分析其中对传奇叙事的传承与借鉴。与此同时,与传统的传奇故事相比,小说亦有“反传奇”的一面,下面分别从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和叙事方法等三个方面对其仿传奇和反传奇的特点进行分析。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刘震云,《一日三秋》,悲剧,传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