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君子为能知乐:《乐记》的乐教传统及其当代性
作者: 杨柳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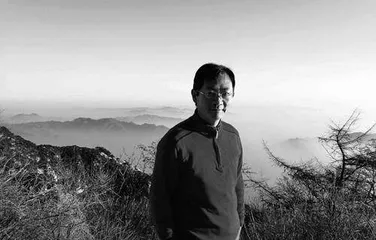
我们今天选讲《礼记》中的《乐记》篇,用的是王夫之的《礼记章句》注解本。为了忠实于原典,我们需要细致阅读《乐记》原文和王船山的注释。这种阅读体验对大家来说会有些特别,因为这意味着要进入一种“经学”的传统。
现代学术或多或少都强调要有一个理性化、客观性或者科学性的视角。这个视角不可避免地会把人类所事所思中内蕴的德义给过滤掉;它认为德义对科学来讲是某种必须清除掉的“杂质”,或者说认为含有德义的观念和思想在科学上是不纯粹的。须知中国传统经学恰好反其道而行之:经学首要的目的正在于传达德义,在于“文以载道”,也就是以“文”来传承和弘扬伦理和道德上的价值。当然,这里的“文”作为“人文”,不仅仅是见诸语言文字的,还包括人类“经天纬地”的一切创制。经学并不是只有德义而已,而是首重德义,它其实也观照到德义之外的其他丰富内容及其意义。经学对事物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也并非没有要求,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华文明重视“史”的传统之中。中华民族是最具有历史自觉和历史经验的民族;中华文明是最擅长记载历史和拥有最可靠最悠久的历史记录的文明。经学并没有把德义与科学性客观性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如果说今天的现代学术过分地求“真”的话,以至于它似乎“真”到了容不下“美”和“善”的地步!而经学是以“善”为宗纲的“真善美”的统一。我们今天无论是读全部中华文化核心经典,还是读《乐记》这个篇章,一定要具有经学的眼光,要带着经学的趣味去读。这样的话,就可以跟所谓现代哲学、现代美学,以及现代艺术史之类的眼光和趣味区别开来。
一
王船山先生在为《乐记》所做的序言中说:“乐之为教,先王以为教国子之本业,学者自十三以上莫不习焉。盖以移易性情而鼓舞以迁于善者,其效最捷,而驯至大成,亦不能舍是而别有化成之妙也。推而用之,则燕飨、祭祀、饮射、军旅、人神、文武,咸受治焉,是其为用亦大矣。周之衰也。郑、卫之音始作,以乱雅乐。沿及暴秦,焚弃先王之典章,乐文沦替,习传浸失。汉兴,雅、郑互登,莫能饬定,而六代之遗传,仅讬于学士大夫之论说。”
这段话揭示了古圣先王乐教传统历史演变的大体脉络。“乐之为教,先王以为教国子之本业”。“国子”指的是王、卿大夫、诸侯等贵族的子弟。“学者自十三以上莫不习焉”,从少年开始,古代贵族子弟就要学乐德、乐语、乐舞等和“乐”相关的道理和艺能。
我们看到“乐”这个字,或多或少会带着今天的“音乐”概念去理解它。要知道这个“音乐”的概念太狭隘了,在《乐记》里所谈的“乐”不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狭义的音乐,实际上它还包括“诗”和“礼”(含仪和舞),是一个更广义的,寓“诗”“礼”于“乐”的概念。在中华文明传统中,诗、礼、乐是一个三维一体的整体,是整个礼乐教化制度在“艺”能上的体现。孔夫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孔子看来,诗、礼、乐三者的文化功能,在人的德行养成中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三者中,乐的特点是“盖以移易性情而鼓舞以迁于善者,其效最捷,而驯至大成,亦不能舍是而别有化成之妙也”。人的性情受乐的影响最为敏感,故而说乐移易性情其效最捷。而德行大体的养成,是以具备乐的“和谐”精神为美的。
“推而用之,则燕飨、祭祀、饮射、军旅、人神、文武,咸受治焉”。这是说在整个吉、凶、军、宾、嘉五礼体系中,都有乐的参与。以诗礼乐养成德行,本来是先王的传统。在周代之前,这个乐的传统,或者说诗礼乐一体的传统,为国之大事,既是教化之大事,也是政治之大事。这个传统是很悠久的,可以追溯到尧、舜、禹的时代。延续到周代,这个传统就达到了某种集大成乃至鼎盛的状态。而到了周代的末期,“礼坏乐崩”,这个乐的传统也就衰败了。“周之衰也。郑、卫之音始作,以乱雅乐。”于是,各种靡靡之音泛滥。更往后,到秦朝的时候,“焚弃先王之典章,乐文沦替,习传浸失”。乐的败坏就更厉害了。而汉朝兴起之后,“雅、郑互登,莫能饬定”。汉朝兴起,当然要制礼作乐。那个时候,前代的雅乐或许还能够找到一些,然而雅乐已然不纯,因为郑、卫之音实际上也掺杂进来。所以,汉初的这个“乐”事实上是比较杂乱的。“而六代之遗传,仅讬于学士大夫之论说。”从尧、舜、禹一直到夏、商、周这六代,这整个乐的传统的制度及其精义,到汉代的时候,只在学士大夫的论说之中还有一些留存。
船山的这段话很值得重视。他告诉我们《乐记》篇的珍贵性,因为它是包含六代乐教精义的仅存的文本。我们知道,儒学有“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一般说来,人们认为《乐经》是失传了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礼记》中的这篇《乐记》,视为《乐经》的文本。
然而,船山也提醒我们《乐记》这个文本传说驳杂,尤其要注意荀子有悖圣人之旨的观点混杂其中,我们要辩证地看待。
此外,我们知道,中华传统有“华夷之辨”。“雅郑”与“华夷”是相关的,其实质都是关乎文明与野蛮的区别。“郑卫之音”实际上是被“中国”视为“夷狄”的,因为它们用靡靡之音来扰乱雅乐。船山认为,在宋代以后,又有胡人部落的音乐对原有中华音乐和乐教的浸染与颠覆。
二
《乐记》开篇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记》)
这个部分讲了声、音、乐三个概念。船山对声、音、乐有精细的分疏:声,“心有合离攻取,因事物之同异从违而喜怒哀乐征见于声响,凡口之所言,气之所吹,手之所考击之节,皆其自然之发也”。音,“宫、商、角、徵、羽之相应合者也。”乐,“声动而形随,形动而所执之器毕肖其容,声容合而乐备矣。”简而言之,声出于自然动发;合乎律吕而为音;组织缀合众音,有时伴以诗、舞而成乐。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这句话倒没有大的问题。船山特别指出,这一段原文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出现在第二句:“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船山认为,圣人并没有把人心看作是寂然不动的,人心本有一股活泼的生机。它是活泼泼地在那里,并没有寂然不动。那么它什么时候表现出它的动?它怎样显现出它的这个似静而动的生动性和活泼性?它是与物相应、感而遂通的。当与物感通之际,人心中的这个内蕴之“动”就非常明白地彰显出来。如果没有事物与人心相感通的话,人心的动之“几”就处于一种隐微的、潜伏的状态,属于情的喜怒哀乐就不会显现出来。但是这个喜怒哀乐之情,是蕴含在人的心性里面的,它天机固有,因物随时而感通。只要与物相应,“情为性绪”,它就会显现;不相应的时候,它作为固有的活泼生机也不会完全沉寂。所以,心之本体并不是寂然不动的。心之本体一直是活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心之动,物使之然”,自然就错了。就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的内因和外因一样,物使心动,毕竟只是一个外因,外物并不能够完全使人心动,因为人心本来就没有寂然不动,而是内蕴活泼的生机,或动之“几”。而佛、老两家往往都以寂然不动为心之本体,所以它们也是错的。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嘽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乐记》)
这一段说乐是由音而来的,“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人的喜怒哀乐敬爱之情,表现于乐之音声,各有其微妙的差异。这里强调乐的根本,出于人心感物而动,还是接着前面“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说的。船山说:“感于物”,谓喜怒哀乐爱敬之心皆因物而起。关于“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船山指出:“记者之意,以寂然不动者为性。六者,情也,则直斥为‘非性’矣。”船山接着说:“喜怒哀乐之发,情也。情者,性之绪也。以喜怒哀乐为性,固不可矣,而直斥之为非性,则情与性判然为二,将必矫情而后能复性,而道为逆情之物以强天下,而非其固欲者矣。若夫爱敬之感发,则仁义之实显诸情而不昧者,乃以为非性,是与告子‘杞柳杯棬’之义同,而释氏所谓‘本来无一物’,‘缘起无生者’正谓此矣。”
人道乃依性情之本然而立,心统性情,情为性绪。心性中本有仁义礼智之性德。《孟子》从人心内含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见人实有仁义礼智之性。而《中庸》以“诚”言“天命之性”与“天之道”。朱熹注“天命之谓性”,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乾健而坤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健顺五常乃人性中实有天赋之德。《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朱熹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船山曰:“‘未发’奚以遂谓之性?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未发者喜怒哀乐耳。”可见,情为性绪,性情本不隔,不可说喜怒哀乐之情即为性,亦不可说情非性。人道无非顺人性情之自然而立,故《中庸》曰“率性之谓道”。因此,船山指出,言“六者非性”,则将情与性判然为二,必导致矫情而复性,道为逆情之物而强天下,而非本人性之自然以为道。
尽管在辨析性情与音声的关系问题上,毫厘不让,但是,船山先生也充分肯定了《乐记》这个段落的精彩之笔。他说:“此章言先王制乐之意,推之礼与刑政而皆协于一,其论韪矣!”船山对细微之处,分辨之谨严,真是令人钦服。他转而指出:“至云‘先王慎所以感之者’,而礼乐刑政以起,则又与荀子之言相似。盖作此记者,徒知乐之为用,以正人心于已邪,而不知乐之为体,本人心之正而无邪者利导而节宣之,则亦循末而昧其本矣。”若人心已入邪僻之径,再用乐去校正它,则强调的只是乐之用,“而不知乐之为体,本人心之正而无邪者利导而节宣之”。那么,乐之体是什么呢?就是人心之正而无邪的那个本然天性。这个天性自然发出来的音声,有所节宣就是乐。
三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
船山说:“音由人心而生,而逮其声之已出,则入耳警心,而心还因以生,邪者益邪,正者益正,而治乱分矣。”又说“‘声’,质也。‘音’,文也。文因质生,而文还立质也。安乐之感,情平而事得其序,政益和矣。怨怒之感,情激而上下相戾,政益乖矣。哀思之感,情疲而偷,民益困矣。音由世之治乱而异,而还感人心,复生治乱。”
这里的音和声,实际上都是乐的代称。“情动于中,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船山把声和音解释成质和文的关系,但声和音实际上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的,因为音本来是由声构成的。当然,音已经具有了对声的文饰,乐由音所构成,音也可以指代乐。文中所谓“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就是指乱世之乐、亡国之乐。
声音与人心之间存在相互生发的关系。“音由人心而生”。声音之所以产生出来,实际上有内在的性情上的根据,再加之与物感通,人就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声音。“而逮其声之已出,则入耳警心,而心还因以生。”声音一旦发出来之后,人心是会受到这个声音影响的,就会发生相互影响。声音或出于邪僻之性情,或出于中正之性情,那么,它们对人心的影响就会使“邪者益邪,正者益正”,从而形成政治与民风之治乱的差别。这就是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
音乐是人的性情的外显,又是政治的象征。同时,音乐也能影响性情和政治。音乐在两个层面与人相互影响:一是在个体的人心性情层面,一是在共同体的政治伦理层面。这两个层面是相互贯通的。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乐记》)
从传统政治与乐的关联上讲,宫商角徵羽对应地象征着君臣民事物。这看起来有些玄妙,其实,进一步往内看,就能发现音乐与人的心性相互关联的这一层。文中对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描述,强调的是五音之乱与国之衰亡及人心性情的败坏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前面这几章,讲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音乐与人的性情和国家兴衰治乱之间的关系。
当下一般人对音乐的看法,往往以为音乐无非是一个好玩的东西,似乎此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种看法,如果与中华传统的观点相对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古圣先贤对音乐的理解跟今天人们的一般看法太不一样了。在古圣先贤看来,并不是什么音声都可以称之为真正的乐的,不是什么曲调都可以随便演唱或演奏的。因为“声音之道”关乎国家的治乱兴亡,关乎人性情的正邪,这在中华传统看来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一个可谓“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