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离到融合: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关系
作者: 王琳博 兰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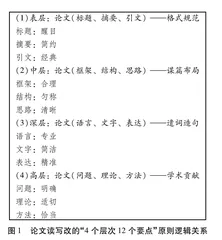
[摘 要]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研究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两者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常使学术共同体成员不断质疑教育理论研究的价值以及教育实践如何指导教育理论发展的系列问题。研究发现,两者关系经常处在“分离”与“融合”的徘徊状态中。两者关系处于分离之态的影响因素有教育理论的抽象性、教师群体的非专业化、学科专业的差异化、评价机制的数据化。为了实现两者关系从分离走向融合,我们可以开展教育理论的“元研究”、重视教师群体的专业训练、培育学术研究的文化氛围和重构考评机制的制度建设。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2)02-0001-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2.02.001
时至今日,重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关系”这个教育学领域中最基本的问题,仿佛与当下的教育研究前沿问题(如核心素养、人工智能、大数据、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乡村振兴与教育扶贫等教育热点)渐行渐远。然而,笔者认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和知识经济时代重申此问题,意义有二:一是从人才培养质量来说,对于新迈入教育研究之门的新人(主要是研究生群体),有利于增强教育研究者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认同,并为未来的教育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论指导;二是从知识价值来讲,对于两者长久以来“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会有一个更全面和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扫除研究者(特别是初入学术之门的“新手”)在认知层面上的“模糊”与“混沌”的感觉。
一、不同学科视角下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表现形态
通过选用“教育理论”“教育思辨研究”“教育实践”“教育实证研究”“教育研究”等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和分析,我们发现,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研究表现出3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关系分离说”;二是“关系融合说”;三是“关系中介说”。
(一)关系分离说
1.从教育社会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进行了研究。闫旭蕾认为,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看,造成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阻隔的原因主要有:由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认识引起的阻隔;由教育理论叙述方式、思维方式引起的阻隔;由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所处场域引起的阻隔[1]。王海英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如何理解“教育理论脱离实践”等问题。在“教育理论脱离实践”的背后隐藏了这样几个问题,即实践的先在性、理论的他功能、利益群体的边界捍卫情结以及理论在转化为实践过程中的延迟效应[2]。方建锋立足于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探讨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应然关系,从研究者和研究方法两个维度分析了导致教育理论脱离实践的原因。教育理论的目的在于培养实践智慧,教育理论不是“应用科学”,而是人文科学或道德科学的特例[3]。
2.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进行了研究。罗祖兵认为,后现代主义思维范式为理解和解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多元的视角。后现代主义认为,教育理论不具有唯一性,教育实践不具有自在的客观性,教育研究没有固定的方法。后现代视域中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4]。
3.从教育实践逻辑的视角进行了研究。李润洲认为,从“实践逻辑”的视角审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就会发现教育理论与实践间的隔阂、脱离是双向的,有一定的必然性。教育理论与实践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也是教育理论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5]。
(二)关系融合说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除了存在“分离”之态,也有“相互融合”的和谐画面。有学者从实践哲学的视角研究了两者相互统一的关系。李长伟认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所以分裂,是由于近代以来科学对实践哲学的僭越。在实践哲学视野中,理论和实践、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是不分的。只有重新重视实践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才能复归统一[6]。宁虹等人认为,在实践哲学视野下,理论不再被概念所固化为抽象的认识,理论总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实现自身。教育理论可以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它并不与教育实践相对立,而是具有不可分割的本然联系[7]。其他学者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教育实践的特性和新基础教育研究实验的视角分析了两者存在统一的关系。彭泽平认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构成的是一种内在的、间接的、反思性、批判性的关系,而不是同一的、对应的、直接的线性关系[8]。徐继存认为,教育实践需要教育经验和常识,但仅仅停留在教育经验和常识的层次上是远远不够的,教育理论需要沟通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既把握教育实践的方向,又寻求前进的最佳途径[9]。吴黛舒认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脱离”是一个实际问题。“新基础教育”研究认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不是简单的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滋养”的新型关系[10]。
(三)关系中介说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除了存在相互“分离”和“融合”的状态,还存在一种中介情况。这些“中介说”主要有中介研究、教育中介、行动研究、教育思维、教育理念、课堂研究等。毛祖桓认为,如果说教育理论研究的功能偏重于“求真”的话,那么,中介研究的功能则更偏重于“行”的方面。中介研究的长处恰恰有利于填补从教育理论到教育实践二者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11]。张应强认为,教育中介主要存在于实践特性占主导地位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教育中介主要有教育中介思维、教育中间理论和教育中介机构,三种教育中介的完善是解决教育理论与实践紧张关系的基础[12]。宋秋前认为,行动研究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能动的实践性中介。以教师为主体的行动研究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既有教师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的批判,又有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问诊和反思[13]。鞠玉翠认为,行动研究就是为了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端。实践主体与研究主体的沟通是在实践和研究的过程中实现的,行动主体与研究主体合一的自然结果就是行动过程与研究过程的合一[14]。刘庆昌认为,教育思维是人类的教育实践理性,是教育理论认识在教育实践面前的凝结,也是教育实践经验在人们认识中的凝结;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定的教育观及其支配下的教育操作思路的统一体。基于教育思维特殊的内涵和鲜明的思想色彩,它可以充当教育理论走向教育实践的认识性中介[15]。李震峰认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离主要是因为没有严格区分教育理论与教育理念,教育理念具有超前性、有限理性和整体性[16]。王鉴认为,课堂研究作为教育研究的中观层次,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结合的最佳纽带。课堂研究的多重价值在于实现教育理论创新、推动教育实践变革、促进教育研究者的专业发展等[17]。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处于“分离”状态的影响因素
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达到“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境界。但是,实践中所谓的“教育理论”却没有有效地指导教育实践,至少在教师作为研究者的学术共同体中的教师群体并没有对“教育理论”形成极高的认同感。“在我看来,理论就是所谓的专家故弄玄虚的那一套,泛泛而谈,脱离教育实际,对我们工作改进没有实质性的帮助。”[18]在现代社会,以教育学术研究为业的教育学人必须弥合教育理论与实践互不沟通、各自为政的“断裂”,不仅仅要做一个勤勉的“研究者”,不断创造有价值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还应当是教育理论成果、教育科学知识的“解释者”与“传播者”,关注教育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对全社会教育观念的引领,提升全社会的教育智识,引导广大一线的教育实践工作者创造性地开展教育工作[19]。
(一)教育理论的抽象性
既然被称为教育理论,那么它就是对现实中教育现象背后规律的抽象化认识、归纳和总结,是不太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如果教育实践者本身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技术和比较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就不太容易理解、接受和认同教育理论研究者们所提出或建构的教育理论。这样的状态就容易造成教育理论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两大行为主体之间难以形成观点一致的情景。在现实生活中,教育经验与教育理论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我们很难将教育经验与教育理论比较清楚地分开和辨识,即使是教育研究者,他们也难以准确地辨识哪些应该属于教育经验,哪些又是基于教育经验基础之上的教育理论。因为经验因人而异,社会背景与文化知识不同的公民对经验都有各自的解读,都深深地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烙印。而教育理论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它是在丰富的教育实践之上而形成的,已经经过了一定时空领域中教育实践的检验。教育理论研究主要是由思辨形式进行,而教育思辨研究经常受到批评与指责。正如有学者所言,“当代教育思辨研究主要受到问题虚空、论证主观和观点晦涩的批评”[20]。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教育理论中总是少了些许“实证”的元素。同时,反观国外的教育理论,它们往往扎根于丰富的教育实践中,西方教育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本身就是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历者,正因为这样的经历才使得他们的理论享誉全球。如拉尔夫·泰勒出版了《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一书,该书后来成为世界教育名著,泰勒本人也被誉为“课程评价理论之父”。他的这本代表着教育理论与思想的经典名著是建立在他“八年研究”基础之上的。同理,卡尔·雅斯贝尔斯、罗素、杜威、苏霍姆林斯基等享誉世界的教育名家都有过不同程度自己办学创校的经历。如杜威于1896年创立一所实验中学作为他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并任该校校长;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任教,担任这所农村中学的校长、教师和教育者长达32年。他们的扛鼎之作也是承载他们教育理论思想的有形载体。与国外的教育学家相比,我们在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学习的同时,恐怕在探索教育实践的中国道路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们还需要从中国教育实践变革的历史中学习更多成功的教育经验。如民国时期的教育学家非常重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融合,像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验、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院的办学实践,还有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合川草街镇创办的行知学校等。
(二)教师群体的非专业化
教师群体的非专业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知识、技术和学术训练不够系统和精深;二是在教育研究中缺乏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这也成为影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处于“分离”状态的因素。在现有的教师群体中,老教师存在学历层级较低,理论素养欠佳,实践经验丰富的特点,而从国内外名牌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则存在学历层级较高,理论积淀丰厚,实践经验欠佳的特点,他们几乎没有在中小学教育领域工作的经历或体验,相应地也就缺乏比较丰富的中小学教学、管理与科研的经验。如果没有扎根中小学教育场域之中,没有对中小学课堂进行过深入细致而持久的观察,没有走进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内心丰富而又细腻的情感世界,没有对中小学课堂教学与研究有自己切身的体会,没有采用新的教育模式进行教育实验,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所做出的教育理论研究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指导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呢?这个问题恐怕还值得商榷。“在没有理解与消化的前提下,援引大量的理论学说与各方观点,使得整篇文章成了一个文献资料的大拼盘。”[21]事实上,教育理论研究者在进行某个主题或领域研究时,还是基于各种文献的阅读、思考、反问、比较、记忆、联想等复杂的思维活动之后,用自己特有的表达方式与思维习惯将我们对某个主题、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的见解呈现出来供同仁批评与指正。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会让人觉得教育理论研究是从一些故纸堆里寻找一些与现实问题有关的答案,有些“我注六经”的状态,从文献到文献,最后形成具有个体思维色彩与话语体系的文章。
(三)学科专业的差异化
在学科大家族中,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比,教育学学科的专业性不够强,入门门槛较低,属于“弱学科”。教育学学科所培养的人才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与医学、农学、工学等学科相比,如果医学在某个领域发明了新的治疗技术或药物,那么医学最新科研成果可以马上投入到临床之中,并且做到药到病除,救死扶伤;而教育学学科的科研成就不会像医学等学科那样可以立竿见影,因为教育学学科研究所面临的对象是具有丰富内在精神气质的独立个体。同时,学术界还对教育学学科属性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教育学是不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教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还是一门人文学科?教育学是一门综合学科?等等,这些关乎教育学学科属性的问题还一直没有定论。克里希那穆提曾直言:“教育不应该成为一种专家的职业。”[22]教育原本就不以专业性见长,其优势在于精神的丰富性[23]。即人人都可谈论和评价教育,而且非专业性的人所谈论的教育观点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在西南大学主办的刊物《教育学在线》中看到一篇题为“教育学研究生是豆腐渣”的帖子,标题本身便足以激起每位教育学人的愤怒。该帖的言论就有:考研大军中流行的口头禅是“考研究生上不了学,那就考教育学”。平心而论,文中所列理由大体属实:内容不多,好掌握;专业方向多,招得多;等等。在许多人眼中教育学的地位不高,价值不大[24]。正如钱钟书所言,“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学系学生,教育学系学生没有谁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25]。因为在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精神劳动,只要劳动或活动,人的行为就具有了教育性。教育理论研究属于人文社科类研究中的一种类型,它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可以按照实验法重复进行研究,而且通过实验研究完全可以对学科理论进行“证伪”或“证实”,从而去判断是接受该理论还是排斥该理论。教育理论研究面临的研究对象是形形色色的人,而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命体,人是每时每刻都在生长、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那些内隐在人心理上的密码与活动是无法重复性进行研究的。因此,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会因为学科自身的差异影响其传播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