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自由和那个世纪被遗忘者的代言人”
作者: 陈淑婷瑞典文学院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公报中,称赞安妮·埃尔诺“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称她“用简单、干净的语言进行书写,描述了羞耻、羞辱、嫉妒,其行为令人钦佩”。法国总统马克龙表达了对埃尔诺的祝贺,赞誉她是“女性自由和那个世纪被遗忘者的代言人”,“50年来一直在书写一部关于国家集体和亲密记忆的小说”,并恭喜她“通过这次加冕典礼进入法国文学界的诺贝尔奖大圈”。
埃尔诺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解释说,“这个消息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头脑一片空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相信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我想到了父母、家人,感觉在他们眼中自己也许已经做到了最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但同时也赋予她“巨大的责任”,因为“文学不是中立的,从来都不是,只谈论精美的书籍、美丽的文字,是一种掩盖文学力量的行为;而我的写作始终触及现实的东西,无论是关乎女性的现实还是社会的现实”。
安妮·埃尔诺的获奖也许让人感到有点意外,但只要了解她将近50年的文学生涯,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埃尔诺1940年9月出生于诺曼底的小镇利勒博纳市。她上面有一个姐姐,但年仅6岁就因白喉病逝,她的作品《另一个女孩》就是关于这个姐姐的。姐姐离开后,父母才决定再要一个孩子,因为他们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只要一个孩子,尽可能让孩子过得幸福舒适。1945年,因为埃尔诺无法适应当地气候,她的父母决定搬家到伊沃托,并开始经营一家杂货店。虽然父母经济能力有限,但依旧把她送到私立天主教学校,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埃尔诺也并未让他们失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其在文学方面。学校里同学们的社会阶层普遍高于埃尔诺,这让她初次体会到阶层等级的存在。1958年,18岁的她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到奥恩省的一个夏令营工作,也正是在那里,她不仅体验了集体生活,还和领队辅导员有了肌肤之亲,她后来在《一个女孩的记忆》中讲述了这段经历。1959年,她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鲁昂小学教师师范学校,然而入学后她发现这里的学习生活并不是她喜欢的,于是她果断放弃。1960年她去伦敦做了一段时间的互惠生,同年9月进入鲁昂大学学习文学,之后还曾就读于波尔多大学。在大学时期,她开始尝试写作,毕业后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学和中学教师。她24岁结婚,丈夫出身中产阶级,两人婚后育有两个男孩儿。1977年,她与家人搬到巴黎地区,在远程教育中心任教。1980年她与丈夫离婚后,便一直住在法兰西岛大区的塞尔吉市,至今仍然住在那里。后来她罹患乳腺癌,在2005年出版的《照片的使用》一书中提及了这段经历。
埃尔诺的生活经历成为她创作的主要灵感来源。丰富的人生经历,独特的写作风格,细腻的切入视角,以及与社会学的紧密相连,都是她成功的要素。她的作品将个人经历与社会、历史相融合,主题涉及社会地位(《位置》《耻辱》)、婚姻(《冻僵了的女人》)、男女关系(《单纯的激情》《迷失》)、生活环境(《外部日记》《外面的生活》)、堕胎(《正发生》)、阿尔茨海默症、亲人离世(《一个女人》)等,所有这些构建了一部关于埃尔诺自己的“自我——社会——传记”的“文学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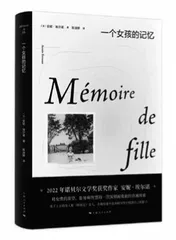
埃尔诺的首部作品《空衣橱》(1974)就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她在其中叙述了女孩丹妮丝·勒苏尔童年和青春的故事。小说开头呈现给读者一个痛苦而残忍的堕胎场景,接下来丹妮丝回顾过去:她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中长大,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经营着一家小杂货店,收入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丹妮丝的学习成绩优异,尤其是文学。学校里的同学大都来自较高社会阶层,这让她非常羡慕这些有背景的孩子,并开始对父母产生憎恨,尽管他们拼尽全力地供她读书。丹妮丝不断地在两个对立的环境中挣扎——一个是她的父母和村庄,另一个是她的学习和新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来越感受到她与父母教育背景的差异,与父母渐行渐远,这种分离是最让她焦虑的。整部小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
1980年代初的法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创作流派,许多作家开始采用一种新的自传式叙事形式,通过追溯祖先尤其是父母的存在,以期在现在和过去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还原祖先的形象,向他们致敬或对他们进行谴责,从而表达自己的遗憾、内疚、不满等;在此过程中,作者也能够追寻自己昔日的足迹、探索根源、理解自我、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等等。多米尼克·维亚将这种写作称为“亲子关系”写作,并指出了这种写作最主要的三个特征,即书写他人(父亲、母亲或某位祖先)、不同于传统自传的独特写作形式、叙述并非按照时间线性展开。
《位置》被学者们认为是“亲子关系”写作最早的代表作品,安妮·埃尔诺自然成为其重要的代表作家。小说巧妙地把个人回忆、自我审视和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融合在一起,寻找早已渐行渐远的父亲形象;作者通过回忆,通过文字和照片,重构了父亲的形象;同时也是对一个社会阶层致敬——当主人公进入资产阶级世界后,便有了自己新的身份,她长大的这个社会阶层早已被抛诸脑后。埃尔诺的母亲去世后,她重复类似书写,写下了《一个女人》。如果写作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礼物,那么《一个女人》至少有三层含义:首先,它是作者送给自己的礼物,帮助她走出哀伤;其次,它也是送给读者的一份礼物,通过对亲子关系的分享,让读者联想到自己的状况;最后,这是送给母亲的礼物,从一种倒置的亲子关系角度让母亲“复活”,此时的女儿成为母亲的母亲。
《我无法走出自己的暗夜》讲述了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故事素材源自埃尔诺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日记。主人公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自己的母亲,45岁的她此刻才觉得自己真正长大成人。《我无法走出自己的暗夜》和《一个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都是书写母亲之外,“我无法走出自己的暗夜”这句话出现在《一个女人》的故事讲述中——这其实是母亲在信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母亲的痛苦与无助。
继埃尔诺的首部小说《空衣橱》问世26年后,《正发生》再次涉及“堕胎”这个主题。小说讲述了女孩意识到自己怀孕后的一系列经历。基于女孩所处的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她被认为过度放纵,于是她想尽一切办法要摆脱掉肚子里的东西。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女主人公不得不面对这样几个困难:医生们由于担心丢掉工作,不愿意为她实施人工流产;她的家庭和社会阶层不接受非婚怀孕;社会禁忌迫使她不能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年轻女子迷茫而无助,她向父母和密友隐瞒了怀孕的事实,最后终于在巴黎的卡迪内街秘密堕胎。《正发生》曝光了一个被原则、禁忌和阶级偏见所吞噬的社会,无情揭露了现实的残酷可怖。
《悠悠岁月》讲述了主人公的大半生,从战后在诺曼底伊沃托小镇度过的童年一直到2000年代的生活。她的人生开始于一个简陋的环境,但她通过持之以恒的学习以及考取教职和写作,成功脱离了那种环境。1960年代的青春期,她体验了苦涩的爱情,之后又经历婚姻、分居、生育以及女权主义时代和经济危机。虽然属于私小说类型,但并未脱离社会和政治背景,将一个女人的生活放置于更大的生存环境中,同其他人的生活密切关联,构建了一个集体的存在,用以表明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人生经历,更是同样生活在“二战”时期的那一代人的生存写照。
《一个女孩的记忆》讲述了1958年夏天,一个18岁女孩在夏令营第一次与男人同床共枕的故事。男人主动接近她,然后又抛弃了她,让她独自忍受周遭人的责难。尽管如此女孩仍旧不死心,离别后依然希望找回男人,为此决定让自己变得优秀……最后,脱胎换骨的女孩已然对男人没有了留恋。作品中写道:“我也想忘记那个女孩。真正的忘记,就是不再想书写她,不再认为必须书写她,叙说她的欲望与疯狂,愚蠢与骄傲,饥饿与停经。”“我不是在塑造一个虚构的角色,而是在解构曾经的那个女孩。”埃尔诺如是说。
40多年来,安妮·埃尔诺凭借创作实力逐渐确立了自己在法国文坛的地位。她的作品经常出现在中学、大学的课堂上,同时在英语世界和其他国家也得到了广泛关注。学界的研究重点由作品主题(包括社会阶层提升、性别问题、母女关系的复杂性等),到埃尔诺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再到作家的叙事语言和写作技巧等。进入21世纪以来,评论界对埃尔诺作品的研究角度又有了不小的变化,比如关注其童年和成长背景的重要性;从受布尔迪厄、波伏娃等人影响的社会学和女权主义视角研究其文本;从个人、社会和性的层面解读其自豪感与羞耻感之间的矛盾辩证关系,等等。2006年,埃尔诺的《照片的使用》一书出版,而2011年问世的合辑《书写人生》开篇也收录了100页的摄影日记,以家庭相册的形式把之前她未发表过的照片和日记分享给读者。自此,法国评论界的关注点又转向了埃尔诺的“写作与摄影”。其实,自《位置》开始,埃尔诺便经常在作品中穿插照片描述,而《照片的使用》则是首次在作品中放入其真实照片,从而引发人们思考文本与图像、摄影与传记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对于安妮·埃尔诺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探讨是广泛而多样的,这无疑凸显出其创作的深度、广度和厚重价值。
本文作者陈淑婷,天津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师、埃尔诺小说《一个女孩的记忆》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