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火焰》:雪地里的血与花
作者: 永舟
延期三年后,由双雪涛悬疑小说改编的电影《平原上的火焰》,终于在大银幕与观众见面。
在冰天雪地里讲述一个悬疑故事或一个爱情故事,都不难,难的是将二者结合,稍有不慎就会落入如《燃冬》那般缥缈、虚无的青春疼痛。《平原上的火焰》并未能完全规避这一点,血色与玫瑰的结合,极大依赖原著文本的意志。
2022年底,与小说同名的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开播,为“文艺悬疑”这一危险的组合博得了一席之地。平均一小时的单集长度,为铺陈时代情境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在九十年代末期东北工厂改制的大环境下,众生相因此鲜活。
相较之下,电影版进行了不少缩略与跳跃,这或许是电影的野心太大:既想讲好一个悬疑故事,又想映衬上世纪末东北工人阶层共同经历的伤痕,还想从中抽丝剥茧出两代人隐秘的内心痛楚和掣肘。但整体叙事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重心,而是雨露均沾,却在操作风格上保持了原著的含蓄。
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被编剧导演们看中,不是因为并不新鲜的悬疑元素本身,而是围绕两个主角庄树与李斐的血色浪漫,是弥漫在文本间的某种卡夫卡式的荒诞寓言。人与人之间暗流涌动的爱恨纠葛,不露声色的冷峻和凛冽,像东北平原上漫长无尽的寒冬,令人在畏怯的同时,也难以抵御凝视深渊的诱惑。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尽力去还原这种人物内在命运和性格差异摩擦出来的浪漫,却也因此放弃了一部分对悬案结构与社会脉络的探讨,让前半部分铺陈的肃杀,最终演变成半截青春疼痛文学。
时代悲剧
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以发生于90年代初沈阳一起贯穿八年的连环杀人案为原型,一犯罪团伙连续多次作案,专门杀害出租车司机。多年来,不安与恐惧弥漫在当地居民心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紧张,下一代人受到上一代人的影响,也因此卷入了漫漫冬季之中。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里,刘昊然饰演的男主角庄树,出场时还是吊儿郎当的混混少年,他原先对这起城际大案同样是不屑一顾的。
在他的世界里,有象征那个落魄年代最后活力的地下舞厅,有与朋友们在河里炸鱼的松弛,也有让人感到不耐烦的家庭—父亲偷偷行贿厂长,为自身前途作出阴暗的挣扎。母亲常年寡言、淡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以及与她一样奇怪的邻居女孩李斐。
这些奇异的、暗流涌动的人际关系,复杂之处并不在于表面的关系链条,而是个体内心深处各自不同的性情和欲望,是人与人之间微妙而克制的纠缠和关照。因此,若脱离原著去看电影,难免对个中奇妙感到茫然。
原著小说里化用了出自圣经《出埃及记》中的主角“摩西”作为重要意象,“摩西”在希伯来语中有“从水里拉起”的意思,寓意着某种救赎与信念。依上帝指示,有罪者需要在旷野中漂泊 40年,下一代才能进入光明幸福的应许之地。
在原文本中,这是对一代人命运的暗语。虽然电影改编时并无保留这份隐喻,但保留了那种建立在罪恶与救赎之上的悲剧性。事实上,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并非一个固定的人,而是一类人,或者说一种情绪、一种冲动、一种弥漫在那段时期工人群体间的普遍压抑。
李斐的父亲李守廉是连环杀人案的其中一个作案者,也是最后一个。他“偶然”杀死的司机,恰是那时假扮出租车司机查案的警察蒋不凡。蒋不凡死后,曾经与他有过交集且受其触动的庄树立志成为一名警察,八年后,他接过了蒋一凡遇害的悬案,并顺藤摸瓜找到了李斐的父亲。

两代人的命运因此纠缠交错。那场为了见庄树而发生的车祸让李斐遭受截肢,也从此丧失了年少时的梦想与企望。半条生命浑浑噩噩地活着,仅存的一点对爱情的幻想,也在庄树找到他们父女俩那一天,开始撞向毁灭。
原著故事里,两条并行的叙事重心,分别是宏观视角下外部环境的变动,以及一个主体少年启自内心的语言和目光。下一代并不直接参与上一代经历的变革,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父辈的影响,走向未知与无序。
命运的偶然性,是构成这宗贯穿多人的时代悲剧的重要支点。观众难免跟随剧中人多发问一句:如果平安夜那天,李斐没有搭上那辆出租车;如果出租车司机不是警察蒋一凡;如果她的父亲不是李守廉而是庄德增,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故土与女性
对故乡的复杂感情,是《平原上的火焰》里不可忽视的重要情感意象。
少年庄树显然对故乡是有感情的,虽然他自己也说不明白这份感情到底是依赖、留恋,或仅仅是一种熟悉感和惯性。他对渴望逃离的李斐不解地反问:“你为什么总想离开呢?这里不好吗?”

李斐没有回答他。她也很难用语言去解释,自己对逃离故乡的渴望来自何处。她用冰冷的眼神望向冰冷的平原和雪地,破落的城市和工厂,似乎一切自在不言中。
庄树虽然不能理解李斐,但庄树的母亲傅东心能。这两个来自不同世代的女性,都是那个环境里的“异类”。她们热爱文学与艺术,却找不到能容纳自己的地方。在重工业的世界里,她们是罕见而轻飘的一抹淡色。
在这个邻居的女儿身上,傅东心看见了当年那个被放下的自己。李斐和自己一样喜欢读书、画画,且拥有优异的学习天赋,有逃出平原奔赴大海的勇气和欲望。傅东心欣赏李斐,愿意无偿教她画画和阅读,甚至愿意拿钱资助李斐逃离东北,去更温暖的未来。
相比起庄树,李斐才更像她的孩子。
不一样的是,作为年长一代,傅东心顺从地接受了传统女性的命运—相亲,结婚生子,依附着老公找一个平淡无趣的工作,然后就这样过完一生。
相较之下,李斐当然是更勇敢的。她很确定自己要去更大的城市、更好的学校读书,下岗的父亲给不出学费,就自己努力考上免学费。她和父亲都舍不得傅东心,那就索性多买票邀请她一块儿走。在李斐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迂回和顾虑,她是一个敢爱、敢想,更敢去做的女孩。
只不过,在电影里,这股贯穿两代女性的敏锐和孤独感,被简化成了一些一闪而过的、交代匆忙的片段。傅东心得知李斐想要离开后,往后者书包里塞了一沓钱;周冬雨用文艺少女心动式的神态和口吻,祈望地劝庄树与自己一起到南方去。如果没有看过小说原文,其实并不能体会这些桥段的分量。
她口头说着不想待在这个地方,却没能具体表达出为何而不喜欢,唯一的线索,就是她优异的成绩,使这个正在走向破落的小城市不再“配得上”一个前途可观的中学生。
李斐和傅东心两个女性角色,很容易让人想起2023年的剧集《漫长的季节》里的三个女性角色,沈墨、殷红与黄丽茹。她们都同时被困在衰落的大环境与充满压迫感的小环境里,虽然各自的选择与际遇不同,却都最终通往不可逆的悲剧。
与上面三个人物比起来,《平原上的火焰》对女性的塑造要温和一些。尤其是傅东心,她从头至尾的含蓄、沉默,显示出对于时代命运的消极抵抗。
在由钢铁、命案和烈酒组成的世界里,女性角色往往是其中一抹令人揪心的亮色。又像去年的电视剧《我是刑警》里,杀人犯的妻子白玲勤恳朴实一生,却难以逃脱丈夫犯下的罪孽为自己与家庭带来的不可承受的打击。
个体的命运彼此嵌套,因此,时代齿轮的转动,碾压的绝不仅是单独一个有罪者。当曾经的辉煌黯淡,个体从停摆的列车坠落,不得不硬着头皮直面前方,直面眼前的茫然与未知。就像范伟在《漫长的季节》里呐喊的那样:“往前走,别回头。”
疼痛不“青春”
最后还是绕不开爱情。
电影最后一幕,也就是海报上最显眼的那幅图景—庄树与李斐彼此倚靠在车前,橘黄色的车灯似火焰,从两人身后向前照射。而将二人彼此衔接的,除了一对手铐,还有洒在对方身上的鲜红血液。
爱情的意味,在此刻得到直白的具象显影。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于,如果没有爱情,《平原上的火焰》并不特别,而又恰恰是因为爱情,它险些掉入如今电影类型的“食物链底端”—青春疼痛。
“青春”象征着生长和希望,是沉溺爱情幻想也不会被指责的特权阶段。“疼痛”则指代独属于那个青涩年代里对世界的错觉,以及因为难以掌控自身命运所致的困顿和无力感。在涉世未深的青春时代,这份无力感是可以被体谅甚至是被怜悯、呵护的。
只不过,它们不仅保质期十分有限,而且完全经不起现实视角的考验。如今对青春疼痛最大的诟病,在于其脱离现实的无病呻吟。既然都将故事搬到了东北这么不“青春”的画布上,爱情的形态,从理论上来说就很难再那么轻盈和明媚。被衰老、落败和肃杀笼罩的青春,得有些别的与现实更密切的关联凸显出来才行。
在《平原上的火焰》中庄树对李斐的爱情,从前期的懒得和她搭话,到中后期时不时突兀地想要强吻,来得如此粗俗、生猛,像极了围绕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子的刻板印象:不善言辞,喜欢用冷漠以及强迫来表达好感。
李斐看似更沉默内敛,但内心的火焰其实燃烧得更为旺盛。她会直接多买一张票,有把握劝服心上人跟随自己一起南下。也会直接邀请庄树到当时堪称禁区的粉屯玉米地里去放火。圣诞节前夜,一团熊熊烈火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燃烧,像炽烈的心脏跳动。这也许是李斐当时所想象到的,最浪漫的告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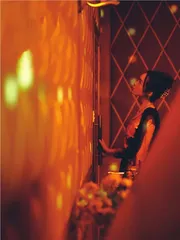
《平原上的火焰》的监制是刁亦男,这位拍出过另一部东北悬疑片《白日焰火》的导演,曾解释过为何选择东北作为悬疑故事的发生地:“因为此地的气候符合冰刀杀人的设计。”肃杀的雪原覆盖一切,枪声、呐喊,连血液的凝固都更快,死亡和罪恶在此地也就更加不露声色,更为残酷和彻骨。
对于犯罪题材如此,其实对于爱情也是一样的。天地太宽广,也太萧瑟了,这份荒凉的萧条会稀释爱情的浓度,倒逼人去反思一些更切肤的东西。如今,在某种现代主义的审美影响下,发生在东北的爱情故事,早已脱离早年间以喜庆、乐观与朴实为基准的“东北爱情故事”,而是演变成“失意中的诗意”。
《平原上的火焰》把这份诗意描绘得很美,呼啦着寒风的东北平原,干燥漫长的冬夜,点燃一撮火,烈焰照亮爱人的脸庞。这是电影里最具浪漫意境的画面。
火不仅代表少女李斐燃烧的心,也代表她对爱情的某种信仰。虽然正是因为这份信仰,她遭遇了改变命运的车祸,甚至可以说就是因为庄树而走向深渊。但八年前后,她仍然坚定地想要去赴约。经历这么多的李斐变得麻木、消极和厌世,但只有在望向爱情时,她的信念重新被燃起,她才变得坚定和勇敢。

已成残疾人的她在公车上为自己涂上口红,代表着年轻的浪漫的心在她心中仍有复苏余地,她依然为当年的心仪对象庄树保留着一份希冀和纯真。
有了这份余味,当观众在看完电影后大呼“不过是另一部《燃冬》”的时候,至少能为女主角留一份敬意和祈愿。过时的“青春疼痛”,疼痛的其实是现实,而不是青春。
既然宏大环境的变化如此难以抵挡,至少还有点爱情,还有点理想和纯真,可以帮我们抵御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