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班的年轻人,在“零工”中成长
作者: 祝越
去年底,柚子决定给自己找点自由的“体力活儿”。
她主动到社区群里发“自荐”,并如愿做了一天收纳工,还认识了一个保洁阿姨,商量以后一起接活儿。这一份零工,让柚子在一点点收拾房间的过程中,有了与过去的脑力工作不一样的获得感。
类似的现象,正在更多年轻人身上蔓延。
上学、毕业、找工作,似乎是每个人生活必经的轨道。而当轨道出错,生活陷入动荡的循环,刚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要如何选择?
“临时工”“零工”,这些属于“70后”“80后”的名词,在今天有了新的化身—“灵活就业”。不止是单纯地贩卖劳动力,当代年轻人,在信息时代,持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新“零工”。
近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了《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报告提到,新型灵活就业的供需规模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份额呈扩大趋势。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就已经达到2亿人左右。
统计数字背后,年轻人在多种“零工”里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有人因为无法接受低时薪,最终回到公司全职上班;有人学会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技能,也因此找回在职场被挫败的信心;还有人同时打着多份零工,遵循“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原则……
而不论未来如何选择,他们真正在寻找的,是一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对于自己来说,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
离开轨道的年轻人们
2017年,再次辞职的砂砂选择了离开一线城市,回到自己的老家—山西省的一个小县城。
这个选择背后是她在工作中积攒的痛苦。砂砂本科就读于中文系,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文案。2015年,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撰写各种测评稿件。工作不久,刚上班的热情劲儿过了,她开始经常性地拖延。领导要求每周五交稿,砂砂总是拖到周日的凌晨,然后熬一个通宵把稿子赶完。
“其实最后写出来是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印象了。”她熬过两三次通宵,感觉自己的脑子像浆糊,很难受。拖延状态也让砂砂陷入焦虑,后来,她每天早晨都起不了床,下班后一走出公司,就开始哭。
类似的焦虑、拖延与崩溃,也延续到她的第二份工作中。工作中的困难和压力时常让她情绪不稳,最后一次崩溃是因为失恋,第二天上班,她迟到了很久,“别人都找不着我”。在此之后,她不得已提出了辞职。
小一也经历了反复辞职。2019年毕业至今,她已经换过5份工作,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也不到一年,最短则只有两三个月。
她原本有一条看似通畅的轨道。在小一父亲的规划中,她大学要选择经济学专业,将来就可以去做会计工作。那时的小一还很懵懂,也没有太多的自主性,没怎么思考,就按照父亲的设想填了志愿。
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做电商客服,她常常发错货,即使为此赔了不少钱也没有改变。做审计工作时,她会反复检查很多次,仍然会犯很多低级错误。她也常常在工作中分心,白天的工作拖到晚上11点、12点才开始。到了深夜,如果遇上不懂的问题,小一不好意思去麻烦同事,拖延与焦虑叠加,她一边工作,一边扯自己的头发。
转行并不容易。既定轨道上的人要脱离轨道,找到新的方向,需要经历诸多波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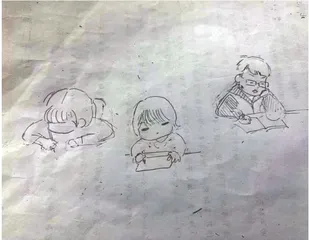
小一曾尝试去找工作不顺的原因。因为从小就粗心大意,也常常走神,她怀疑自己是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根据检查,她的情况似乎徘徊在ADHD的标准边缘,可吃过医生开的药也没有效果。父母则把工作问题归结于作息紊乱,试图让她早睡早起,可最终她也没做到。
2023年夏天,辞掉一份销售助理的工作之后,小一彻底回家躺平,靠自己的存款和父母的工资生活。
处在焦虑之中的砂砂,同样没有想到回老家以外的选择。多次情绪崩溃后,她觉得自己没法工作了。至于转行去干别的,她又感到恐惧,“做别的我也不会”。
待在家里,对工作的排斥和原生家庭本就存在的问题,让砂砂更容易崩溃。最极端的时候,砂砂会直接离家出走。有一次,父亲给她介绍了工作,砂砂嘴上答应,说自己要去面试。等到父亲走了,她出门坐上公交车,然后买高铁票去了北京。
生活似乎在原地打转。砂砂后来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但吃药治疗并没有让她明显好转。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不工作。2020年,砂砂又找到一份文案工作,给一个公众号写稿,内容是推荐女大学生穿搭。没做多长时间,疫情来了,居家办公的砂砂再次开始拖延,也再次因为拖延而痛苦离职。
她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愤怒。气愤之余,她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做过去那种文案工作了。
自由与可能性
脱离轨道后,打零工的日子给了年轻人更大的空间,让他们得到休息与滋养。
“我有点害怕被一个机构绑住。”受到这种想法的影响,2023年大学毕业后,柚子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零工或兼职。
与全职相反,零工生活往往与“自由”关联。打零工时,柚子只用对自己当下的工作负责,她尤其喜欢写稿、剪视频这类计件工作,“只需要做完那件事就可以”。小一的自由是骑着送外卖的电动车在大街上跑,有时候跑到深夜,街上没什么人,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声唱歌。砂砂则尝试了在电影院兼职,一次生病,她请了一个月的假,也不用担心被经理责怪。

自由带来的还有可能性,没有职场压力的他们,大脑变得轻松而活跃。柚子曾受朋友的邀请去景德镇布展。展摊的主题是“垃圾艺术家”,他们要负责垃圾分类,但会场里垃圾桶的数量很少。柚子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做一个“游动的垃圾桶”?这个想法很快落地:一个工作人员背着竹篓在会场里走动,逛展的游客既可以往竹篓里丢垃圾,还能跟工作人员互动,打卡完成捡垃圾的小任务。
类似的灵光一现还有很多。在展摊上,柚子根据自己过去对鲜切花的了解,给游客讲解一朵鲜切花生产背后,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活动结束后,大家一起回收用过的荧光棒,柚子感觉里面的灯带还能再次利用,就把它们拿出来,放进了旁边的玻璃瓶。玻璃瓶里的灯带闪闪发亮,好几个人被它吸引,把这些原本废弃的“垃圾”捡回了家。
充满可能性的“零工”生活,也让人们得以在其中探索自我。
砂砂的职业选择拓宽了。过去她对职业的想象局限于文案,而下决心不做文案之后,她尝试了书店店员,也进入电影院、麦当劳、汉堡王打工,还去当了一周的蛋糕店裱花学徒。
她逐渐意识到,比起坐在办公室写文案,自己更喜欢动手、跑外勤,做一些有即时反馈的工作。在电影院时,每天下班,她都能看到自己又检了一堆电影票;在麦当劳里,她逐渐成为打甜筒冰淇淋的熟手,顾客有什么需求她都能很快完成,“这些具体、细微的东西是最有趣的”。
然而,“零工”所开辟的广阔可能性,仍然会在现实面前受阻,这也催促着打工者们去思考未来的方向。
最大的阻碍自然是钱。小一跑外卖很快乐,但时薪很低,因为她不敢跑太快。平台规划的路线常常需要逆行,或者横穿马路,她也不敢,“两三块钱就能买我一条命”。砂砂最喜欢的电影院兼职,时薪只有11.8元,最多的一个月她也只拿了2000多。这意味着她只能住在家里,否则就无法养活自己。
“打零工”也少了晋升的可能。因为喜欢电影院的工作状态,她希望能长久地在这里待下去,成为全职员工,甚至再进一步成为值班经理。但她所在的电影院没有岗位空缺,如果要培养员工成为经理,也会优先年轻人,而那时砂砂已经接近30岁了。
砂砂意识到,如果留在老家的县城打零工,即使她可以自由地尝试多个不同行业,也只能一直待在最基础的岗位上,拿最低的工资。
这并非她所期望的。2023年下半年,砂砂给老家市区的13家电影院挨个打电话,确认了他们都没有值班经理空缺。然后,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启程前往上海,重新开始全职生活。
另一种眼光

打零工的日子告一段落,但这段经历给砂砂带去了新的眼光,她得以用更平和的心态对待工作。
曾经,工作中的困难总能轻易地击中她。“情绪来的时候,它就像下雨一样,一直在身上淋。”处理情绪总是会消耗砂砂的很多精力,但那时的她还没有应对方法。
打零工让她建立起了自信。她亲身体验到学习各种技能带来的快乐。在电影院做爆米花,起初她很害怕被锅烫到,也担心油会炸开。上手之后,她能熟练地按比例加入油、玉米、白糖,在掀锅时感受扑来的香气。不少小孩会站在旁边看她做爆米花,砂砂感觉,自己变得很“酷”。
写文案的时候,她常常感到惶恐,怕自己做不到、做不好,零工经历转变了她的想法。“干了这个之后就觉得我啥都会干,有什么不会的,学完就会了。”
这种心态,让刺激她情绪的东西变少了。砂砂变得更愿意和同事交流,也从他们身上学到自己不会的东西。她也逐渐学会应对自己的情绪,不再总是如临大敌,而是把它的到来看作感冒,意味着她需要躺一躺,把它养好。
在新的眼光之下,工作这件事本身也浮现出另一种意义。对现在的砂砂来说,去新的领域,就像是在游戏里点亮未知的地图,而工作就是积累经验值、不断升级。
柚子也有类似的感悟。“工作不完全(会)是舒服的体验,但人生有很多经历,不一定要是舒服的。”在那些不舒服的感受中,她反而会认识自己。除了赚钱,她也把工作看做是一种向外探索和自我成长的机会。

一次不成功的请假,就让她重新认识了自己。2024年年底,长期打零工的柚子想要体验全职的生活,于是入职了一家温泉酒店做宣传。后来她得到一个去日本旅行的机会,但领导没有批准她的假期。她特意开了一份文档,权衡工作和旅行两种选择……最后,柚子选择了保留全职工作。她对自己的变化感到惊讶,“有了一些更在意的东西”,放在过去,柚子可能会为了玩直接辞职。
不过,柚子依然喜欢同时打多份零工的状态。在她看来,这就像是把鸡蛋放在很多个篮子里,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如果我有很多份兼职,整体收入不比全职低多少的话,即使其中一个兼职没有了,还是比较稳定的状态。”而且,零工给她留下了更多探索外界的空间。
砂砂也在摸索自由职业的可能性。现在的全职工作相对清闲,她可以花时间去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争取能接到更多的广告。她也通过互联网和不同行业的人联络,想从他们那里了解自己未来职业的可能性。
零工生活的自由空间,依旧吸引着年轻人的回归。而无论选择怎样的工作形式,于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运转模式。
“可持续”是柚子在采访中常常提到的词。从大学开始,她就一直关心环保议题。对“可持续”的最初理解,大概要追溯到她5岁前生活的农村老家:老家的房子四周环山,视野开阔,空气也格外清新。靠近山顶的泉水很清澈,家里人出去干活时,都会直接从溪流里接水喝。
现在,她对“可持续”的理解延展开,不仅关乎环境,也关乎人的身心。那次充满自由发挥空间的布展经历,让柚子有了切身体会,“一定是我自己可持续,这件事(工作)才会更可持续”。
也许,人也应该像那座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