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歌》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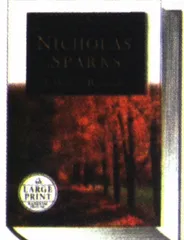
本期新书只有两部,而且都属惊险一类,倒使我们得以介绍上期的一部新作《素歌》。素歌一词原指基督教仪式中唱诗班的无伴奏齐唱。现在用作书名,显然是指书中所描述的纯朴恬淡的生活及作者肯特·哈鲁夫的朴实无华的叙事风格。的确,这部新小说以其简洁的语言和一句句对话,也以丹佛以东接近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交界处的科罗拉多高原的景色,使全书具备一种坦诚、精巧和可爱的旨趣,从而令读者爱不释手,心情难以平静。
《素歌》的天地是一座叫作霍尔特的小镇,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有带着两个男孩艾克和鲍比的父亲古思瑞;有被母亲逐出家门的怀孕少女维多利亚·卢比多;有接纳了她的未婚的麦克佛伦家的老兄弟俩哈罗德和雷蒙德;此外还有一个名叫玛吉·琼斯的妇女。这座小镇并非尽美尽善,不过,美也罢,丑也罢,一切都简单明了地摆在那里。
故事开篇时古思瑞的妻子埃拉正躺在客房中折腾,她莫名其妙地患上了一种精神反常症,已经有数周或数月之久了。维多利亚的母亲把女儿锁在门外,是出于对其外出的父亲的一种报复心理。与老父同住的玛吉·琼斯接待维多利亚住了几天,对她讲,她既然想把孩子生下来,就要去马丁医生那里检查。维多利亚想找个女医生,玛吉说这里没有。“你听我说,你现在这里,这儿就是你待的地方。”这句简单的话道出了霍尔特镇安身立命的原则,也就是《素歌》全书的基调,贯穿了所写的从初秋到翌春的全部时间。
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埃拉·古思瑞搬到了芝加哥街的一处租房,然后又迁到丹佛她姐妹家。玛吉·琼斯把维多利亚带到了镇东南的一处牧场,住进麦克佛伦兄弟的家中。年仅10岁的艾克和9岁的鲍比看着他们母亲离去,他们还目睹了小镇上所有芸芸众生的所作所为。古思瑞身为教师,发现自己搅进了一个满口谎话、为所欲为、恃强凌弱的学生的生活。一匹马不可思议地死于搅肠痧。一个男人坐在“急流”酒馆中告诉古思瑞:“我妈妈过去常对我说,只要你用心观察,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中都有教益。”不过他似乎在发表个人见解,而不是谈古思瑞的事。
就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从秋入冬,随后由冬转春。霍尔特镇逐渐露出了自身的风貌:有一片“较老的居民区”,随后是干街的三个街区和北面的地界,“那里的住宅较小,中间大多夹杂着空地;那里的住房都漆成蓝色、黄色或淡绿,在铁丝网拦着的后院里可能养着鸡,拴着狗,在低垂的桑树下美洲血根草丛中还会有旧车在锈蚀”。城中的每一处地方和周围的乡村在作者的笔下似乎都以其个性矗立着。
一支气候和光线的赋格曲响彻全书。当维多利亚从丹佛乘公共汽车归来时(她曾随使她怀孕的男孩一起去了那里),她放眼望着车外飞速退去的景色,感到“汽车行驶着,进入了霍尔特县地界,四下又是平展展的一片沙地了,孤零零的农舍旁的矮树,南北向的沙石路段就像儿童画本中的线条,筒形水渠边上是四股铁丝编成的网,铁丝网后面不时有奶牛和牛犊,或是一匹红色的母马和不满一岁的马驹,远处的南部地平线上露出蓝色的矮山。冬小麦是仅有的真正的绿色”。
维多利亚这个人物是作者的惊人之笔,用玛吉的话说,她终于醒悟到她自己身在何处了。后来是出于麦克佛伦兄弟的帮助,他俩和她一样坚韧温情,尽管开始时一想到十几岁的少女居然“满脑子都是你我想都想不到的念头”而惶惑。他们身上混杂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古朴风范,一种过时的谨小慎微和牧民们那种满不在乎的直率,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有时要把整只手臂伸进母牛的阴道中去摸怀着的牛犊。但他们对维多利亚的尊重似乎有一种毕恭毕敬的意味,而艾克和鲍比事实上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这种尊重和麦克佛伦兄弟俩往往可笑的固有的礼节,在他们走进维多利亚的医院待产病房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无声无息、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把帽子拿在手里,仿佛由于某种他们无法左右的缘故到迟了什么正式场合或宗教仪式。”
麦克佛伦兄弟俩无缘无故地便决定让维多利亚在他们家安居了。他们只是在把这个主意灌输给他们的玛吉返回镇上好久之后,在干着零活,从马槽上敲掉冰碴时商议了一会儿就决定了。当这兄弟俩最后面面相对时,“西方低矮的地平线上只剩下细细的一线紫色暮霭了”。哈罗德和雷蒙德都知道要做什么,不过还是哈罗德开了口:“真见鬼,瞧瞧我们这副样子吧。两个孤老头子,年老体衰的老光棍住在这离最近的镇子也有17英里的乡下,就算你进了那镇子,那儿又算得上他妈的什么。想想我们自己吧,脾气古怪又傻乎乎的。没人过问,一切全靠自己,倒是想干什就干什么。如今到了这把年纪,又能怎么改变呢?”
《素歌》的成功之处恰在于此。当小说急转直下,读者可能感到被作者紧紧抓住上衣前领时,你却觉察到了麦克佛伦兄弟的醒悟——他们虽不自明其原因,却清楚地想要改变——轻而易举地流进了你自己的醒悟,使你相信:果真在科罗拉多州有这样一座叫作霍尔特的小镇,事情一定会千真万确地如书中所写,懒散和宽容同时存在。裁决的大潮已经冲刷掉了那里的一切,只留下了一个事实上的天地,生命在那里诞生着,虚耗着。
总之,作者以独特的手法,用情景交融的笔触谱写了一曲自然与人默默生息、静静改变的“素歌”。
法国畅销小说排行榜
从警察到作家
艾立克·杨,52岁,1969年进警察局工作,1978年离开警察局进了监狱,1980年出狱当了记者,先后在《巴黎日报》、《新文学》和法国国内广播电台报道新闻,1999年11月出版自传性质的小说《黑暗的诱惑》,以其直面警界的真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事件是真实的,但是作者更换了时间和地点,主要人物温森特警官则是多个现实人物的糅合。他17岁结婚,早早做了父亲,开卡车,卖保险,21岁才找到警察的工作,起初他兢兢业业,挣钱攒钱,养家口,可他很快迷惑于他被要求去禁止的世界,犯罪团伙里到处是死亡,到处是爱情,生活就像吃了迷幻药的人在飞。终于在1976年他出了事,加上警察局上下各派的陷害,他被关了两年。出狱之后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黑暗的世界,可那个世界毕竟是他最亲切的,此后在各个新闻机构他做的一直是犯罪新闻,“似乎有什么神奇的东西悄悄钻进了他的大脑和血管,让他不得不这样做”。后来一位编辑朋友邀请他把当年经历写成书,这时他才发现岁月的分量,“我以为早就把过去消化得差不多了,实际上我仍然停留在咀嚼的阶段,”他说。
小说出版之后,同行们对艾立克·杨的成果褒贬不一,杨本人的评价是:“最真实的感觉还没写出来。”最真实的感觉,可能就是对黑暗世界的迷恋和恐惧,杨说即便在他当警察的时候,他也怕警察,怕警察必须面对的一切。现在,杨已辞去广播电台的节目制作,专心写一部纪实作品,名为《法律与社会》。他说:“回顾往事,我毁了自己的家,被子女抛弃,时间都浪费了,仿佛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堆垃圾。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在死前写完20本书。”
(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