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60)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施武 何亮 丁小双 徐斌)
怎么学雷锋
施武
学雷锋应该说是件好事,因为雷锋是好人,学好人做好人总没有错。问题是:学着学着,总是变了味了。
我小时候也学过雷锋,记得有一次是给警察岗亭打扫卫生,把个岗亭擦得明晃晃的,上面的玻璃之透亮像是我们动了手脚把玻璃拆下来了似的,给自己家干活都没这么卖力过。还有一次是满大街找铁钉,最后到老师那儿去称重量,比谁捡得多,没问过那些锈不堪言的铁钉将派什么用场,只记得我捡得不算多,好像这雷锋没学好。
今天我骑着车出门没多远就看见三五个小学生举着牌子高喊:“免费打气!”小嗓子一声高过一声,牌子上写着:“学雷锋,免费打气。”我的车真的有点气不足,可是并不怎么想让他们打气。一路下来,总共不足千米的一个路段上,竟然有五六组如此吆喝的小孩。听来听去,他们的吆喝里,那“免费”二字似乎是其精华所在,喊得尤其使劲。其中有两组小孩相隔的距离不太远,当一个骑车人果真停下来让一组小孩免费打气时,另一组小孩的脸上明显流露出焦虑的情绪,于是更加使劲地喊叫。由于我要过马路过不去,就看着他们给那个人的车打气。打完气后,那个人刚说完谢谢要走,举牌子的小孩拿出一个小本子,请受益者留言。那人走后,几个孩子都凑到小本前:“数数,几个了?”
我走了。没什么可看的,跟我小时候的境界差不多。
雷锋干免费服务后面跟的目的状语是“乐”—助人为乐。我等如此学雷锋的目的状语是上面的评语,评语好了,许多便宜也能沾了。这真是对雷锋的亵渎。
正巧我在读茅于轼老先生的书,其中说的学雷锋的坏处更严重: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义务修理锅盆碗罐,于是在他面前排起了几十人长的队伍,每人都拿着一个待修的东西。电视台喜欢拿来做宣传。茅先生说,如果没那个长队,宣传就没意义了。可是,那个长队里的人可不是来学雷锋的,是来捡便宜的。所以,以学雷锋的方式教育人,每教育出一个好人,必然同时培养出几十个专拣便宜的人。这样,拣便宜的人将数十倍于做好事的人。茅先生是经济学家,他算了一笔账,发现从经济效率上看,这种在实际运用中变了味的活动实在是弊大于利。
(本栏编辑:苗炜)
透明和不透明
文 何亮 图 王焱
“斗私批修”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那阵儿,我正在长白山下的一个部队里当兵。每天要冲着伟大领袖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不说,还要随时向组织上汇报自己的“活思想”,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比如下岗回来的路上看见老乡的苞米曾想过掰两穗烧着吃,虽然终于没掰;拉练走累了时想过装出点病上收容车,虽然终于没上,等等。当然所谓组织上实际就是我们连队的指导员,他对听取连里兵们的思想汇报有一种特殊兴趣,兜里总揣着个记录人们活思想的小本子,还有一些可以针对各种活思想对症下药的导师名言领袖语录等等。山于兵们在汇报自己想法的同时总是会捎带着讲些周围的人和事,所以我们这位指导员对连里的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有时谁在被窝里喊出句梦话也会马上传到他耳朵里去。至于他自己,却从不向我们坦露什么,像电影里的一些大人物似的喜怒不形于色,满脸只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让群众尽可能地通体透明却把自个儿包得紧紧的,这专利要归到咱们的老祖宗头上,打从孔夫子起就说“民可使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也说过“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就都含有教领导只管看群众的牌千万别让群众看领导的牌的意思。不过那会儿还只是偏重于不让老百姓知道政治上的道道,倒也没强迫他们坦露自己,可能那会儿的民心毕竟还比较古朴还不怎么危险吧。到了唐朝,武则天前无古人地以女儿身当了皇帝的时候,总疑心有人要造她的反,就发明出一个叫铜匦的玩艺儿来,让人往里头投告密信。明朝的朱元璋,恐怕也是因自己出身太低文化太浅,当了皇帝还总觉得跟做梦似的,心里不那么踏实,于是也弄出“检校”和“锦衣卫”等手段来,其耳目之广,察人隐私之细,可谓登峰造极。真正把权力的眼睛张到极致,让普通群众透明到极致的,恐怕还得数“斗私批修”和“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那些年头。我和我的战友们站在老人家的像前请示汇报时,向指导员也就是向组织上汇报思想时,绝对是十分虔诚的,我们之间的互相监视互相打小报告也大都是自觉自愿的,因为都把这当成是帮助同志爱护同志。
一个人对于想要窥探他人隐私的统治者来说越来越无藏身之地了,这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不过作为已经被逼到墙角再无退路的个人来说,唯一还有些反抗余地还可找回些精神安慰的办法,是要求政治也得尽可能地透明一点—反正当年我要是知道我的指导员在让我们“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候却跑到村里去搞女人,我肯定不会傻×似的每隔一周就向他汇报一次思想,听他用抄在小本子上的领袖或导师的名言来解我的思想疙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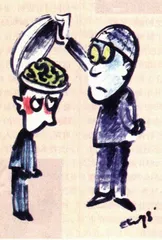
有关品味
文 丁小双 图 王焱
凡是干记者这一行,大概都希望能有皮特·梅勒那样的采访机会,这厮对富人如何花钱有兴趣,有一天,美国(GQ)杂志的老板打电话给他,说你不是对富人花钱一事想有所研究吗,那你就去跟富人鬼混吧,账单山我们报销。
梅勒接受了采访任务,写回报道,并辑成专著,名为《Expensive habit》,台湾人译成汉语,叫《有关品味》。
梅勒在里面讲故事,说1000英镑的一顶巴拿马草帽,1300英镑的定制皮鞋、雪茄、衬衫、鱼子酱等等,极具诱惑力,我这儿不想复述,倒是想说说这书名的译法。把“奢侈的习惯”译成“有关品味”,就是承认金钱与品味划上了等号。这样翻译我不大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因为我受过刺激。某一日,我跟一位有钱的朋友去逛时装店,正赶上打折,小姐就劝我那位朋友买一件皮衣,说:“可以便宜2000块呢。”我那位朋友着装考究,钟爱范思哲,听了小姐的话,很不以为然地说:“我这件衬衫就2000多块。”他手指衬衣领子,脖子一歪,那意思是让小姐看清他衬衫的牌子。这位朋友的言谈举止让我颇为脸红,要我说,这样做很没有品味。
我不是说有钱人都粗鄙,而是怀疑一股风气,那就是把品味当成一种商业行为来操纵。北京有一家鞋店,以有品味号称,去年夏天,我的一位女同事从那儿买了双凉鞋,鞋瘦长,价钱不太贵,200多块,可穿上去并不舒服,做鞋的是艺术家,追求鞋子的造形可能甚于穿着的舒适感,女同事将就着穿,后来发现,凉鞋上的皮带子居然掉色,染得脚丫子上右两个黑道。要我说,这样的鞋应该属于劣质产品,尽管造鞋的主人说他们的产品有品味。
翻看时尚类报刊,观看时尚类的电视节目,我发现“品味”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有许多建议说如何穿衣戴帽才算是有品味,这些建议都以一定的金钱作基础,如果按这种商业行为的逻辑来推理,那么皮特·梅勒讲的那些东西才算最有品味,与最有品味的东西相比,那些不那么昂贵的东西就不那么有品味了。
我觉得品味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跟钱多钱少没关系。所以,那些自以为有钱才是有品味和那些把有品味当作商业口号的倾向都让我不舒服,毕竟,怎么才算有品味是个很个人化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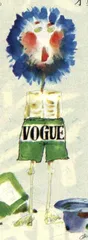
上升为理论
徐斌
在一份晚报上《京剧走向青年》的报道中,提到大学生发出了“我们要了解京剧,热爱国粹”的呼声,并说有的大学准备开设京剧选修课,“让学生不光从欣赏的角度,而且还要从京剧艺术的理论……等等做深入的探讨”。
我并不反对在大学里开设京剧选修课,只要不把它上升为理论,如果那样做了,上升为理论的课程的考试就会非常的可怕,所有的审美的要素都会被排除在考试内容以外,代之以理论,或曰:条条杠杠。每逢考期临近而要背诵大量的条条杠杠以应付各门业已“上升为理论”的课程的考试是我大学生活中最为黑暗的一面。
我的求学经历每每向我证明上升为理论的课程是无聊且无用的。比如二年级时上英文写作课,所用的课本在前几章里先就一些写作、修辞名词梳理了一个遍(赶巧使用此套课本的老师也是极按部就班的人),此番梳理的结果是使得我等学子认为英文写作须另有别才,不是晚生小辈可以学会的。幸好三年级时来了个活宝美国老太太,才让我们认识到写作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说话,解放了思想,不然的话,恐怕我们不仅英文写作做不来,汉语写作也做不来了。
再就是四年级时要学习教学法的课。很不幸,我们的老师是专攻此术的教学法硕士,可以想见,他教的东西,是上升到了理论的。于是我们的教学法课就成为老师口若悬河宣讲理论,学生笔走龙蛇记笔记的听写练习课。天可怜见那些辛辛苦苦背诵了这些理论在最后的考试中拿了好成绩的一些同学:直到他们哆哆嗦嗦站在讲台上,才发现这些理论既不能使他们讲的课更有趣,也不能使之更有条理。大学毕了业,在另一个城市求学的朋友送我一本书,英国朗文公司出版的,’名为《TeachingEnglish Tuough English》。真正教给我实用的教学法的正是这本书和其他讲课真正有趣的老师的言传身教。
前两天监考,发现当年我所学的一门不成系统的课现在也“上升为理论”了,名日“教师口语”。其前身乃“普通话”课是也。当年的普通话课没有给我的普通话任何助益,我很想知道它上升为理论后是怎样的情形。于是在监考的同时翻看一下学生的课本,结果第一页就使我头发昏。再看一下学生的试卷,发现自己的普通话知识根本不足以对付从头到尾充满理论的试题。有学生私下里告诉我这是垃圾,我一百个赞成。我粗略算了一下,我上大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有人向我灌输这样的垃圾知识。随着上升为理论的东西的进一步增加,现在的孩子还有多少有效的学习时间,实在令人怀疑。
既然有人总是抱有把一切上升为理论的壮志,我认为我现在完全有理由对某些学校已开设和将开设的京剧选修课心存疑虑。我希望这样的选修课保持一种欣赏课的状态,万万不可上升为理论。虽然我说过了,我本人不喜欢京剧,可我也不愿意有人要把它上升为理论,倒掉那些还努力想去喜欢它的青年人的胃口。在我的学生时代,要是有人跟我讲京剧的理论,我敢肯定我是要逃课的。但是若有人给我讲一讲某出戏的唱词,没准儿我还满有兴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