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魅力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王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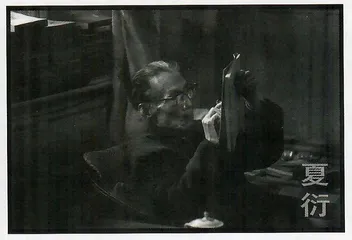
在六部口那个漂亮的四合院和陈设简陋的房间中,我们从来只谈国家、世界、文艺大事。我说:“上星期三,报纸上有一篇重要的报道……”
他说:“噢,不是星期三,是星期四。”
我为他的水晶般的清晰吓了一跳。因为他是夏衍,比我大三十四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距离我出生人世还有7年。
他永远是那么敏捷,条理,言简意赅,不打磕绊,不模糊吞吐,不哼哼啊啊,节奏分明而又迅速,应对及时而又一针见血。他的这些特点使你不相信他是一个九十多岁的人。
他当然是绝对的前辈,然而他从来不摆前辈的谱。他真诚待人,渴望吸收新的消息,而且,青年人一样的幽默。
华艺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了一个 “当代名家新作大系”,出版社的领导要我求夏公给写个序。考虑到夏公的高龄,我起草了一个提纲供他参考。夏公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各人文章写起来风格不同,捉刀的效果往往不好,他无法参考我代为起草的提纲,他自己一笔一划地另外写了颇有见地而又清彻见底的序言。他还对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朋友说:“按王蒙的那个提纲去写,人家一看,就是王蒙的文章么,怎么会是夏衍写的呢!
就这样,他老人家就把我的提纲“枪毙”了。
提起文艺界某些宗派主义现象,夏公不火不怒地笑着说:“我看他们一个是‘鲁太愚’,一个是全都换。”他用了与韩国两位政治家的名字的谐音,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请韩国朋友们原谅,这里绝对没有对韩国政治家不敬的意思。
然后他又俏皮地说:“有些人现在是分田分地真忙了,但是谁知道分了地后长不长庄稼?”
他莞尔一笑,觉得有趣。
我从没有看到过他发怒,他也从来不向我诉苦,哪怕是老年人的生理上的病苦。他从不谈个人,也不说任何个人的坏话。对于个人之间的亲疏远近恩怨,他一贯认为是小问题。这样我也就不好意思向他抱怨任何人,包括抱怨起来绝对不会冤枉的人。同样,我也从不与他谈我个人处境上的风波。上述的幽默中的讥讽意味,对于他来说,也就算是到了顶了。他自己还是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每天他细细地看书看报听广播,只关心大事。
小事当然也有,例如养猫与观看世界杯足球比赛实况转播。
今年元月初,我最后一次在他清醒的时候看望他,我们谈论的是社会治安问题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胡绳同志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那天他精神很好,坐在椅子上谈笑风生。说“曹操”“曹操”就到,说着说着胡绳同志进病房来看望夏公来了。据说那是他此次病情不好以来情况最好的一天。
倒数第二次与他(昏迷前)的见面是去年11月底。他那天十分疲劳,静卧在病床上。他已经卧床数日了。见此情况我稍事问候便起身告辞,以免打搅。夏公平躺着衰弱地说:
“我有一个耽心……”
我忙凑过去,以为他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他说:“现在从计划经济变成为市场经济,而我们的青年作家太不熟悉市场经济了。他们懂得市场么?如果不懂,他们又怎么能写出反映现实的好作品来呢?”
我感到惊呀。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夏公关心的仍然是全中国的文学事业。
他的离去也是颇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的。1995年1月21日,他清晨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就感觉不好,发了点脾气,摔了一样餐具。于是他自觉不对头,找了子女来,从容地、周到地、得体地吩咐了后事。两个小时以后,他昏迷过去了,从此再没有苏醒过来。他一辈子清清白白,走也是清清白白地走了的。
许多年轻的与不年轻的文艺家都喜欢到夏公那边去,与他交往令人心旷神怡,温馨而又超拔。他是聪明而又宽厚,德高望重而又平等待人,洞察世事而又不失趣味乃至天真,直面真实而又从容幽默,我行我素而又境界高蹈,永保本色而又并不苟同,更不知道什么叫迎合讨好。他是铮铮铁骨,拳拳慈心,于亲切中见分量。夏 公的性格是一种美,夏公的人品与智 慧实在是充满了魅力。他的去世令我万分悲伤,但是一旦回忆起他的音容 笑貌谈吐识见,我不能不发出会心的满意的微笑。 夏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