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评点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李书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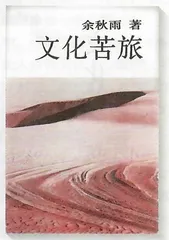 一
一
京沪批评界一直对余秋雨保持沉默,我相信这沉默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余秋雨关于文化的一系列文章唤起了当代文化人一言难尽的心情,也把他们置于欲说还休的境地。
余秋雨以堪称鲁莽的方式去揭示文化人内心最隐秘也最神圣的角落,以一种使文化人不无羞耻的语调来表达他们的骄傲和尊严。对于文化人来说他既是同志,又似异己,对他的文章是褒还是贬、是认同还是拒绝都有违于一个文化人的良知,而非褒非贬的温和评论又难以容纳阅读余秋氏文章所产生的强烈情绪。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对余氏文章说一点想法,一种现象难于评说正是它需要评说的充足理由。二
余秋雨无疑是一个文化的热爱者。“我终于答应交给他一本主题文集,主题就是文明,碎成了碎片而依然光亮的文明,让人神往又让人心酸的文明”(《文明的碎片?题叙》)。余秋雨喜欢用阔大的雄壮的词汇,所以他反复申述他文章的主题是文”;而实际上他所谓的“文明”在这里显然有点大而无当、辞不达意了,他所说的其实不过是“文化”,是文化人从事的那种文化他的文章或者选取中国文化史中最有光彩的片断加以浓笔重彩的渲染,或者选择垂名千古的文化英雄加以一唱三叹的讴歌,或者选择毁坏文化的愚氓加以毫不留情的鞭挞,都很带声色。
他的用意肯定是极其严肃的,严肃得甚至太有点正襟危坐了,以至于他的这些被称为散文的文章都以论文的章法来结构,一二三四,起承转合,少见散文应有的那种轻松和随意。他的文章写得很投入也很用力,显出一种不加掩饰的刀斧之痕。
作为一个文化人,余秋雨这种对文化的执著本来是平常不过的,然而问题却并不如此单纯。在阅读中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记起我们所身处的现时代也即余氏文章的语境,我们发现只有把余秋雨放到他自己的语境中来观察他才显得意味深长。余秋雨身处其中以高亢的声音张扬文化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漠视文化、漠视文化人价值的商业时代。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文化人及其价值在遭受悲剧性击打之后紧接遭到喜剧性消解,当文化人阶层意欲在悲壮中重新登台的时候却发现场景已换、观众已空,娱乐大腕和商界大款取代他们吸引了大众的视线和兴趣,他们的信念和话题在整个时代变得言不及义,文化的新旧之争转换为文化的有无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同时天涯沦落。不仅是文化被作为民族最高价值的古典时代已经遥远,不仅是八十年代回光返照式的文化运动已经一去不返,即使是把文化视若洪水猛兽因而也从反面体认其重要性的“文化大革命”也已恍若隔世。最使文化人受伤的也许还不是他们所受到的冷落,而是从千年受尊崇到一朝被冷落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文化人面对街灯迷离、物欲横流的商业时代产生了落花流水般的失败感和渺小感。
这一切用余秋雨的话说就是“文明成了碎片”。而余氏本质上是一个在这文化失败的时代里不甘失败的文人。他不愿意随波逐流弃文从商,也不愿意退居一隅独守自己的园地,他身上其实很有几分文化战士的品格,他要重建文化的至尊地位。他的文章少有周到的描写,多是滔滔不绝的主观倾诉,难平的意气使他有几分盲目,对周围的世界难以静观;他的叙述语调也是朗诵式的,用的是社论的节奏和诗的旋律。他的写作不是一种交流而是一种宣谕,他竟然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里展开了一场单枪匹马的文化启蒙。
作为一个文化人,在阅读中我不无同情地注意到余氏文章的种种细节。余氏最着意也最着力的是写文化和文化英雄的悲剧,以及这些英雄们反抗并且压倒命运的悲壮。在这种抒写中,余秋雨寄托了他的怆痛和愤怒,也寄托他的抗议与挑战。他笔下总有一种难以释解的紧,他下笔总是把背景和多种的成份删减得非常简单,把故事熔铸得很纯粹,纯粹得可以一无障碍地表达他强烈的抒情意向。而强烈的抒情意向往往也都十分弱,遇到哪怕是些微非抒情杂质都会顷刻瓦解,所以作者必须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杂质排除。其实苏东坡在黄州的处境和心境要复杂得多,但余氏却将其简化为一个“突围”的姿态;其实范钦藏书自有其一言难尽的动机,而余氏却执意地把他简化乃至曲解为一个怀着隐秘文化使命的地下工作者。他下意识地把他的人物和场景都造型化了;这种造型化的形象确实给予读者强大的心理冲击,也只有这种凝固而单纯的造型才拥有那种文化征服的力量。与这种造型化互为表里的是余氏往往把文化形象理想化,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机会来烘托文化的辉煌、庄严和繁荣,就连提到朱熹讲学“一时之舆众,饮池水立涸”这样未必可信更未必可喜的记载时,他也精神为之一振。在《笔墨祭》中他写道:“相传汉代书法家师直官喜欢喝酒,却又常常窘于酒资,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你看,他轻轻发出一个生命信号,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在这里他已完全是按文人心中的想望来描写俗世了。这种理想化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精神传统;古代士人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文人们一种经典的自我夸大。其实“乱臣贼子”们根本就不看孔子的《春秋》,更何谈惧怕,他们甚至可以把孔子呼来喝去。然而这种精神传统对文人来说却有自我的意义,在某种境况下甚至有助于他们重建自己的信心和人格。余秋雨今天援引这种精神传统,是对文人失落乃至沦落处境的一种防卫和对抗。
在这种与物化时代对抗的心境中余秋雨无法平静地叙述哪怕是一件本来很轻松的事情。漫游西湖、凭吊古迹本可以自在从容,但余秋雨却使这种漫游和凭吊颇带上了几分文化示威的意味(《西湖梦》);把玩笔墨本也是一种雅趣,而余秋雨却使这种把玩充满了斗争的激清(《笔墨祭》)。“示威式的漫游”和“饱含激情的把玩”成了我对余氏文章挥之不去的阅读印象,也框定了我对余氏的基本认识。我甚至发现他文章的题目也出奇地整齐,成五字(《风雨天一阁》、《寂寞天柱山》),成三字(《道士塔》、《阳关雪》、《西湖梦》、《笔墨祭》),成四字(《千年庭院》、《抱愧山》、 《分关何处》),排在一起有一种队列般的凛然。这也是一种战斗的造型?三
从评价的立场看,余秋雨的文章自有其来由,他的许多段落和句子也写得很得趣,作为文化人读起来还时时会有一种同仇敌忾的亲切感。然而,也正因为作为文化人、作为同类来阅读,余氏文章中才见出一些让我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东西。他用心太多,用力太过了,他的文字有太强的表演性,表演得可以说有些做作了;他的不少浓得化不开的句子在浪漫主义已经消歇的文学时代读来难免使人面红耳热,他太想追回文人从前的姿态了,却反而显得有点失态;他也太想在当代建立起文人的尊严了,却反而变得有点折辱尊严。尽管余氏总是在慷慨陈词,但你读过去就会发现他的声口总带着几分空洞、几分虚弱,还有几分凄凉。
最先破坏我的感觉的是《风雨天一阁》中的段落,余氏写到他去天一阁时正赶上下大雨,他不得不脱鞋趟水进阁;这本来很平常,但余氏却抓住这平常的情节一味地生发:“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 ‘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者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这也太自雄自壮了,也太煞有介事了,文化人再焦灼、再急于表现也不可以到这种见神见鬼的程度。余秋雨在《都市良知》一文中写到上海一位钢琴家之死:“为什么范大雷之死会使整座城市哆嗦一下呢?为什么熙熙攘嚷的人群都突然为之停步,踮起了脚尖?”这一望而知是在夸大,这种夸大也太过份。余氏对于文化的被承认、对于文化的社会地位看得太重,因而他不自觉地给自己制造这种幻觉。
余秋雨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总爱用那些望之俨然的套语,诸如“文化感受”、“精神标准”、“文化指令”、“序列”、“网络”之类:这即使不算败笔,至少也是种着相。何况余氏文章中还有真正败笔或称硬伤。“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阳关雪》)。据我的记忆艾略特的荒原意象同余氏眼中的坟场形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竟会想起《荒原》。《笔墨祭》中写到林纾,居然写及“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开了个玩笑”,这显然是信口乱说。当时的“双簧”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保守派的口吻攻击《新青年》杂志,刘半农以记者的名义作答的;刘半农既没有“假冒‘王敬轩’”,也压根与林纾无涉。这种硬伤虽曰细小,但在以张扬文化为主旨的文章中却是不应该出现的。余氏文章中的用词也有不妥贴处,常常因追求华丽和宏大而显得不自、不地道。 《文明的碎片》中第一篇《废墟》的第一句话“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就有语病,“寄情废墟”如果不是不通的话,至少也在与“诅咒废墟”的并列中显得不工。
我们看到余秋雨的文章本意在于拯救文化人的沦落,但有时却变成了另外一种精神沦落;本意在于代表文化人发言,但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都是文化人对于现时代的一种应对;你或许不欣赏这种应对,但你却应该失语。然而,无论如何,余氏的文章重视它。文化人与这种商业时代的磨合将是长期而痛苦的,余秋雨的文字可以看作文化人在这种磨合中的一段心史。 文学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