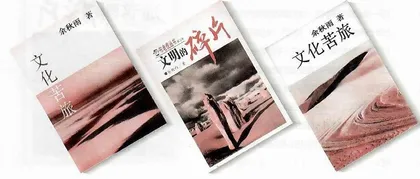近访余秋雨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晓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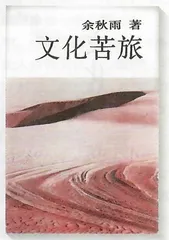
▲徐甡民 □余秋雨
▲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多层结构,虽有通联,更成割据。因此学者的 “知名”经常只是在于高耸狭小的层面上,而并不具有实在的社会性。余秋雨先生却是个例外。如今他的名声得以穿越多层文化的壁垒,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概念。
对于声名日炽,余秋雨自己怎么看呢?他有没有为此所累呢?
□我是一个文化研究者,现在却常常成了一个被研究的对象。我的一些文章受到读者的欢迎,除了感谢之外,有时也有点惊讶。我文章中谈到的许多文化观念,其实前人也多有谈及,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只是于此表达了我的生命体验,可能有一些新的视角和新的表述。甚至有许多“块面”,在理论的深刻性、完整性和严密度上,都还有遗憾。在这里我时常感到惊讶的是,许多读者对文化对以前的东西知之甚少。
另外也有点忧虑。我收到许多来信,其中不少都表达了独尊一家、排拒其他的意思。我是一个文化多元论者,看到自己的作品诱发了某种排他性,是我极不愿意的事情。这并不是谦虚,实在是因为比较清醒。譬如说到什么散文领域的导向,这就成笑话了;包括某些具有威胁性的比较,都是不恰当不可能的事情。
说到名声之累,当然会有。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名声这东西经常与讦非议诽谤构成正比,这倒也没什么。只是现在应邀参加的社会文化活动太多,当然我并不绝然拒绝和反对参与社会文化活动,这正是我主张当代文化论者既要有书面文化,也要有行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各种关系各种制约,使我自己很难把握一个比较好的度,关键是要从被动参与变成主动参与……
▲历来的文人形象或者说是学者风范,总是格守经院书斋的谦谦君子。但当一个学者的能量及风格不再与经院书斋完全对等以后,他就在某种程度成了一个公众性人物,这时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都要受到社会公众的更多关注和批评。
学者与社会的联系应该在于他的学术以观点。但是既有了“公众性”,人们就会将这种对于明星的关注移诸于一个学者,有时的确是滑稽而又尴尬的。
□治学的道路与方式,在观念上也是变化发展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守恒与变体共同存在交替发展的。但是人们对于传统总是比较习惯,而对于变体则常常不以为然。如当年胡适、郭沫若,是为学者无疑,但是在更早的比如晚清的国学家看来,显然是大不以为然的,学者怎么可以写小说?怎么可以写白话诗呢?
我很欢迎对我的文章的批评,也欢迎提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实在用不着再大表姿态的。
但是同时我也希望读者不要对我的文章寄予太高的要求。许多读者从各个方面,对我提出了各种很多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要求。我理解他们的善良愿望,但是我实在只是我自己,很难超越了自己而去成为别的社会角色。
至于出于某种不健康的心理,出现的无端攻汗,那就是另外一种问题了。我想如果我什么事情也不做,就没有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既是对于我的某些“社会抬举”的反弹,也是由于这块土地上的某种文化劣根性所致。对这些事,以前,我一直奉行不予理会、沉默是金的做法,但是我发现这样做有时反让人觉得是软弱虚弱,所以我不打算一再沉默了。同时我希望中国一切具有或多或少文化成就的文化人,不要受到这种麻烦和干扰。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个人的问题呢?原来我们习惯中的学者多是“夫子”型的,他们温良谦和,诚恳笃信;他们发奋著述、不求闻达;他们激扬蹈励、忧国忧民;他们上下求索,痛苦思考……然而余秋雨却既为学者,又未循人这样模式,端起这些架式,他显得十分“海派”,也显得洒脱,在繁忙的应酬相邀中,巧于周旋与回避。除了在文章中论及,余氏很少对人言及自己的心迹与苦衷。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作为学者,他的交际要比别人多得多,但是余氏又十分重视看重“私人空间”,因而又会令人有种封闭及至隔膜感,使人不容易或者不乐于与之“套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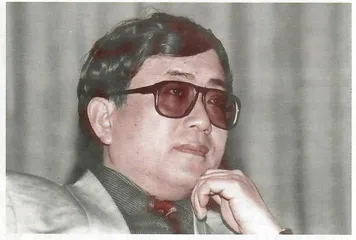
余秋雨先生近照
□我真正是渴望友情和朋友的,我可能的下一篇文章,就会是谈朋友问题的。朋友固然可以十分亲密和随便,但是朋友的真实基础其实并不在于互相开放私人空间,太多的历史事实已经于此做了足够的的交证。我有一位住在虹口区的朋友为人很好,平时家里高朋满座,可是他家中数人最近一起遭受横祸,在最需要朋友帮忙的时候,朋友都不见了。这种事情在社会上发生得太多了,有趣的只是,在一个现代都市里,这些朋友离去的原因,不是顾忌援手破费,而是怕沽了“晦气”。感慨之中,我所能做的,只是把我一部书稿的一半稿费送给他,希望以此给他一些精神上的支援。
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是终极性的,而不见工具性的;在人生世界里,朋友应该是绝对意义的,而事业功名是相对的。
▲有时候觉得,如果余秋雨喜欢“风流”,他会不会是一个当代最大的风流才子呢?但是在这样的印象背后,我们也能十分偶然地知道他“私人空间”中与“风流才子十分不协调”的苦涩。比如在同期完稿的某半夜,他的头痛病犯得很严重,只好摸着墙壁去找药,竟至摔倒在地。独居八年,这时自是无人照应。凉水扑面稍事卧床后,他又再起床笔耕。这次极其偶尔的流露,我想可以说明,任何才学都来之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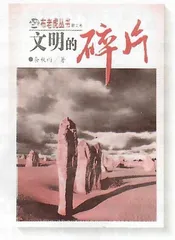
关于余秋雨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从1992年3月初版至今已重印再版了7次,总印数达21万册,即使不算那些无以计数的盗版偷印书,也创下了中国文化散文乃至全部散文类图书的出版纪录。而新近出版的与《文化苦旅》内容大同小异的《文明的碎片》和《秋雨散文》销量却依然不减。作为学者的余秋雨先生因此而成为明星。
内蒙古武警部队不久前致电《文化苦旅》一书的责编王国伟,欲购 《文化苦旅》3000册,说是要给部队中尉以上的干部每人配发一本。其重视程度仅次于“邓选”。
山东一农民,到处求购未得,以为此书只能通过拉关系走后门才能得到,于是致函北京某出版社编辑,愿出高价购买。
在台湾,《文化苦旅》再版过5次。
销售的盛况,引起舆论界的关注。有人统计,不包括港台及海外的报道,《文化苦旅》在大陆的见报率不下150次,而各种名目各种类型的奖励和荣誉,几乎将这本20多万字的小书淹没。据了解,仅1992年一年 《文化苦旅》所获大奖有:
上海市文学艺术成果大奖
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
金钥匙图书一等奖
台湾1992年最佳读书人奖
台湾金石堂最佳书奖
余秋雨获得各种各样的头衔有:上海市政府咨询委员、深圳市政府文化顾问、上海交大名誉教授、哈尔滨话剧院顾问等。据粗粗统计,有案可查的如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门的顾问、地方艺术院团名誉院长、团长之类的兼职就有100多个。而他所拒绝的兼职有多少,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电视台举办电视小品大赛要请余秋雨当评委,各类笔会研讨会要请余秋雨去讲课。
面对余秋雨及《文化苦旅》所产生的轰动效应,理论学术界则众说不一,毁誉参半。
“余秋雨的散文,将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留下独特一笔,在他之前尚未有人这样写散文。他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找到了契合点,涌动着新的血液和生命力,创造出全新的散文境界,别人不可替代,不可模仿”,上海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这样说。
另一位著名学者则认为:“余秋雨散文写得是不错,把学术通俗化,使一般读者容易走进,但那种未经整理过的、完全感性的思想自然难免缺乏逻辑,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虽然漂亮,但似乎很难写出深度。”
北京的一位相当年轻的学者则认为:“文学一旦成为一种工业操作,批量生产的东西,其思想的含量和情感的浓度自然会减去许多。余秋雨散文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有别于那些职业散文家,但到后来他自己也成了职业散文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这只是一部分评论者的看法。令人奇怪的是,笔者曾就“余秋雨热”请教过不少学界泰斗文化名家,他们对此都“亡顾左右”。与大众的爆热,成鲜明对照,学界中的人们对余秋雨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沉默。
《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的第二本散文集《山居笔记》已然封笔。有人说南方某书商已花8万元人民币将《山居笔记》版权一次买断。也有人说,上海某出版社出巨资给曾首发 《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个专栏的《收获》杂志社,准备出一套含 《山居笔记》在内的“收获丛书”。
《山居笔记》能否象《文化苦旅》一样轰动得漫天飞响,目前尚无法得知。也不排除《山居笔记》再度将余秋雨推向文潮的可能。
有一位青年评论家对此发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见解:“余秋雨的时代结束了,但好多人却似乎刚刚开始关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