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着科学羊肉的纪录片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袁越)
 ( 《我们他妈到底知道什么?》剧照 )
( 《我们他妈到底知道什么?》剧照 )
凯瑟琳今年36岁,独身,有自己的房子,硕士毕业,工作稳定,收入颇丰。她属于美国城市中产阶级中人数正在急遽增长的一派——不愁吃穿,热衷于去世界各地旅游,喜欢钻研东方哲学。注意身体健康,但同时却花费了更多时间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最重要的是:他们自认为很叛逆,是美国城市居民中最讲究“酷”的一族。去年夏天,这一派人不约而同地说着同一部电影:《我们他妈到底知道什么?》(What the #$*! Bleep Do We Know?)。
这部去年2月份出品的电影选择了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一个只有3289名常住人口的小镇耶尔姆(Yelm)作为首映地点,制片方没有在媒体做大规模宣传,而是完全依靠观众间的口口相传。到去年7月,这部电影的期待值被抬到很高之后,它才终于在旧金山首次面对主流观众群。在那个历来崇尚自由精神的城市,这部电影一炮打响,当时的美国媒体纷纷转载一条消息,说到现场观看首映的600余名旧金山观众在电影结束后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家兴致勃勃地交流心得,很久都没有人离去。
如今这部成本只有500万美元的小制作电影已经获得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票房,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三卖座的纪录片。世界各地的许多观众自发地成立了讨论小组。今年春天,这部电影的DVD正式发行。网上预订该DVD的人数仅次于《超人总动员》。
表面上,这部电影讲的是量子物理学,起码采访对象有一大半是这方面的学者。但这部电影没打算让观众准确理解量子物理学的全部要旨,而是着重描述量子物理学最有趣的两个推论:波粒二象性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的意思是说,微观粒子具有“波”和“粒”的二重性质,有时候它们的行为像波(比如光),只有能量没有质量;而有时候它们却像粒子,有质量,有弹性。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意思更为神奇:你不可能同时精确地测量出一个粒子的质量和速度。这句话推广一下就是说: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地方!读者只要稍微想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两点是和我们的日常经验背道而驰的。
在讲述量子物理学的同时,电影还穿插着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故事。阿曼达是一个摄影记者,正在遭遇所谓的“中年危机”,干什么都不开心。有一天,她走在街上,接连遇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见到了许多妙语连珠的高人。在他们的旁敲侧击下,阿曼达仿佛突然悟出了人生哲理,电影结尾时候乌云散去,前途一片光明。这一段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如果把它单独拎出来,就是有史以来最蹩脚的故事片。不过,在这样一部据说是有关量子物理的科教片里出现,它立刻就成了一个卖点。有这段故事,这部电影便立刻从“最差故事片”变成了“最酷科教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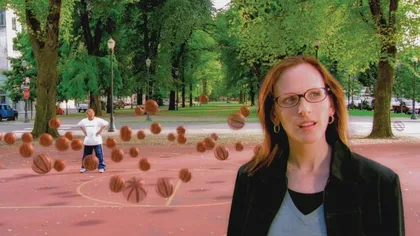 (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玛丽·玛特琳扮演剧中的女摄影记者 )
(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玛丽·玛特琳扮演剧中的女摄影记者 )
阿曼达的出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让观众觉得这部电影说的就是他们自己。那么,阿曼达最后到底悟出了什么高深的道理呢?电影里的“她”是无法告诉你的,因为这位女摄影记者的扮演者是曾经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玛丽·马特琳(Marlee Matlin)。众所周知,马特琳的获奖作品是1986年的那部《小神的女儿》(Children of a Lesser God,又译《无言的爱》),她不但扮演的是一名哑女,生活中她也真的是个哑巴。选她作为女主角可谓一箭双雕:一来她有很高的知名度,却要价不高。二来她不会说话,所有那些带有明显说教性质的访谈和旁白便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那么,旁白都说了些什么?其实归根到底就一句话:人的思想会对现实世界起作用。这个明显是“反科学”的论点是怎么推出来的呢?首先,电影中用了很多特技镜头来描述人的大脑的工作方式,并由此告诉观众,外部世界其实并不存在,它只是大脑内部产生的幻觉而已。其次,电影中还演示了几个很有趣的实验。比如,一位被采访者声称在美国的“犯罪首都”华盛顿特区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大帮自认为通灵的人齐聚该市,希望用集体祈祷的办法降低犯罪率。结果真的见效了,犯罪率降低了25%。不过这位被采访者的一句话泄漏了天机——原来当地警察一开始对此实验持怀疑态度,后来被实验者的热忱所打动,开始积极配合他们。警察如果参与了这个实验,犯罪率能不下降吗?
量子物理学,正是这门艰深的学问为导演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既然世界是不可测量的,那也就是不可知的。既然基本粒子都具有波粒二象性,那么他们之间就可能不停地以波的方式传导信息。既然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没准大脑中的那些电子在同一时间跑到了体外,对外部世界发生了作用。最重要的是:既然人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习以为常的原理都已经被量子物理学推翻,那么这个世界理所当然地会有很多奇妙的事情超出了常理。于是,任何奇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人的大脑没准真的能控制外部世界。哪怕只有一点点作用,就足以让人叹为观止了。
一个看似“反科学”的论点却被“科学”的方法所证明了。这种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做法正是这部电影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这部电影的导演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前文提到这部电影的首映选择在华盛顿州的耶尔姆镇,因为这里是一个名为“拉姆沙”(Ramtha)教派的大本营,而这部电影的三个导演以及投资人都是这个教派的教徒。据称这个“拉姆沙”是一个生活在35000年以前的亚特兰蒂斯大陆上的武士,他委托一个名叫“J.Z.奈特”(J.Z. Knight)的通灵女士向人间传话,于是奈特受主之托,创立了这一教派。教主奈特其实在电影中作为一个被采访的对象多次出来讲过话,只不过她和其他那些科学家一起出现,电影中又没有打字幕告诉观众采访对象的身份,于是大家很容易把她想成是科学家中的一员。
最先提到这部电影和耶尔姆小镇之间关系的美国《时代周刊》意外地选择了沉默,并没有进一步告诉读者耶尔姆小镇和“拉姆沙教”的关系。这大概是因为《时代周刊》很怕这些“新世纪”宗教。原来,《时代周刊》曾经登载了一篇揭露“科学教”(Scientology)的文章,被该教告上了法庭,并遭到该教教徒们的恐吓。其实这个“科学教”翻译成“山达基教”或者“认知教”更为准确,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学会认识世界的方法”。这个教派的确非常注重利用科学做幌子,教主朗·胡波特(L.Ron Hubbard)自称是一个核物理专家,他对外宣称自己所用的方法很多都来自科学知识。可是,他的核物理学位,以及所谓的科学方法后来均遭到科学界的质疑。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教”非常善于利用好莱坞的影响力。相信很多读者最早听说这个教派是因为好莱坞的许多大牌明星都是它的支持者,其中包括汤姆·克鲁斯、妮可·基德曼、约翰·屈弗塔和科特·科本的妻子科特尼·勒夫。一份被公开了的“科学教”早期文件中赫然列出一个条款:凡是能和好莱坞明星搭上关系的教徒都可以获得奖励。正是由于这些明星们的言传身教,才使得“科学教”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鼎盛一时,成为美国第一大“新世纪”教派。可是后来一些教徒开始控告教主胡波特非法敛财,一些该教的内幕也纷纷被包括《时代周刊》在内的媒体披露了出来,这才使得“科学教”渐渐失了人气。
如今,随着这部纪录片在全世界的热销,“拉姆沙教”大有取而代之的气势。J.Z.奈特比胡波特还要聪明,她深知科学和好莱坞对于宣传新宗教的价值,于是她巧妙地把这两者结合了起来,用这样一部酷毙了的电影,吸引了一大批自认为激进的城市知识分子的支持。
对此现象,科学家是怎么看的呢?美国西北大学粒子物理学家安德列·迪格维尔(Andre de Gouvea)对记者说:“这部电影的导演利用了物理学中一些还没有完全被解答的疑问,以及不太容易被测量的问题,巧妙地误导了观众。”迪格维尔博士进一步解释说,量子物理并不是像这部电影所说的那样是无法预言的,正相反,它能够准确地知道粒子所有可能的行为轨迹,并能在统计学上给出一个粒子所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一般人大概认为凡是涉及到“概率”的都不能称作“精确”,事实恰恰相反,统计学其实是一项非常严密的数学分支,科学家可以依靠概率计算准确地预言所有行为。
“更重要的一点是,量子物理学是针对微观世界的一门科学。”加州大学圣塔库鲁斯分校的粒子物理学家布鲁斯·舒曼(Bruce Schumm)这样解释,“这部电影中提到的关于思维改变世界的说法是完全不科学的,需要做很多严密的科学实验才能证明它的正确性。”而这一点在电影中完全没有涉及。
“我其实不在乎这部电影的正确性。”那位圣地亚哥的凯瑟琳这样对记者说,“它让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对生活重新有了信心。”确实,这部电影没有任何涉及宗教的说教,甚至还提出世界上不应该只有一种宗教统治全人类。这种符合世界大趋势的说法肯定赢得了很多人的掌声。其实,类似说法正是如今流行的“新世纪”教派的一个共同之处。他们已经不把自己叫做宗教(Religion)了,这个词有“组织”的嫌疑。他们喜欢称自己为“灵性”(Spirituality),或者叫做“权力下放”(Empowerment)。他们宣称人性高于一切,人是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说法给了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以极大的鼓舞。但是,你想学习自救的技巧吗?你想喝“被祝福”过的圣水吗?你想知道怎样获得下放的权力吗?请掏钱入教。这就是他们的敛财办法。从“科学教”到“拉姆沙教”都是如此。这两个教派的创始人如今都已经是百万富翁,依靠贩卖自救处方而聚积了惊人的财富和权力。 纪录片科学羊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