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墨之战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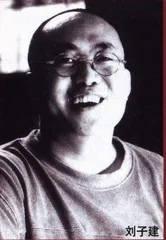
刘子建
这个题目好像要说堂吉诃德骑士的风车之战,在8月20日刘子建的“墨与光”实验水墨画展上,要找到这之间的相似之处似乎不难。刘子建被认为是谷文达之后最重要的实验水墨画家,2000年在美国的中华5000年展览上,实验水墨也是以他为代表进入展览。尽管如此,批评家们好像把这个高帽子放在这儿之后就了结了对他的继续评论,因为很多批评家不知道这次展览是他的第一次个人展览,刘子建一再说从中可见自己的寂寞艰苦。
中国的水墨画是很奇怪的领地,沿袭传统画法和题材的作品有巨大的需求市场,那些画家基本上不介入当代艺术的各种争论和比拼。另一些人视变化为生活的法规,过去需要的东西,今天不再需要;过去创造的东西,今天不再创造,现代艺术也不能免于这些无情的规律。水墨画就成了一块特殊的实验田,特殊在于,实验者们珍视笔、墨、纸这些材质的特性,以及它们与中国文化身份的连接。同时,按刘子建的说法:“古典模式的水墨或许有自然人伦的自我完满,有天人合一的诗性,但现在的社会生活根本上不是它生存的语言环境。”
中央美院易英教授说:“现代水墨在艰难地突破自身的局限,力图进入当代话语的情境。”他的结论是很难,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悖论。艺术家们作了很多尝试,其中主流是表现水墨,比较激进的是直接走向装置和行为。但表现主义式的水墨疏于形式的研究,离不开套用西方表现主义的精神或欧洲抽象画的做法,而装置和行为的做法更倾向于解构。这块实验田是否还有可为的事渐渐地远离了人们的视野。
刘子建自称理想主义者,是因为他坚信,虽然水墨已经固化成了一种传统文化的识别系统,但线型水墨是对水墨性情的错误认识,它的材料自有独立性,就像中国语言,他就要赌用这种语言来说现代话。当他开始最近实验后,他获得了广泛好评。
皮道坚是中国水墨研究名家,他说:“还没有人像刘子建这样纯粹使用传统的水墨媒材将黑色空间中无序漂浮物的质量感和动感描绘得如此引人入胜。”而又不是西方抽象绘画的中国版本。他的视觉支点在于:大面积的渲涮晕染、拼贴、拓印,他制造的黑色空间是最被看重的新的语言。其次是硬边拼贴,和水墨渲染渐变形成趣味上的对比。易英认为刘子建运用老材料创造出了近乎完美的现代视觉经验。
刘子建说他的战果:过去的水墨更多的意思是诗性的,讲究那种天人合一的趣味;现在他的做法更多的是理性,是可以辨析的。过去的画面就需要一派模糊,飘逸,流动,空灵,而他的画面效果是清晰的,尤其是硬边拼贴,既保留水墨中漂浮的神秘感,又改变了东方式的神秘,在其中加入了拥挤重叠的物质感和焦虑的现代科幻感。从1985年那种表现主义倾向的实验到现在的理性实验,刘子建在所谓实验水墨已经被很多人放弃的时候,坚持要保守着纯洁的水墨表情。
在更前卫的批评家黄专看来,刘子建的坚持更主要的还不是艺术问题,而是一种文化选择,在他的文化选择和艺术语言的选择之间存在的时差依然没有真正解决,但却是一个最有当代意义的难题。(图片均为本刊资料)

宇宙中的纸船·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