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奥斯特:卖文为生,莫过于此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苌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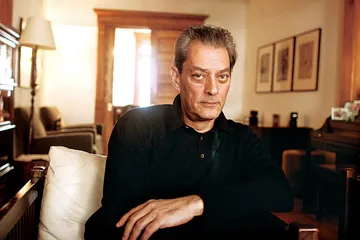 ( 保罗·奥斯特 )
( 保罗·奥斯特 )
即将出中文版的保罗·奥斯特的《Hand to Mouth》(暂定名《穷途,墨路》)是他的自传,写于1996年。作者从他上世纪60年代末上高中开始写起,到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一直写到他历尽千辛万苦等来第一本小说出版。保罗·奥斯特对本刊记者解释为什么这本书只写到80年代初时,笑说:“美国的很多书,都是教人怎么做事的,但我这本书是在教人避免做哪些事。我当时做的很多事都是错的,但在90年代我回视的时候,觉得那并非没有积极的意义。”
现在保罗·奥斯特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他的小说始终在追寻身份与个人的意义,并且以其抽象派,存在主义,意识流——这些不同于美国大陆而是更加欧化的文学色彩而得到认同。在《穷途,墨路》中,保罗·奥斯特写到他在30岁上下的那几年里,碰到的每件事都会以失败告终。他写诗,翻译书,接触各色人等。“那些疯狂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哪里,但是他们在我的记忆里留下痕迹。随着你变老,你会时常回到这些记忆中。”打各种工,但即便是无需劳神动骨的美差,他都无法长期坚持——因为他执著的作家梦。在讲到自己时,他多次提到“固执”一词,这也是很多犹太人与生俱来的性格因素,这最终成全了他的作家梦。
这也不失为一本有趣的自传。保罗·奥斯特1947年出生于新泽西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整个青少年时期,置身于大手大脚的母亲和能干吝啬的父亲不可调和的矛盾之间,可能这也是他进入青春期后既紧张又任性、愚蠢(奥斯特自语)的根源。他任性地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尽管失去大学的保护,他这个反“越战”分子,立刻置身于随时要被征招入伍的风险中。读者不会忘记普拉特,当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系主任,一心想说服学生别在尚有选择的情况下自毁前程,而在保罗·奥斯特退学半年后又给他恢复了学籍。“闯祸嘛,以后有的是机会,不是吗?”那位系主任说。
步入社会后有好几年,保罗·奥斯特一直为金钱焦虑,在权衡利弊后,他放弃自己明晰的直觉,做过很多不靠谱的事儿,但其间他一直没有放弃写作。“要保持练习。”他这样说他的心得。他的第一本书是侦探小说《触击得分》,第一个看过的编辑说,“除去侦探那类东西,你将成为杰出的心理惊悚作家”。但他坚持不改,直至找到新的文学经纪人。“卖文为生,莫过于此。”奥斯特以此作为结束。
已经发行中文版的《黑暗中的人》是保罗·奥斯特出版于2008年的小说,距离他的第一本小说出版已经过了26年,这也是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保罗·奥斯特告诉本刊记者,《黑暗中的人》写了一阵后,他才意识到是对前一本书《密室中的旅行》的呼应。后者是写一个老人在白天的思想旅行,而《黑暗中的人》是写一个老人在夜间失眠,思绪的漫游。《黑暗中的人》有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是老人走神的时候,幻想没有发生“9·11”事件,2002年的总统大选造成美国分裂,新的内战爆发。另一个是现实中老人和同样失眠的孙女的对话和活动。老人渐渐向外孙女敞开心扉,讲述自己婚外恋,也触及孙女的男朋友在伊拉克作为人质死去的真相。两个同命相怜的人在漫漫黑夜中互相医治心灵的创伤,寻找光明。
 ( 作品《Hand to Mouth》及《黑暗中的人》(中文版) )
( 作品《Hand to Mouth》及《黑暗中的人》(中文版) )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高中毕业和大学期间,三次留居巴黎,巴黎的生活经验带给了你什么?
奥斯特:巴黎那段时间对我很重要,那是我特别穷途末路的时候。在70年代早期,我在巴黎认识的诗人和画家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最感动我的是他们的慷慨和善意,尽管他们当时的生活也捉襟见肘,但是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失败的。这种感觉对我那样的年轻人至关重要,他们教会我,不要拿金钱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但是在美国你学不到这些。他们给我上了重要一课,关于“如何做好一个人”,使我受益终生。我年纪渐长后,也很乐意去鼓励年轻人,帮助年轻人。这都是巴黎教会我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没有在困难的时候放弃写作?
奥斯特:因为我心底里接受一点,我写的书也许永远不会被出版,所以出版与否,并不会打击我写作的热情。我写得很自由,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一直沉浸在写作这件事情中,我从来没想过去做别的事情,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我也挣扎了很多年。在年轻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信心可以靠写书养活自己。我写完我的纽约三部曲的第一部《玻璃之城》,没有出版社要它,我带着它去了一家又一家出版社。与此同时,我开始写三部曲的第二部,当第二部写完的时候,第一本还没有找到出版机会,我又开始写第三部。这也是为什么“三部曲”的第三部《锁闭的房间》中,我写了一个小说从来没有被出版的作家,他留下很多手稿,写作的时候,我特别沉浸在他的书被出版的幻想中。在我第三部写到中间的时候,终于碰上了喜欢我小说的出版人,他说:“还有第三部?那太好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黑暗中的人》,仅写爷孙俩看小津的《东京物语》就写了6页,为什么?
奥斯特:首先小说里的孙女是做电影的,而且这部电影的家庭主题扣合小说的主题。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1993年我到东京去,做东京电影节的评委,那年正是《东京物语》上映40周年,他们洗印了一个新的胶片版本,放到银幕上几乎闪闪发亮,上千人在一个非常大的厅看这部电影。这电影没有拿亲情去煽情的地方,但最后灯亮的时候,所有观众都在哭泣。我至今觉得,这是一部超越了东西文化差异的伟大的、有尊严的电影,我非常尊敬它。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小说中所持的反对美伊战争的态度也是你自己的态度吗?你作为美国笔会的副会长,是否了解纽约的知识分子对此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怎样的?
奥斯特:布什时代非常糟糕。美伊战争是美国最大的战略性错误,7年了,“二战”都没有这么长。布什发动这场战争,并没有特别可说服人的理由,现在我们都知道,所谓核武器问题是他在撒谎。我原想他是为了石油吧,但事实证明美国也很失算,迄今我们在美伊战争上已经损失了太多的钱和生命,而伊拉克仍然是一片混乱。美国是个邪恶的独裁者,拉拢喜欢的,打击不喜欢的。一个国家不能满世界乱跑,去修正所有它所认定的错误,我们的政府至今都在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现在我很同情奥巴马,因为他也很挣扎,右翼分子想毁了他,他还要与他们做斗争,尽管右翼在美国属于少数派。现在很多人很迷茫,美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很多人没有工作,失去家园,严重程度接近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三联生活周刊:你最近的一本书是关于什么的?
奥斯特:我的新书《日落公园》将在11月出版,日落公园就在布鲁克林,这对我来说是相对感性的书。其中涉及很多人的很多种观点,关于一个家庭的内部矛盾,关于在今日经济危机下美国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总的来说今日之状况,对于20多岁的年轻人很难,他们每天工作很多,挣得很少。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
奥斯特:我仍然用笔写作,很可能用的还是上次我们对话时的那支笔。每天上午我去我的工作室,平均写三四个小时。一本书的开始对我来说最艰难,我读很多,想很多,刚开始觉得每天能写一页就很好,之后我每天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这本书上。4小时变成5小时,5小时变成6小时这样子,甚至9小时。很耗人,我回家时往往已经筋疲力尽。写作的时候,我并不像有的作家那样在脑子里营造地图,而是更为即兴,一页一页,一章一章地往下写。我总是有很多想法,我觉得写书有一点很吸引我,就是你不知道最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很有机的过程。■ 文学小说莫过于此卖文为生作家奥斯特保罗